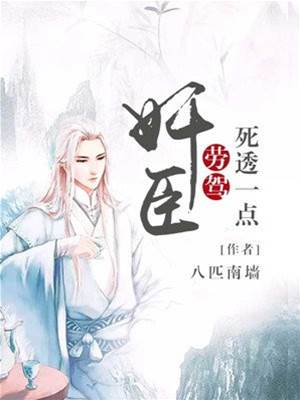《錯嫁皇妃帝宮沉浮:妃》 第十章
接下來的數十日,尚在疆寧的蚩善,加強了對三國絡繹投奔來的族民的排查。
而風長老卻在沒有在王庭出現。
阿蘭說,風長老連日來都在負責青寧城墻的修葺加固,只有晚上方會回到王庭。即便如此,每日里,阿蘭都會定時送上風長老調配好的湯藥。
夕上的些許傷,在這數十日間,逐漸開始復原,背部的箭傷,也結了口子。
但,由于是初孕,加上寒毒,這一胎懷的極是不穩。
可,并不用風長老配來的任何湯藥,每次,都支走阿蘭,將湯藥倒萬年青下。
畢竟,那一日,他沒有應允,替保下這孩子。
所以,選擇這種方式等他應允。
很可悲,很無奈。
然,又能如何?
相信,他一定是知道,沒有服用這些湯藥的。
哪怕,已有這麼多日沒有見他,可,倘若他要知道的一切,他一定就會知道。
這樣一個心思縝的男子,想要瞞住他任何事,真的很難。
心思縝,曾幾何時,他也這麼形容過。
原來,他和本來就是一類人罷。
每日晨起,都會吐,這種況沒有毫的好轉,漸漸地,為了減吐,他每日晚上用的都很,吐完后,早但是出不下的,一日里,等于,只有午飯能略微用點,但,礙著茹素的關系,能用食材亦都有限。
因為加冕為族長的儀式定于七月十六日,族中大小事務,尚不需親力親為,而也愈發的貪睡。
不過,日子,總是過得很快,轉眼,就到了加冕儀式的前一日,這日午后,在榻上睡得迷迷糊糊,一旁,是阿蘭輕輕替扇著扇子突然,一聲尖利的聲撕破這份寧靜,接著,又歸于雀般的寧靜。
Advertisement
夕張開眼睛,輕聲問:
“什麼聲音?”
阿蘭愣了一愣,不過很快就笑著道:
“許是有婢犯了錯,被責打吧。”
“是麼?”夕顰了一下眉,從榻上起來。
殿外的很是灼熱。
沙漠的天氣就是這樣,白天很熱,晚上很冷。
兩個極端,是他必須去適應的。
慢慢地走到殿門,甫到殿門,卻看到回廊那端,走來青的影。
正是風長老,看不到面后的臉,但瞧得出,似乎很是疲憊,他的手上端著水晶的盆,里面,堆滿了鮮滴的荔枝。
走到跟前,將盆遞向:
“給。”
“這——”
夕有些疑,這本是產自嶺南的荔枝,難道,西域也會產嗎?
“是嶺南的商隊帶來的,很新鮮。你嘗一嘗,荔枝溫,這天氣越來越熱,你卻是不能吃寒的水果。”
原來如此。
自是知道這荔枝的難得,以前在巽朝,每每到了夏日,世家小姐也都以此為最大的喜好,雖然不過是互相攀比,沒有幾個是真的著荔枝的味道。因為,這一刻新鮮荔枝的價格,或許,足抵得上民間普通人家一日的開銷。
但,現在,他給這盆新鮮的荔枝,絕不僅僅因為它的價格稀有,卻是細心替考慮到了上寒毒的關系,但凡寒的水果,都是食不得的。
而夏日里,寒的水果卻是占了絕大部分。
“這些吃了,既暖,對孩子,亦是好的。”
聽得出他語音里帶了笑,縱然,看不到他的臉。
低下螓首,只接過盤子,又聽他道:
“外面這麼曬,你要去哪里?”
“只是聽到一聲尖,睡不踏實,才出來看看,城墻那修葺的如何了?”
Advertisement
“稍微修葺加固一下,沒有多大問題。”
“嗯。”
“這王庭,尖聲是常有的,習慣了,就好。”
真的能習慣嗎?
知道,人若真的對于任何事都習慣了,其實是最可怕的。
端著盤子,甫要回殿,他卻突然從手里將盤子接過去,本端的不牢,他這一端,自然,也是沒有任何的阻力,盤子落進手心時,惟有他清楚,自己,有一很淺的失落。
他沒有說話,只端著盤子,隨進得殿。
徑直坐到椅上,他端著盤子,放于旁邊的幾案,隨后,他修長的手指起一枚荔枝,輕輕的沿著那豎形的紋路一擰,那紅的荔枝殼中,便綻開一抹晶瑩的果。
他遞給,卻滯了一滯,若用手去接,那荔枝這麼小,必會到他的指尖,倘若不用手去接,難道,由他喂不?
“讓我來吧。”
阿蘭的聲音將這份僵持打破,纖細的手指從風長老手中接過荔枝,隨后,將殼剝了,放在不知何時準備好的空冰碗里,遞給夕。
這一遞,風長老阻道:
“不能用冰鎮過的東西,以后,這些冰碗不必再用。”
阿蘭捧著冰碗的手,輕輕地了一下,還是收回,道:
“是。”
夏之后,因著天氣炎熱但凡水果都會放在置著冰塊的碗中,一來保鮮,二來也冰爽可口,然,因著夕并不能多食水果,是以,這冰碗,一直沒有用過。
想不到,今日,方用了,又遭了他的說。
原來,他也是會關心人的。
一直以為,他的心,本不懂得怎樣去關心人。
阿蘭的臉上依舊在笑著,只是,清楚,這份笑,是他最艱難的笑。
風長老并沒有再剝荔枝,因為他看到,夕自己輕輕起一個,慢慢地剝了,將那白的果嚼進中。
Advertisement
可,他也知道,是嘗不出任何味道的。
的時間,或許,僅剩下兩年,除非,能找到天香花,只是,那些花,卻都悉數焚盡于旋龍中。
這一次,風長老沒有在殿停留多長時間,帶他出去后,夕把手里的荔枝放下,對阿蘭道:
“手好膩,替我端盆水來好嗎?”
“好啊。”阿蘭雀躍地往殿外行去。
瞧著阿蘭的背影,旋即起,也往殿外而去。
縱是日頭正盛,王庭的樹影憧憧間,猶見冷。慢慢走著,偶有婢見到,也都俯行禮。
這種行禮帶著敬重,敬重的覺該是很多人所夢寐的,于,能說不喜歡嗎?
除了喜歡呢?
還有抑吧。
足下的路,該是母親也曾走過的,如今,母親不知道在哪里,王府的安危亦在顧不得,徒留下,迄今,或許還在被利用的一人。
尖聲再次響起,這一次,聽清了方位,遂喚了守于一旁的侍衛:
“那邊,是什麼地方?”
“回族長,那邊——那邊是韶華殿。”
一指那名侍衛:
“你,帶我過去。”
“可,族長,風長老吩咐,不許讓人進韶華殿。”
“帶我過去。”
只再說出這四個字,那侍衛不敢多辯、畢竟,眼前的子,是他們的族長。
韶華殿,倚竹林而建,十分清幽。
可,喜歡清幽居的人,未必真的是好這出風雅。
一如,曾經巽國的太后,只在香爐薰蘇合香,不過是抑一些念罷了。
明白這點,所以,對于伊泠今日的結局,雖沒有憐憫,然,也做不到心狠置。
守殿的侍衛見到來,本來仍有所猶豫,卻被眼底的一抹威儀所迫,也悉數忽略風長老的命令,開啟殿門。
Advertisement
殿,冰塊灑了一地,融化開,蜿蜒出冰水,伊泠就坐在這并水上,瞧見夕,艷的臉上浮出一抹鬼魅的笑意:
“想不到,我的尖只引來了你,我尊貴的族長大人。”
“除了我,你想引來誰呢?”
夕小心翼翼避開蜿蜒的冰水,站在殿一稍稍干燥的地方,居高臨下地瞧著伊泠。
知道伊泠定是知道風長老回來了,又在王庭,才發出這樣的尖聲。
沒有引來他,伊泠自然是失的。
畢竟,明日就是的加冕儀式,也意味著對伊泠會有最后的發落。
“當然不是你!你不過是個冒牌貨,我引你來做什麼?”伊泠的語氣依舊帶著不屑,“難道你以為,你真的握住了苗水族的實權?我告訴你,你的小腸只會和我一樣,完全一樣,我算是想明白了,那個男人要的,遠不止金真族,他要的更多!他知道,只有苗水族的旗號,才能讓金真族的各大部落真正的歸順!”
“是麼?:夕容不驚,瞧著坐在地上的伊泠,緩緩道,”那你坐在這冰水里,難道,以為他會因憐惜你,改變他的想法麼?”
“告訴你,你都不明白,你這樣的淺的冒牌貨,我憑什麼告訴你,我和他的事呢?從六年前,木長老帶他來到這里,他對我,肯定是有所不同的,只不過,彼時,我還不是族長,或許,他真的喜歡,我不是族長時的樣子,所以,我和你完全不同的!”
夕瞧著,的話聽起來,語無倫次,卻,著另一個味道。
“六年前,你才認識他,對于他,你又了解多呢?”
“我怎麼不了解,哪怕,這幾年,他待在青寧的時間很,可,有一回,也是夏天,我發脾氣,摔了冰盆子,喏,就和現在這樣,我的腳踩到融出的冰水一,他就出現在我的后,把我扶起來,別看風長老從來不笑,其實,他對我,真的很好啊,我為什麼要聽信別人的話,和他對著干呢?如果,我不去派人劫了他的食,如果,我不去設下那些狼群,如果,我不在王庭設下埋伏,是不是,一切就會不同呢?呃?”
伊泠說得越來越快,越來越急,隨后,的臉上清晰地落下淚水來。
能流淚,其實,真的很好。
夕著,口中的“別人”是誰呢?
或許,這個答案,很快,就會浮出水面。
“如果,我的父親是兄長,那麼,我就是嫡系,如果我是嫡系,苗水族就會復,那麼他應該就會按著族規娶我,為什麼,不過是一個嫡庶之差,人和人之間就要這門不同呢?”
伊泠止不住地哭泣,漸漸,口齒開始不清,所以停止了訴說,只低垂下臉,泣的,肩膀都在聳。
夕走上前,蹲下子,細細地看著伊泠,倘若說,這世上,還有一些親人的話,眼前這位,伊泠就是。
所謂嫡庶,不過是長的差別罷了。
倘若,的母親有兄長,那麼,按著族規,的母親不也是庶系嗎?
“是,就一字之差,人和人之間就這麼不同,就像他是長老,你喜歡他,是喜歡他的人,還是他的份呢?”
夕取出帕,遞給,一怔,還是手接過,捂住猶在流淚對的眼睛。
“從你的話里,你和他相時間并不多,他對你關心的次數,恐怕也是屈指可數的,而,他的樣子,一直都掩藏在面后,你連他是否笑過,或許都不知道。
夕的手輕輕扶起,的子很僵:”伊泠,其實,嫡庶二字,真的不能說明什麼,只是,你自己心里一直把這庶系看得太重了。如若不是你心存自卑,不會希,通過得到什麼來證明自己。一如,我說的,你喜歡的,到底是他這個人,還是他的份,是永遠不會變的金真族長老呢?你以為嫁了長老,族長的位置才會更穩,對嗎?“
伊泠著夕的目驀地變得迷離起來,的子順著夕的手,慢慢站起:
“我好擔心,好擔心明日的發落,是他親手殺了我。我不要他親自下這樣的命令,我其實,真的,對他是喜歡的,如果,一定要殺我,你可不可以答應我,由你來下這個命令,可以嗎?”
伊泠說出這一句話,停止流淚的眼睛里,沒有恐懼,有的,僅僅是憂慮。
,難道真的喜歡那個男子,不因為份,不因為其他嗎?
或許,不過是年的一種執念,總以為,那人是該去喜歡的,那人的份,那人的神,都只化作時的執念。
所以,用各種方法去贏得他的注意力,哪怕,帶著對彼此的傷害,都要那一人注意到自己。
可,未必是喜歡,即便到了現在,不愿意由他來發落,不過,是出于對心底,那份執念的維護。
僅是這樣,罷了。
許是坐的太久,突然起,說完這句話,的腳一麻,子就往夕上倒去。
夕扶著,撤手不及,眼前要到跌下去。
一只有力的手說時遲,那時快擋住夕搖搖墜的后背,能覺到,手心的暖融,著不算薄的披肩,一并融了進來。
記憶里,那人的手心,總是冰冷的。
一如,現在的手心一樣。
為什麼,又想起他呢?
閉上眼睛,睜開的剎那,看到伊泠的眼里有著煙火閃現,不過一瞬,恢復清冷:
“風長老。”
伊泠喚出這三字,怯怯地掙開夕扶住的手,繼續道:
“風長老,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
“回去吧。”風長老的聲音在吸煙的耳邊響起,復對伊泠,“一個人,若自己都不惜自己,那麼,沒有人會比自己更惜。”
這句話聽上去很冷冽,實際,卻是對的。
自己的,惟有自己去懂得惜。
伊泠似乎說了一句什麼,又似乎,不過是的囁嚅。
,真的喜歡的,僅是風長老的份嗎?
的手拽著夕的帕,著風長老扶著夕離去的背影,心里郁堵的地方,終是嗆出了一種悲傷。
回,出殿的剎那,夕問了風長老一句話:
“明日,你準備怎麼發落?”
“謀逆之罪,最當誅,留下的命,已是最大的限度。”
“不過是了人唆使,若要追究,幕后的人,焉能幸免?”夕說出這句話,眸華若有似無地瞥了他一眼,復道,“就把發落到偏遠的部落去吧。是伊氏的庶系,我不希,伊氏的人,在拘謹里過完這一輩子。”
風長老知道,夕這一睨的意思,除了沉聲應允外,他沒有做任何的反對。
此刻,不知道,是不是夜深了,一陣風吹過,夕突然覺到,的子一陣的發冷,這種冷,似乎不全是從外沁,而是從心里蔓延出來,一點一點的,滲進里,然后帶到全的,讓每一,都冰冷起來。
下意識地了子,加快步子往金凰殿走去。
心地泛起不祥的預兆——
這,難道就是毒發麼?
不要讓人看到的弱,尤其是風長老,否則,他一定不會容許保下腹中的孩子。
越走越快,風長老形微,卻是阻到的面前:
猜你喜歡
-
完結3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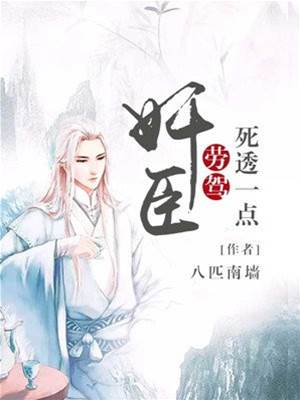
奸臣,勞駕死透一點
蘇問春五歲時撿回來一個臟兮兮的小乞丐,十年后小乞丐踩著蘇家步步高升。春風得意之際,蘇問春伏在他腳邊求他為蘇家討個公道,只得他兩個字:活該!后來蘇問春受盡酷刑著牙闖出一條血路終得平反。兩人尊卑顛倒,他一身囚衣坐在死牢,卻是一臉繾綣:“不是一直…
70.1萬字8 6505 -
完結823 章
棄妃無雙
天道好輪迴! 長平伯府那臭名昭著水性楊花的歹毒小姐,要嫁給困頓落魄到不得不入贅的鄰國質子,滿京城誰人不道一句般配! 質子私逃,伯府獲罪,惡小姐被沒入掖庭宮中為奴,拍手稱快者數不勝數! 可一轉眼,這惡小姐竟搖身一變,改嫁新帝,憑藉不知什麼狐媚手段,當上了一國貴妃,手握鳳印,執掌六宮。 再轉眼,新貴妃清君側有功,母儀天下!
111.8萬字8 7342 -
完結198 章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200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