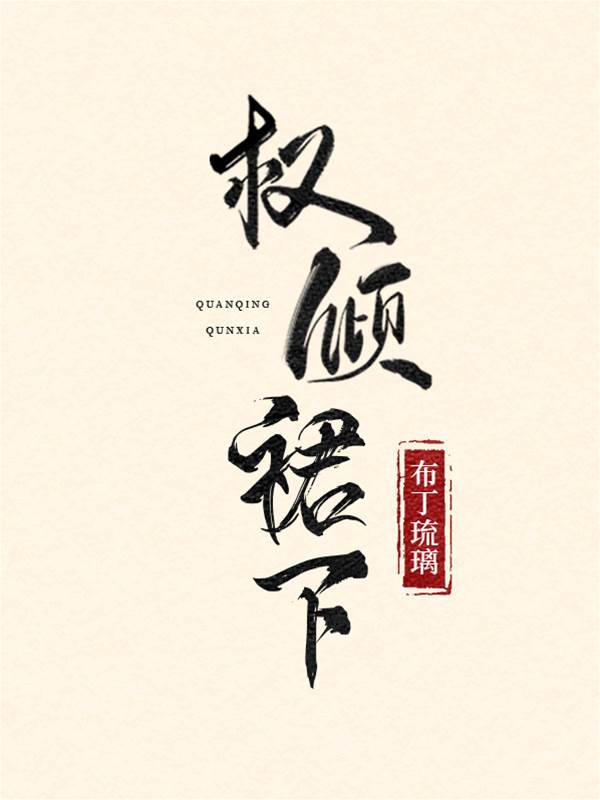《我的相公是廠花》 第十六章
蘇宓開幃簾時,秦衍正閉著眼假寐。
他單手支在紫檀木幾上,撐著額角,袖半褪在手肘,出的手臂理分明,泛著如玉澤。
蘇宓一邊留心秦衍那的靜,一邊尋了車門口的位置輕輕地坐下,生怕擾了他。
但是再輕,還是有些聲響,秦衍倏的睜開雙眸,看向聲音傳來的蘇宓那,恰好對上了小心翼翼地眼神。
“督主好。”大抵是剛剛在屋時候與其他秀爭論了幾句,的聲音有些沙啞。
秦衍眉頭幾不可聞地皺了一下,“嗯。”
早在陳恩來找馮寶時,秦衍便已經醒了,方才只是閉目養神罷了。他收回手,捋了捋袖袍,慵懶地向后靠在墊上,垂眼看向蘇宓。
“蘇姑娘,這是第三次了。”他朝蘇宓說道。
秦衍說的簡單,但蘇宓一下子便聽懂了,他幫了三次了。
第一次是中了藥,第二次是選秀,還有這次,差點沒有車馬上京。
每一次都那麼剛剛好,巧合的好像都是誰故意安排的。蘇宓不傻,秦衍曾問過是何人派來的,甚至不止一次地提過崔知府。想來,他應該是誤會了什麼。
“督主,我真的不認識崔知府。”也真的都是湊巧,可他大概不會信吧。
不知道為什麼,蘇宓就是不想秦衍覺得別有所圖,因此才會執意地,此地無銀三百兩地再提一遍。
蘇宓是神如常地解釋,可耳后的紅卻因著座椅的錯位,盡收秦衍的眼底。
Advertisement
“其實你與崔滿秀認不認識,我并不在意。”秦衍的手半搭在墊上,笑的隨意。
這三日,他已讓陵安重又去查的清楚,并不是他在意蘇宓是不是崔滿秀送的。
而是他的習慣,將人放在邊之前的習慣。
他想留在邊,能讓他高興的人,他當然要留在邊。他要的是查清的底細,至于遇到他是不是巧合,反正也到他手里了,還有什麼區別。
“不過,給你個什麼份好呢?”秦衍看著蘇宓,輕聲自語。
他的聲音太低,蘇宓沒聽清,只聽得‘什麼份’四個字,便以為秦衍在問世。
這也不算什麼,蘇宓決定如實回答。
“督主,我住在江陵城南,家里做的是綢緞莊的生意,上頭還有一個嫡姐,就是酒樓那日遇到的那一個。”
蘇宓垂頭認真地將自己的事稍微說了一遍,等說完的時候,對面依舊毫沒有回應,抬頭看向秦衍。
他也正看著,畔的弧度明顯,笑意灼人。
***
徐州離京府不遠,中途便不再停靠驛站。
蘇宓為子,雖然有些不便,但總的來說,還是比在騾車里舒服了許多。秦衍似乎在想一些事,并不多言,蘇宓自然也不會沒話找話。
就這樣,在離京府還有半日的車程之時,馬車外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馬車也應聲停了下來。
“督主,方才刑千戶飛鴿傳信而來。”陵安騎在馬鞍上,冷冰冰一張臉在馬車外喊道。
Advertisement
“何事。”
蘇宓不知道外頭是誰,但這種時候,是不是該回避,以防聽到什麼不該聽到的?只是微微起了,秦衍朝眼神上下一逡,蘇宓奇異地明白了他的意思,馬上重新安份地坐好。
“督主,前月逃獄的幾名犯人被抓回來了。”
“嗯,既然這麼逃,就將腳筋挑了吧。”
蘇宓低頭聽到這里,心里一,其實逃犯懲罰,自然能理解,的是秦衍說這話時候,那云淡風輕的語氣,和傳聞里心狠手辣的東廠廠督忽然就重合了起來。
第一次是因秦衍獲救的,因此對著他,總會不自覺地將他當作恩人,也就時不時會忽略他的份。可實際上,他從來都是那個本得罪不起的人,想起自己偶爾不怎麼恭敬的舉和話語,蘇宓心里突然有些七上八下。
上一次,他好像便是生氣了,帶給他那麼多麻煩,他讓選,是不是想以后再找算賬。
車外的陵安聽到秦衍意料之中的回答,依舊掛著一副冷漠的臉。
“督主,那挑斷幾條?”
秦衍看了眼不知為何離他坐的愈遠一些的蘇宓,難道是被他的話嚇到了,可他要挑的又不是的腳筋,怕什麼。
“就一條吧。”秦衍仁慈地說道。
“是。”
馬車緩緩恢復前行,可蘇宓的心思卻是千回百轉了一圈,決心一定要謹記秦衍的份,絕不說出任何惹怒他的話來。
Advertisement
在蘇宓的膽戰心驚了半日后,馬車終于到達了京府。
明殷朝的京府為應天府城。青灰的城垣橫亙綿長,六座城門分布在四個方向。
秀們的騾車從州江南而來,是以進的是南城門,秦衍的馬車在進了城門之后,便不再等那些騾車,而是徑直地往宮城門口駛去。
宮門口的石板路上,馬車逐漸停定。
“民多謝督主。”蘇宓恭恭敬敬地說道。
“嗯,馮寶會吩咐門口的宮人,讓他們帶你先去元殿。”
蘇宓在不夠高的馬車里又認認真真地福了一個,這才轉過,彎腰開車門的帷簾。
等到了馬車座的的前板上,有些傻眼了。
秦衍的馬車是兩騎,比單騎的要高上許多,他的量頎長,下來便是一步的事,可為子,一步顯然做不到。
上馬車的時候,馮寶替拿了驛站的椅凳,然而現在,看了一眼馮寶拉著車夫,似乎在宮門口代宮人事,也不好開口喊人來扶著。
噢,可以先坐下來,再跳下去,那大概能稍微緩上一些。
蘇宓正猶豫之間,后好像靠近了一個人,不用想也知道,車上除了秦衍,又還能是誰。
此時是微微彎腰,筆劃著離地面的距離,本就圓潤的部更顯翹,脊背纖瘦往下畫出的弧度格外人。
蘇宓腦中勾勒了自己現下的‘不雅觀’的模樣,秦衍上的檀香氣一陣一陣地昭示著它的主人就在的后很近很近的地方,臉上不由得一陣燥紅,心急之下就想直直跳下馬車。
Advertisement
誰知才做起姿勢,只覺腰間覆上了一只有力的手,一息間便被向后拉進了那人懷里,合著后背的膛溫熱,竟是被后的秦衍直接攬腰勾了起來。
然后便是下一輕。
“啊——”
蘇宓沒忍住一陣驚呼,回過神來,已經被秦衍帶到了石板地上,腰間瞬時沒了支撐,晃了幾下站穩,往一側看去,秦衍已經轉走向宮門,褚的曳撒勾勒出他頎長的背影。
的耳邊灼熱,仿佛還停留著他的氣息。
“太慢了。”他說。
猜你喜歡
-
完結140 章

公府嬌娘(重生)
顏熙去臨縣投靠舅父,被舅父舅母做主嫁給了衛家三郎衛轍。衛三郎生得豐神俊朗、英姿挺拓,猶若一朵長在雪巔的高嶺之花。雖然看著清冷孤傲不易親近,但顏熙卻一眼就相中。只是衛三郎不是真的衛三郎,而是京都長安城魏國公府世子。因失憶流落吉安縣,被衛家誤認…
51.5萬字8 22629 -
連載3516 章

醫毒雙絕:腹黑魔尊賴上門
她,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一朝魂穿!她成了沐家的廢物醜女大小姐,從此,廢物醜女變成了絕色頂級強者,煉丹!煉毒!煉器!陣法!禦獸!隨手拈來!神獸!神器!要多少有多少!可是誰能告訴她,這個人人談之色變,不近女色的魔尊,為什麼天天黏著她,還對她精心嗬護,體貼備至……
282.6萬字8.18 638205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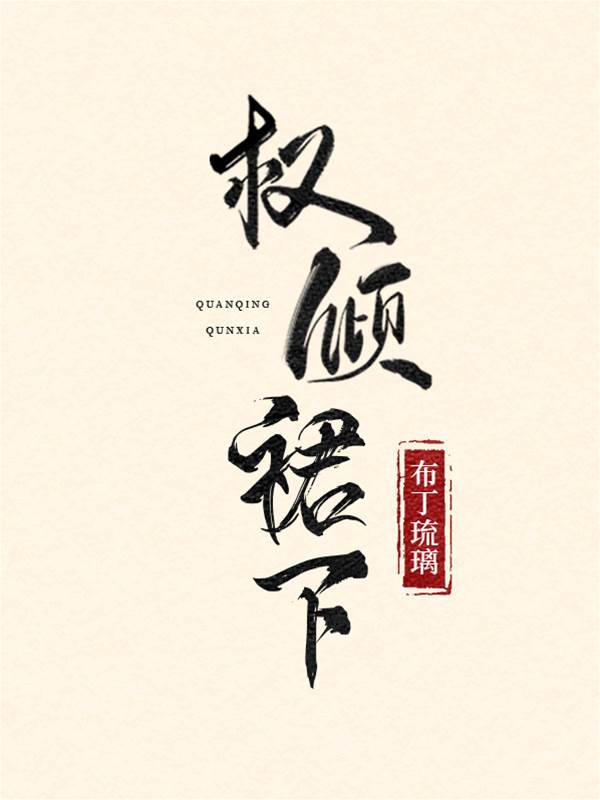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2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