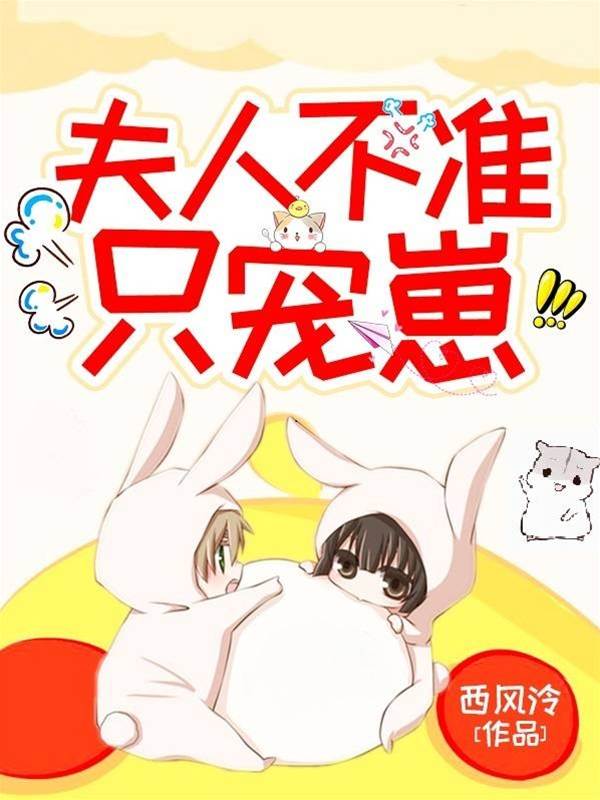《陸醫生他想談戀愛》 第9章 檢查牙齒。
簡卿像鴕鳥一樣埋進碗里吃飯,一聲不吭。
在停下筷子以后,陸淮予也放下了筷子,主地接過收拾的工作,“我來洗碗吧。”
眠眠跳下兒椅,一溜煙兒地就想跑,被他提溜起來,“去刷牙。”
小家伙雕玉琢的小臉糾一團,知道刷完牙就要面臨著被檢查牙齒,嘟著撒地說:“我不想檢查牙齒,我的牙齒很好。”
“不行,忘了你答應我的了?喝了可樂就要檢查牙齒。”陸淮予好看的眉心皺起,低頭看,語調雖然溫和,卻著不容商量的堅決。
“那姐姐也喝了可樂,為什麼姐姐不用檢查?”眠眠聰明地找到了辯駁。
陸淮予看一眼坐在椅子上乖乖巧巧的小姑娘,薄輕抿,“那你帶姐姐一起去刷牙,都要檢查。”
“???”
咬著吸管喝下最后一口冰可樂的簡卿眨了眨眼睛,腦袋上冒出一個大大的問號。
對上陸淮予帶著威的眸子,眠眠反抗無效,只能拖著的尾音識趣地屈服,“好吧。”
小家伙扯了扯簡卿的角,“姐姐,你跟我來。”
于是就這麼懵懵懂懂地被拉去衛生間。
陸淮予替找來新的洗漱用品,趁小家伙刷牙的功夫和解釋,“抱歉,眠眠的牙有些齲壞,需要定期檢查齲壞程度,但總是不肯老實看牙,麻煩你配合我一起哄孩子了。”
他的聲音低啞徐徐,謙和有禮,宛如山間醴泉清冽徹。
“沒關系。”簡卿搖頭表示并不介意。
等們刷完牙,陸淮予也收拾好餐桌,從廚房走出來,襯的袖口被他卷起,出冷白修長的手臂,線條致結實,沾著漉漉的水珠。
陸淮予從玄關的柜子里取出銀的金屬藥箱,藥箱的正面著紅十字標志。
Advertisement
他低著頭,在藥箱里挑揀,找出一個小小的手電筒,兩包一次口腔械,和藍的用手套。
眠眠在沙發的角落里,像是在等待刑,盯著陸淮予的一舉一。
隨著男人的腳步越走越近,越來越害怕,把整個腦袋都藏進了靠枕里,撅著個小屁,好像這樣就看不見一樣。
簡卿坐在一旁看著小家伙的反應,忍不住被逗樂,拽著的小短把人拖出來,“有這麼嚇人嗎?”
“你們誰先來?”陸淮予淡淡地問。
眠眠蹬著,趕說:“姐姐先,姐姐先。”
陸淮予挑眉看向簡卿,眼神詢問的意見。
簡卿看小家伙實在是害怕,決定讓再躲一時,“要怎麼做?”
“躺到沙發上,頭枕在這里。”陸淮予扯過蓋住眠眠的靠枕搭在沙發的扶手。
簡卿聽話地照做,躺著的姿勢讓有些拘束和不適應。
一次口腔械盒的包裝紙被緩緩撕開,發出‘刺啦’的聲音。
眠眠渾一抖,跳下沙發,一溜煙地跑回了房間,只留下一句,“姐姐看完再我。”
然后‘砰——’地關上了門。
“......”
躺在沙發上的簡卿有些后悔幫這個沒良心的小家伙。
雙手疊,不安地著手指。
“張什麼,你也和眠眠一樣害怕被看牙?”男人低低涼涼的聲音傳耳畔,帶著三分的揶揄。
簡卿扭過頭朝他看去,陸淮予不知什麼時候戴上了醫用口罩。
口罩遮住了他的半張臉,黑的碎發垂落至額前,只出一雙漆黑如墨的眼眸,比窗外沉沉的夜還要深邃。
心臟倏地跳一拍。
“有一點。”老老實實回答。
學校每學年都會組織學生去醫學院的口腔科系免費洗牙,每次簡卿都是拖到最后一天才去,確實不太喜歡冰涼的械在里搗弄的覺。
Advertisement
“眠眠現在看不見,我可不可以不看了?”對著陸淮予小聲地商量。
“不可以騙小朋友的。”陸淮予低垂眼眸,食指漫不經心地撥弄一次口腔械盒,挑出探針和口腔鏡,“放松一點,不會讓你難的。”
他傾靠近,兩人的距離一下子拉得很近。
的臉幾乎是著他的襯衫服,頭埋進他的口。
陸淮予手臂了過來,以一種摟著的姿勢,作間到了彼此的。
男人上淺淺的薄荷香在空氣中蔓延,味道很好聞,簡卿突然覺得房間里的暖氣有些熱。
“張。”他的嗓音淡淡,沒什麼緒,就像是在例行公事。
簡卿看已經到這份兒上了,躲也躲不掉,只能認命地乖乖張。
窗外的雨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停了,客廳里安靜異常。
涼颼颼的金屬械探口中,牙齒的聲音顯得格外清晰。
簡卿睜大眼睛看向天花板和暖黃的水晶燈,不敢看陸淮予的眼睛。
好在他也沒有和對視,只是認真地在檢查的牙齒。
里看得不是很清楚,陸淮予慢條斯理地說:“再張大一點,別。”
簡卿配合地張大,像個聽話,任其擺弄的洋娃娃。
口腔鏡在后牙槽深停留許久,探針反復勾著牙齒窩。
時間仿佛停滯不前,短短的幾分鐘像是度日如年,折磨著的神經。
好不容易男人將口腔鏡撤出,簡卿剛松一口氣,正要作撐起,就聽見陸淮予說:“等一下,還沒好,你有四顆齲齒,我要給你做一下冷測。”
簡卿一聽四顆齲齒,心里咯噔一下。
從前不怎麼關注口腔方面的健康狀態,一直認為的牙齒沒什麼問題,怎麼也沒想到會有那麼多顆蛀牙。
Advertisement
陸淮予去到廚房,從冰箱里找出一小塊方冰塊,裝在玻璃杯里拿來。
“找不到更小的冰了,可能會有點不舒服,難你就舉手。”他重新在沙發邊坐下,戴上薄薄的藍用手套,映出骨節分明,十指修長的廓。
他的語調平緩,舉手投足間都著優雅和專業。
簡卿有一瞬間的錯覺,以為躺在的是南大醫學院口腔科的作臺上。
唯一不同的是,比起醫學生的生疏和糙,陸淮予每一步的檢查都練而又溫和,如沐春風徐徐。
干燥冒著白氣的冰塊被放進口里,著一顆顆的牙齒。
他極有耐心地每挨一顆牙齒,問一句,“覺得到痛嗎?”
簡卿皺著眉去努力痛,最后搖了搖頭。
“這里呢?”
冰塊漸漸往深移,朝右下第七顆牙去,冰塊不算小,又陷得太里,簡卿嗓子里哼了一聲。
察覺到的不適,陸淮予立刻將冰塊撤離,“有口水可以咽下去,都是干凈的。”
“......”
簡卿聞言閉上乖乖咽了咽口水,清了清被自己口水嗆到的嗓子。
陸淮予左手拿著手電筒和口腔鏡,右手用鑷子夾著冰塊,也不催促,就在旁邊靜靜等著重新把張開,繼續進行冷測,直到每一顆牙都被檢測過遇冰是否有痛。
終于他將所有的械放回托盤里,摘下手套和口罩,推著的背起,遞過去一杯水。
簡卿接過水杯小聲道謝,耳泛著紅,有些發燙,假裝若無其事地將手指發間,撥出碎發遮住。
小口地抿著水,不安地詢問他,“我的牙怎麼樣呀?”
陸淮予看小姑娘張兮兮的表,忍不住輕笑逗,“現在知道擔心了,剛不是還不想讓我檢查嗎?”
Advertisement
他走到客廳的一角,在眠眠的玩堆里翻出一面帶柄的鏡子,“躺回去,我指給你看。”
簡卿拿著鏡子,乖巧地重新躺平,全程話很,被擺弄著牙齒也說不了話,反倒是平時看起來清冷淡淡的陸淮予話多了起來。
兩個人好像完全演變了患者和醫生的份。
手里舉著鏡子,依靠口腔鏡的反,照出牙齒側面有一個小小的,以及窩明顯的黑。
過鏡子,簡卿清晰地看見陸淮予用探針在小和窩里勾弄了兩下。
低涼清雅的聲音在耳邊響起,像是清風徐徐。
“你看右下第七顆牙,雖然表面齲壞了,但是我用探針去勾,沒有卡住,齲壞的部分黑質地,冷測也沒有問題,說明還是淺齲壞。”
他說著把口腔鏡倒轉方向,對準上牙,“你的右上牙也是一樣,上下左右第七顆牙都是一個問題,明顯的對稱齲。”
陸淮予低頭對上簡卿的眼睛,耐心地詢問,“看清楚了嗎?”
他剛剛摘了口罩,整張臉無遮無擋的映眼簾,高的鼻梁幾乎要上的,羽似的睫分明。
即使是這樣倒著的角度看,也是五深邃,眉骨致,每一線條都著完。
兩人的距離很近,甚至能聽見彼此的呼吸聲,男人溫熱的氣息噴灑在臉上。
簡卿的呼吸有些,說不出話,只能慌張地點頭。
陸淮予將口腔鏡從里再次撤出,不可避免沾了些口水,拉著滴落在邊,晶瑩剔。
他順手出一張紙巾,幫拭。
瓣,隔著略微糙的紙巾,他的指腹溫熱,力道很輕,又很快離開。
猜你喜歡
-
完結143 章

重生之大佬的復仇嬌妻
前世,她受人蠱惑,為了所謂的愛情,拋棄自己的金主,最后身敗名裂,慘死在家里。 重生后,她只想抱著金主大大的大腿,哪里也不想去。可后來發現,金主抱著抱著,好像不一樣,她有點慌,現在放手還來得及嗎? 某天,金主把人圈在懷里,眸光微暗,咬牙切齒說“叫我叔叔?嗯?” 她從善如流,搖頭解釋,但他不聽,把人狠狠折騰一番。第二天,氣急敗壞的她收拾東西,帶著球,離家出走。
34.1萬字5 41505 -
完結968 章

總裁我不要辦公室戀情
一場奇葩的面試,她獲得了雙重身份,工作日她是朝五晚九忙到腳打後腦勺的房產部女售樓,休息日她是披荊斬棘幫上司的生活女特助。 他們說好只談交易不談感情,可突然有一天,他卻對她做了出格的事……「商總,你越線了」 「這是公平交易,你用了我的東西,我也用了你的」
255萬字8 19761 -
完結10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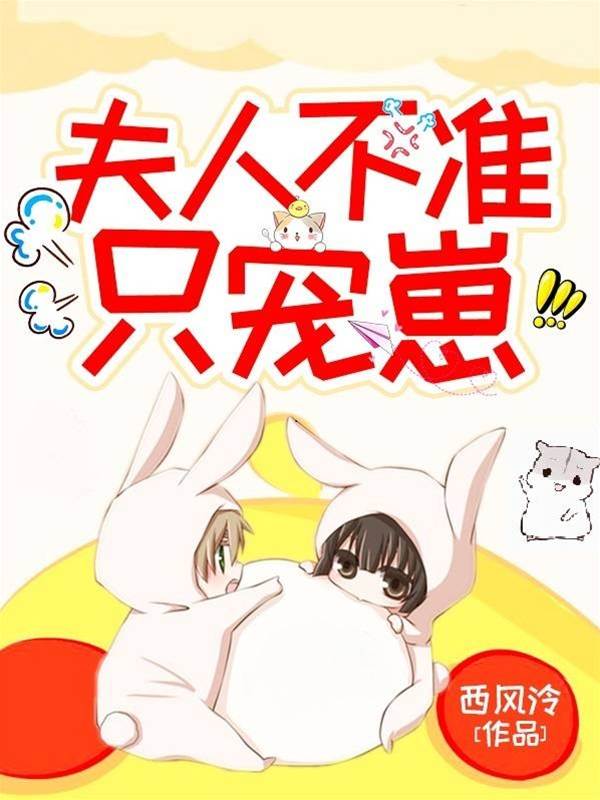
夫人不準只寵崽
南悠悠為了給母親治病為楚氏集團總裁楚寒高價產子,期間始終被蒙住眼睛,未見楚寒模樣,而楚寒卻記得她的臉,南悠悠順利產下一對龍鳳胎,還未見面就被楚家接走。
24.6萬字8 7223 -
完結389 章

炙吻
今年18歲的許芳菲,父親早逝,家中只一個母親一個外公,一家三口住喜旺街9號。 喜旺街徒有其名,是凌城出了名的貧民窟。 許母開了個紙錢鋪養活一家,許芳菲白天上學,晚上回家幫母親的忙。 日子清貧安穩,無波無瀾。 後來,樓下搬來了一個年輕人,高大英俊,眉目間有一種凌厲的冷漠不羈和刺骨荒寒。男人經常早出晚歸,一身傷。 故事在這天開始。 * 又一次相見,是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原,雄鷹掠過碧藍蒼穹,掠過皚皚白雪。 許芳菲軍校畢業,受命進入無人區,爲正執行絕密行動的狼牙特種部隊提供技術支援。 來接她的是此次行動的最高指揮官。 對方一身筆挺如畫的軍裝,冷峻面容在漫山大雪的映襯下,顯出幾分凜冽的散漫。 看他僅一眼,許芳菲便耳根泛紅,悶悶地別過頭去。 同行同事見狀好奇:“你和鄭隊以前認識?” 許芳菲心慌意亂,腦袋搖成撥浪鼓,支吾:“不。不太熟。” 當晚,她抱着牙刷臉盆去洗漱。 走出營房沒兩步,讓人一把拽過來給摁牆上。 四周黑乎乎一片,許芳菲心跳如雷。 “不熟?”低沉嗓音在耳畔響起,輕描淡寫兩個字,聽不出喜怒。 “……” “你十八歲那會兒我執行任務,拼死拼活拿命護着你,你上軍校之後我當你教導員,手把手教你拼組槍支,肉貼肉教你打靶格鬥,上個月我走之前吊我脖子上撒嬌賣萌不肯撒手。不太熟?“ “……” 鄭西野涼薄又自嘲地勾起脣,盯着她緋紅嬌俏的小臉,咬着牙擠出最後一句:“小崽子,可以啊。長大了,翅膀硬了。吵個架連老公都不認了。” 許芳菲:“……”
62.8萬字8.18 159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