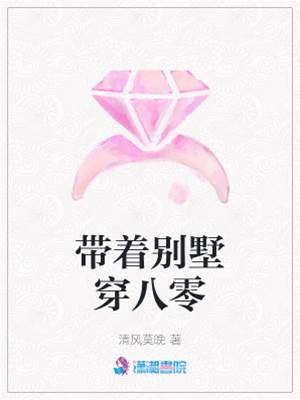《延遲心動》 第17章 晉江文學城獨家 一手就能抓住
倪裳定定看著面前的多葡萄, 一時說不出話來。
被放置過久的冷飲杯上掛滿了水滴,好像一張淚痕縱橫的哭臉。一粒水珠順著杯壁滋溜下,滴在倪裳的指尖上。
沁潤, 微涼。
倪裳的心卻仿佛被燙了一下, 炙出滋滋啦啦的雀躍聲響。
心底似乎也有一小塊看不見的地方, 被溫熱細膩融了……
垂下不堪的長睫,不太敢接對面男人的灼灼視線。
角已經彎出細微弧度,開口卻依舊是悶悶不樂的傲:“這放太久了……都不能喝了。”
炎馳緩慢“哦”出一聲, 刷地站起,一手流暢出車鑰匙:“再去買杯。”
“哎——”倪裳連忙出聲阻攔,一手不由扯上男人的夾克擺, “不,不用了!”
收回胳膊,看著被自己抓出褶皺的角,兩腮慢慢爬上緋紅:“都這麼晚了, 不想喝涼的了……”
炎馳輕笑了下:“行, 那喝點兒熱的。”
他重新坐下——直接坐到旁邊的位置, 骨節分明的大手舀出一小碗蟲草牡蠣湯, 遞到面前。
倪裳剛要手接,男人手腕輕輕一移, 又把碗拿開了。
他看著笑, 狹長黑眸輕佻上揚:“喝了‘蟲貴魚蠔’, 就要跟我和好了啊。”
倪裳輕嘁了聲,微微偏頭:“你就是個騙子……”
賭氣時又是扁又是嘟臉的, 不自覺就流出很心的一面。
兩道細長柳葉眉似蹙非蹙,說還休。
落男人眼里,簡直就跟個委屈小媳婦兒似的, 多看兩眼心都了。
炎馳眼尾彎了下,將湯碗輕輕放在面前:“我怎麼就騙子了。”
他邊玩味勾起來:“是騙你了還是騙你心了啊?”
Advertisement
倪裳:“……”
他又開始煩人了。
眼看孩那眼神小鉤子一樣嗖嗖過來了,男人低笑了下:“真沒騙你。”
他斂眉正:“我也是今天過去見著你,才知道你居然是老宅那邊的。”
倪裳睫尖了下,神松:“真的?”
男人輕闔眼皮,無聲確認。
倪裳想起江漁“原地結婚”的玩笑,還有那句“月老都牽不出這樣的巧合”,心中悸快跳兩拍,又涌起麻麻的。
“哪里會有這麼巧的事啊……”
炎馳悶笑了聲,深深看一眼:“所以我說,擱古代,天王老子都要給我們證婚的。”
天作之合,金玉良緣啊這是。
倪裳:“……”
倪裳橫了男人一眼,目幽幽的:“那你當時為什麼不立刻告訴我?”
炎馳輕呵出一聲,一條胳膊吊兒郎當搭上椅背。
“當時想,不好長時間沒見了麼,一上來就說鬧心事兒,多影響。”
倪裳臉上又是一臊,極小聲嘟噥:“誰跟你有啊……”
炎馳扯了下角,眼神向面前的湯碗示意:“先吃,邊吃邊說。”
這是要說正事了。
倪裳拿起湯匙,舀起一小勺“蟲貴魚蠔”,低頭抿了口。
別說,雖然這湯的名字很糊弄人,但味道還真不錯。
口味偏甜,鮮香濃郁,有點像西式的油湯,還能嘗到白葡萄酒的味道……
一直等到碗底快空,炎馳才緩聲開口:“有個事兒,先跟你說下,這個項目我是年中才接手的,最開始去你們家的那幾個人,說話做事好像都不客氣了些?”
倪裳看了男人一眼,不置可否。
炎馳扯過那盤‘荷好雛’,一手拿起刀叉。
“你們前頭那幾戶,之前想多要拆遷款,鬧的……有靜的。他們是把你們家也當那路子的了。”
Advertisement
他下刀分解烤鴿:“我已經理過他們了。搞不清楚狀況,還那樣對老人說話,不應該。”
倪裳垂眸看著炎馳拆鴿。男人頎長的指輕易鉗控刀叉,下刀利落又莽,用力時手背上鼓起掌骨和青筋。
又抬眸看他。
他認真談事的樣子跟飆車時好像兩個人,卻又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似的——都一樣的鋒利霸道,言辭強勢。
也一樣很吸引人……
炎馳將盤子推回到面前:“那幾個早該登門致歉的,要老人家不介意的話……”
“不用了。”倪裳搖搖頭,又夾起一塊烤鴿放男人盤子里,“不介意,但也不想再在這些事上花時間。”
炎馳點點頭:“行。”
他看了兩秒,又問:“那,你們這段時間一直在拖延時間,是想讓文局介吧?”
倪裳手中的筷子一頓。沒想到他會這麼直接。
放下筷子,也直接道:“文部門關注我們家有一段時間了,定資質的事是早晚的事。”
炎馳輕“哦”了聲,突然轉了話題:“你們不想要錢,一心只想保房子,是對這棟老宅有?”
倪裳緩慢點頭:“這棟老宅,是我們家的祖宅,是我太爺爺的師父建的。”
“我太爺爺是個孤兒,太師父對他有知遇之恩,也有養育之恩。所以太師父的這棟老宅,對于太爺來說非常重要。”
炎馳眉心擰了下,像是想起來什麼:“你太爺爺是不是就是那位……”
“倪向黎。或許你聽說過他,前兩年電視臺還專門過來給我太爺爺拍了一部紀錄片,名字《最后的旗袍大師》。”
倪裳輕描淡寫著,語氣里也有些自矜的驕傲:“我們家四代人,都是旗袍手藝人。”
Advertisement
炎馳黑眸中閃過訝異,很快又是了然。
怪不得。
這樣一來,那條朋友圈就解釋的通了——還真是“霓裳有”啊。
男人的視線又從孩領上的盤扣轉到袖口緄邊。
也怪不得,能把旗袍穿得這麼有韻味,渾然天的。
家族傳承啊……
倪裳拿起手邊的茶杯抿了口,娓娓道來:“我們家四代人,也都在這棟祖宅里長大。老宅對于我們,絕對不單是一棟房子,更像是——”
柳眉微蹙,努力尋找合適的措辭:“大概也像是,一個親人……”
祖宅是有生命的,他們四代人的迭便是它的年,他們的生老病亡也變它的一吐一息。
就這樣,百年老宅也為一位包容的長者,是他們的居安之所,更是心歸之。
倪裳了下腕間的玉鐲,輕聲繼續:“我太爺爺活了96歲,做了80多年的旗袍。他這輩子除了5000件旗袍外,留下的,也就只有這棟老宅了。”
茶的眼眸慢慢垂斂,聲音也更低:“我太爺爺是個很純粹的手藝人,臨終前留下言,讓我傳好旗袍的手藝,守好家里的老宅子。其實當時我也不懂為什麼太爺對老宅這麼執念,現在我才明白。”
抬頭,雙眸明潤而堅定:“老宅,從某種程度來講,也是一位見證者,見證了旗袍的從生到興,又從興至衰。太爺爺想讓我留在老宅里做老手藝,大概也是讓我——”
“居此,明其志,風尚來回,匠心不改。”
炎馳眼中一震。
他認真看了孩幾秒,眸很深:“我明白了。”
倪裳也抬眼看他,眼中有盼,也有期許:“那……”
男人默了兩秒,一下子又把話題拉了回去:“文局的什麼時候去你們家?”
Advertisement
倪裳猶豫了下,回答:“最遲下周吧。”
男人若有所思,搭在桌沿上的指節輕點了兩下。
“拋開拆遷的事兒,我客觀說一句,你們的老宅,可能定不上文資質。”
倪裳睜大眼睛:“……怎麼會?”
“我今兒大概看了圈,宅子呢,確實是古董老宅,就是——”男人頓了下,起眼皮看,“留下來部分的太了。”
倪裳眨了眨眼,明白過來。
老宅到現在,保留下來的部分,大概只有當初建造時的十分之一……
“你們家這樣的,其實已經算保存很好的了。但沒辦法,古董這玩意兒,缺一個角多一個豁,就不是原來那意思了。”
看孩眼睛失落低垂,炎馳了下胳膊:“等文局去那天,我也過去。”
倪裳有些意外地看他:“你來做什麼?”
“牽涉到拆遷,就跟我有關系。”男人理直氣壯道,他舌尖頂了下腮幫,黑眸很慢地眨了下,“我還有個想法……”
“什麼?”倪裳問。
覺得,或許老宅的轉機,就在這里了。
但炎馳又淡淡撇開話頭:“到時候再說。”
倪裳沒再追問,又給自己盛了半碗和好湯。
這件事,一下子本來就不可能談清楚。
而今天的談話就算結束了。
比想象中的輕松許多——之前預備的如臨大敵,渾扎刺的狀態都沒派上用場。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們的關系正朦朧曖昧,并沒有覺男人站在自己的對立面上。
又或者,他本來就是個談心的高手。
家庭熏陶的緣故吧,他就算不去賽車,應該也是塊經商的料……
談判的兩個人都說了,桌上的那只原諒牌烤鴿很快被瓜分干凈。對于倪裳的小貓胃來說,今天絕對算超水平發揮。
孩餐后拿著巾細致的樣子也像小貓自潔,炎馳看得邊慢慢翹起來:“飽了?”
倪裳點頭,放下餐巾,摁桌上服務鈴:“我買單。”
炎馳瞟了眼時間:“還不算晚。”
他站起:“樓下就是商場。”
倪裳不解,眼神詢問。
男人斂目,朝腳下示意:“去給你買雙鞋。”
倪裳愣了下,低頭看鞋面,瞥見蕾上的污黑,又趕往后。
“不用。”有點不好意思,“鞋又沒壞……”
“換雙平的吧。”炎馳說著,角又勾了下,“一會兒你再摔了,老子還得抱你。”
倪裳橫他一眼,耳臊熱:“誰要你抱了啊!”
男人低低笑了下:“又不是沒抱過。”
倪裳:“……”
包廂的門被敲響,服務員推門走進來。不是剛才上菜的那位,看制服,應該像領班或者經理。
微笑看向炎馳:“二爺,您還有什麼需要嗎?”
倪裳微怔。
二爺?
“有。”炎馳懶散散道,“還要一雙平底鞋,好穿好走不磨腳那種。”
倪裳有些赧然地看了眼經理,一手扯男人袖口:“我都說了不用……”
“沒問題。”領班看了眼倪裳,笑眼更彎,“買多大碼的呢?”
倪裳:“……”
見抿不說話,炎馳挑了下眉:“大概——”
他一只手掌攤開,似笑而非:“我一手正好抓得住那麼大。”
倪裳:“!”
他這是什麼鬼形容!
倪裳的臉紅得不樣子。領班的職業素養驚人,還能面不改地繼續問:“那是35碼半?36?”
很小聲回答:“36就可以,謝謝。”
領班應下,很快轉離開了。
倪裳的耳廓依舊紅得發亮。抿瞪男人。
“又瞪我干嘛?”炎馳慢悠悠問,“我說錯了?”
不等說話,他突然俯下——
“那就再量量。”
倪裳還沒反應過來,一只腳腕就被男人抓住了。
一驚:“你——”
細瘦足踝被男人一手鉗握,撤不,也掙不開,落網之一般由他掌控。
炎馳單膝著地蹲在面前。他形高大,半蹲下來也到口。
稍一垂眸,就看到男人頭皮的寸頭。
發茬又短又,一把估計會扎手。
再往下,是睫在眼窩拓出的濃影,以及走勢峭的鼻梁。
男人收起調笑的神,環腳腕的手掌熨帖蕾,拇指在細踝細致輕按。
再抬眼看時,目認真關切:“真沒事兒?”
“沒事。”倪裳心跳稍快,抬手拍了下男人的胳膊,“你起來吧……”
炎馳依舊蹲著,眉心饒有興致地了下:“看來還真量錯了……”
他猝不及防捉起另一只鞋跟,兩只細脆足踝一下子都被他握在手心。
“我一手就能抓倆。”
倪裳:“!”
“炎馳!”倪裳窘,抬腳就要踢男人,“你——”
流^氓!
男人起后退,輕松躲開攻擊,得逞的輕笑壞頑劣。
倪裳忿忿瞪了他一眼,提起包兀自往門口走。
炎馳抄起外套跟上,低聲:“單買過了。”
倪裳:“……”
倪裳回頭,無奈又無語。
怎麼,這頓飯要欠他一輩子了?
男人無辜揚眉:“你要買也行啊。”
“那多錢?”倪裳從包里拿手機,“我轉給你。”
炎馳也出手機,指尖在屏幕上點了下,調出一個二維碼。
倪裳沒看,直接掃過去。滴的一聲輕響,的屏幕上跳出一張名片——
紅白賽車服的頭像。
怔住,抬頭看男人。
炎馳也在直勾勾看著:“把我微信加回來就行了。”
猜你喜歡
-
完結566 章

顧先生的金絲雀
c市人人知曉,c市首富顧江年養了隻金絲雀。金絲雀顧大局識大體一顰一笑皆為豪門典範,人人羨慕顧先生得嬌妻如此。可顧先生知曉,他的金絲雀,遲早有天得飛。某日,君華集團董事長出席國際商業會談,記者舉著長槍短炮窮追不捨問道:“顧先生,請問您是如何跟顧太太走到一起的?”顧江年前行腳步一頓,微轉身,笑容清淺:“畫地為牢,徐徐圖之。”好友笑問:“金絲雀飛瞭如何?”男人斜靠在座椅上,唇角輕勾,修長的指尖點了點菸灰,話語間端的是殘忍無情,“那就折了翅膀毀了夢想圈起來養。”
159.6萬字8 16339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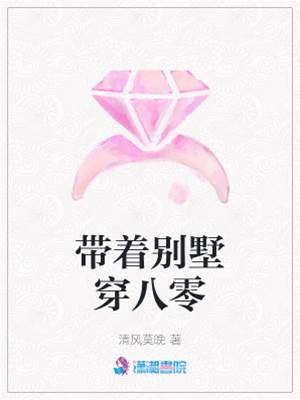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5893 -
連載830 章
厲總,夫人不想復婚還偷偷生崽了
姜彤剛辦理了離婚,后腳就發現她懷孕了。兩年過去,看到這條新聞的姜彤,趕緊藏好了和前夫長得如出一轍的小包子。藏不住了,只能帶著兒子跑路。那個殺伐決斷的男人氣勢洶洶堵在門口,直接抱起她往床上丟。“想帶我的崽跑去哪?嗯?”“我錯了……唔。”-小劇場:很久之后,姜彤去南山祈福,才看到厲璟辰在離婚那年掛在月老樹的紅條。
146.9萬字8.18 144989 -
完結234 章

蝴蝶效應
雙重生 雙向救贖 ----------------------------- 宋郁自縊而亡的消息炸裂在一個普通的清晨,翻涌、龜裂、燃燒了一個月后歸于平息,人們開始慢慢接受這位娛樂圈的天之驕子、最年輕的大滿貫影帝已經逝去的事實。 只有周雁輕,他不相信那個他視如人生燈塔的人會
38.8萬字8.18 24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