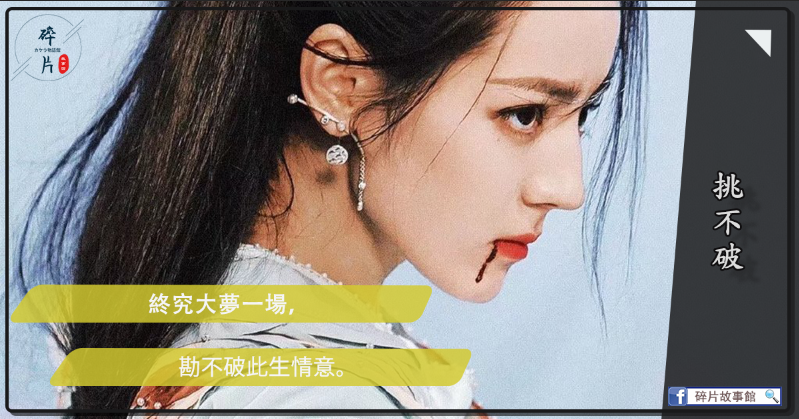《挑不破》第3章
「修煉。」
許是我專注的目光太過灼烈,流淵微微側過頭去,避開了我的注視,
「金丹之上有元嬰,元嬰之上還有化神、合體、大乘……」
「待你修煉至大乘,便可如曾經的若華一般,開啟玄靈秘境,將其中蘊藏的復蘇之氣散入靈界。」
我人都聽傻了。
身為原作者,我都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寫過這種設定。
這里看似是書中的世界,許多細節卻與原文中的設定南轅北轍,更遑論我穿過來時,蘇若華和男主都已經不見了。
到底有沒有真的飛升到仙界,我也并未親眼所見。
這里,到底是不是《仙途》中所描繪的世界?
我還能……穿回去嗎?
我越想心情越沉重,自個兒拿了壺靈酒坐在樹上喝,月光清凌凌地照下來,風拂動樹葉沙沙作響。
沒一會兒,我就有些喝醉了。
這時身邊有細微響動,我偏過頭去,看到鴉川提著一壺酒,神態自若地在我身旁坐下,仰頭灌了一大口。
這姿態的確足夠風流瀟灑,配合他那副漂亮到極致的皮囊,硬生生構造出流風回雪的從容與飄逸。
「你怎麼孤身在此喝酒,流淵呢?」
我將酒壺與他碰了碰,沖他低笑:「身為弟子,若與師尊把酒言歡,豈不是亂了套?」
「那你怎麼就有膽子與我喝酒,莫非覺得我比起流淵,毫無威嚴?」
他也笑,可眼底的笑意就薄薄一層,像是冰面上的霧氣。
原文設定里他與流淵代表了正邪兩道,便十分不對付。
如今我穿進來,才知道這種不對付已經嚴重到,但凡在兩人面前說句彼此的好話,都會令對方不爽。
「不是我覺得你毫無威嚴,分明是你主動來找我的。」
我斜睨他一眼,「你與他既是同門師兄弟,又為何反目至此?」
「……你與她,倒真有幾分相似。」
他望著我,微微出了神,仿佛從我臉上瞧見了昔日蘇若華的影子,
「舊日往事,已不可追,只是后來仇怨互相累積,著實算不清楚了。」
他與我講了幾件事,聽著倒不新奇,都是原文里我寫的劇情,只是由當事人說出來,又多了層奇妙的意味。
酒意浸潤,他又并未用靈力驅散,嗓音里便多了幾分沙啞。
我寫出的癡情男配,自然萬般符合我的審美。
這人生著一張極為出色的面容,下頜線條凌厲,薄唇染了水意依舊是淡色。
偏偏嵌著一雙眼尾狹長的含情目,帶著幾分醉意望過來,總有種深情脈脈的意味。
我邊聽邊喝酒,到最后愈發醉得厲害,鴉川大概也喝多了,竟然問我:
「你這三日在融金洞中,難熬嗎?」
這話問得,狗聽了都笑。
「難不難熬不都得熬過去嗎?」我反問他,「你們親手把我扔進去的,我有反抗的余地?」
他搭在酒壺上的手指忽然輕輕顫了一下。
「其實呢,我這個人挺怕疼的,尚未筑基時會來月事,每次都痛得死去活來。但如果真有重要的、非做不可的事情,我也是能忍著疼完成得很好的。」
我支著下巴,沖他意有所指地笑,「鴉川,我什麼都不怕,逼急了,是痛是死,我都不怕。」
他沉默了好久,忽然伸手攬住我的腰,凌空而起。
「走吧,周容。」
他輕聲說,「逃出天玄門吧,我帶你回魔界。」
6
月色清清冷冷地落下來,鴉川就這樣輕而易舉劃開天玄門精妙至極的護山大陣,帶著我飛了出去。
他隨手掐訣破陣的從容,我看得清清楚楚,在心中默默衡量一番,更確認現在不能與他翻臉。
原因很簡單,因為打不過。
想到這里,我順勢將臉埋進他肩窩,深吸一口氣,低聲道:「……英國橡樹和榛子。」
鴉川沒聽清:「什麼?」
「沒什麼。」
我寫鴉川的人物設定時頗廢了一番心思,就連他身上若有似無的香氣,都是我那段時間最喜歡的香水。
此刻時空變換,虛實流轉,書里的紙片人切切實實帶著這樣的香氣出現在我面前。
我心中忽然生出一種光怪陸離的荒謬感。
鴉川的速度很快,距離原文結局已經過去太久,他的修為步步精進,已經到了靈界第一修士的地步,舉手投足間便可短暫撕開空間,跨空而行。
天亮時,我們已經抵達魔界千余里外的一座小鎮上。
晨間風涼,我們的酒也醒了,重新戴上了彼此熟悉的面具。
找了家客棧住下,鴉川眉尾輕挑,饒有興致地望過來:「容容的酒可醒了?」
「醒了、醒了。」我訕笑,「昨夜我醉酒失控,對魔尊多有冒犯,還望您不要見怪。」
他目光停留在我臉上,似在評估,良久,終于道:
「罷了,容容還是個小女孩呢,本尊又何須與你計較。」
說完,他拋給我一塊極品金靈玉,讓我打坐休息半日,下午再動身去魔界。
我依言照做,結果打坐入了定,等回過神,一眼就看到房間里站著的三尊大神。
鴉川倒還好,依舊是那副慵懶從容的模樣。
流淵卻擰眉望著我,目光里全是冷意。
再看景淮,小師弟紅了眼圈,一臉小白蓮似的表情:「師姐竟要丟下阿淮,偷偷跟他回魔界嗎?」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