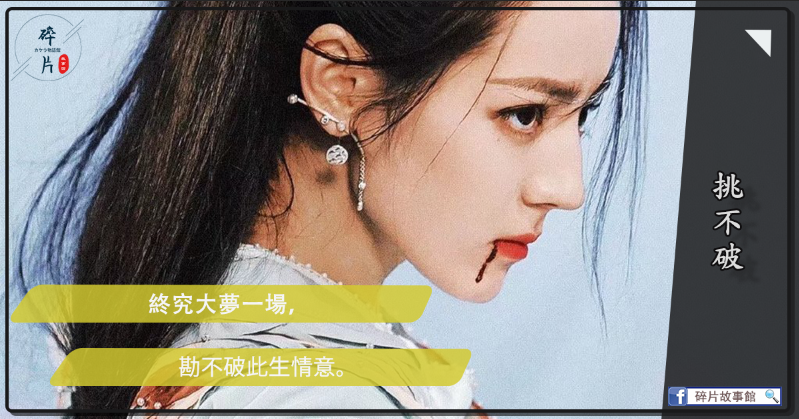《挑不破》第6章
是流淵。
縱然我已經突破至元嬰,在他面前依舊不堪一擊,甚至動一動手指,就可以催動我元嬰上的禁錮。
景淮原本站在一旁,此刻皺了皺眉,制止道:「流淵,夠了。」
流淵冷淡地看向他:「心疼?倘若此刻在這里的是若華,絕不會如她一般。」
提起蘇若華,景淮神色微微一變,卻也沒理會流淵,只是自顧自走過來,將我扶起:「師姐,你沒事吧?」
他面對我時,總是繃直了脖頸,落在我臉上的目光帶有某種示弱的意味。
作為創造他的作者,我當然無比清楚。
原文里他每每面對蘇若華,都是這樣一副乖巧又脆弱的模樣,就是為了勾起她的憐愛之情。
可我到底不是蘇若華,便扶著他的手,望著流淵冷笑:
「師尊既然要我拯救靈界眾生,又為何要在我丹田之中設下這般禁錮?今日不說個明白,我再也不會修煉,就擺爛,靈界跟我一起完蛋吧。」
流淵神色冷極,正要開口,我身后倏然傳來一道帶著怒意的聲音:「流淵,你敢傷我容容?!」
回頭望去,又是鴉川。
他飛身過來,執一柄兩寸寬的細長血紅長劍,劍尖遙遙指向流淵。
這是幻神劍,他的本命法寶。
方才從徹骨冰泉湖出來后,他與我先行分別,說要去對面湖畔取一樣東西,原來是拿他的本命法寶去了。
兩人靜對片刻,流淵冷冽的嗓音傳來:「魔尊要阻攔我管教我天玄門弟子嗎?」
鴉川冷笑一聲:
「周容只是你天玄門弟子,并非賣身給了天玄門,怎麼,你全門派上下還都要求著她,你現在又在這里擺什麼師尊的架子!」
他話說得毫不客氣,說完便將幻神劍一收,反手過來,抓住了我的手腕:「容容,我們走。」
我身上水痕未干,渾身濕淋淋的,連同手臂也是一片冰冷。
可同他相貼的那一處皮膚,卻漸漸火燙起來。
我抬步欲與鴉川同行,身側卻傳來景淮的聲音,帶著一絲細微的顫抖:「師姐。」
深吸一口氣,我回頭望他:
「景淮,我并非蘇若華,也不會吃這套。蘇若華已經同她的道侶飛升至仙界,她對你,從來只有同情憐憫、姐弟之愛,沒有半點風月之情,你不必如此。」
這話說得景淮臉色微微發白,瞳色幽深。
他望著我,眼底掠過一絲無措的兇狠,壓低了嗓音道:「你胡說!」
「其實你心里很清楚,正是因為蘇若華并沒有喜歡過你,所以你才只能靠著賣可憐在她面前占得一席之地。」
作為作者,我自然知道最戳這幾個人心窩子的話該怎麼說。
這句話說完,我收回目光,默默與鴉川一同離去。
飛舟飛至魔界邊緣時,鴉川忽然出聲:「他們一直跟在后面。」
我知道他說的是流淵和景淮:「不用管,由他們去吧。」
細細密密纏繞在元嬰上的靈力禁錮仍無半點松動的跡象,縱然鴉川已經允諾,找到一處金靈石礦脈,便可嘗試著幫我解禁,還能順帶著提升修為,我卻仍舊開心不起來。
「接下來我們去哪兒?」
「金靈石礦脈只在靈界南——」
鴉川話音未落,神情忽然一凜,眼神變得森寒無比。
下一秒,我還沒反應過來,身下乘坐的飛舟便被擊了個粉碎,接著黑氣密密麻麻纏繞而上。
鴉川縱身躍過來,攬著我的腰落在一旁。
「!位面魘鬼!」
一百年前入侵靈界,以至于爆發了位面之戰的,就是此物。
他們形狀不定,通體烏黑,一息間便可散作霧氣,又可瞬間合攏,被籠罩的無論是凡人還是修士,都會被霧氣吞沒,化作烏黑的一部分。
親眼所見此物,我毛骨悚然,下意識想催動靈力,卻想起了丹田中禁錮。
流淵這孫子!
我將手伸進懷里,正要握住流光珠,身畔鴉川聲音響起:「容容,在一邊躲好。」
說話間,越來越多的漆黑霧氣涌上,而后面的景淮和流淵也追了上來,三人皆是一臉凝重。
我自知事態嚴重,趕緊乖乖躲在了一邊,眼睜睜看著他們與魘鬼纏斗起來。
這三個男配,在原文里就是修仙界頂尖的存在,如今數百年過去,修為更是深不可測。
然而他們三個人加在一起,也不過與那堆魘鬼戰了個平手。
我終于知道,一百年前的位面之戰有多可怕,怪不得靈界四處瘡痍,許多原本的靈秀之地,都呈現出枯敗的模樣。
只是……魘鬼不是在一百年前位面結界修復后就該消失了嗎?這些又是從哪里來的?
我心中隱約覺得不安,卻又說不出哪里不對勁。
怔怔然間,忽然聽到了鴉川的聲音:「容容!」
那聲音好似響在我耳畔,又似乎在天邊。
我猛然回神,才發覺身側不知什麼時候悄無聲息出現了一團濃黑的霧氣。
那黑色如宇宙黑洞般,有種未知的巨大恐懼,而我甚至來不及后退,就被它猛地吞了進去。
死亡的恐懼連同刻骨冰冷一同涌上來,我張了張嘴,還沒來得及發出聲音,手腕忽然被一股熟悉的溫熱力道抓住。
鴉川不知如何,竟飛身過來,替我擋下了那團黑霧的致命一擊。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