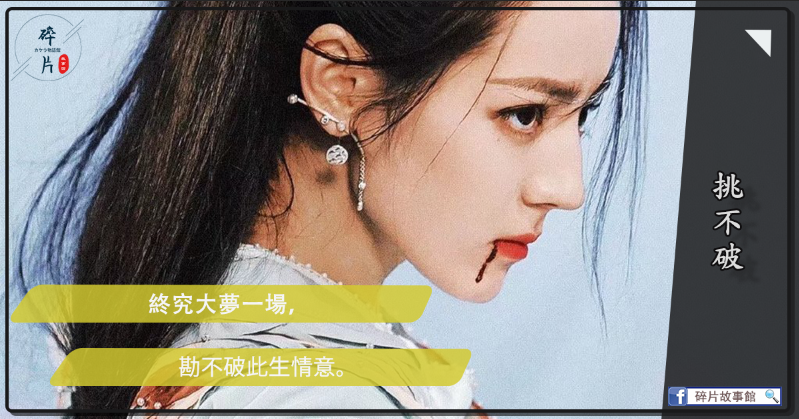《挑不破》第7章
我眼睜睜看著他胸口的血肉被消融掉一大片,而那團黑霧只停滯了一瞬,又不屈不撓地涌了過來。
在它重新將我們吞裹之前,鴉川蒼白著臉劃開空間,帶著我一同跳了進去。
10
我們被傳送到了一片小鎮外的山脈。
從空間裂縫中出來后,鴉川握著我的手無力地松開,向地面跪倒而去——
我連忙扶住他,急聲問:「你怎麼樣了?」
按理來說,像他這個實力的修士,又是魔修,別說傷口,就是斷肢殘身,也能飛速修復回來。
可他胸前缺失的那塊血肉上,仍有絲絲縷縷的黑色霧氣繚繞,似乎正是這股霧氣,阻礙了新鮮血肉的生長。
我又驚又懼:「這就是位面魘鬼嗎?」
「是。」鴉川受了重傷,聲音也比之前微弱許多,「魘鬼沒有形狀,更沒有生命,他們只會吞噬一切生命,化作無生命的自己的一部分。」
這已經不是我原文里寫過的東西了,我對魘鬼僅有的一點了解,還是在天玄門的藏書閣中,找到了一本介紹一百年前位面之戰的科普藏書中提到的。
修士有血有肉,會受傷,會痛,這卻是一群沒有生命的東西,怪不得靈界強大的修士那麼多,還能被摧殘成現在這樣。
我望著鴉川胸前的黑霧:「那你的傷口該怎麼辦?」
「容容是在擔心我嗎?」他望著我,笑得眉眼彎彎,雖然面色蒼白,一雙眼卻艷若桃李,「我真是感動。」
「這種時候了還他媽跟我調情!」
我急得爆了粗口,伸出手去,想試探性碰一下那些黑霧,卻被鴉川躲開:
「別碰,你如今禁錮未解,我又受著傷,倘若這東西真纏上你了,我一時半會兒還解決不了。
」
他神情終于嚴肅起來:
「這只是魘鬼的一小部分,用靈力消解掉便沒事了,只是可能需要小半日時間。」
「這段時間內,還需要容容幫我護法了。」
鴉川拿出一柄匕首型的法寶,遞到我手里:
「你靈力被鎖,倘若真遇到危險,便用這個吧。這法寶能用神魂之力催動,至少能抵御片刻,撐到我醒來便好。」
他頓了頓,咬牙罵道:「流淵這狗東西!」
對這句話,我深以為然。
然而有句話含在唇邊,猶豫了半晌,終究還是沒有吐出來——
「我丹田中的禁錮,當真只是流淵一人的手筆嗎?那日我們一同在房間醒來,你竟對流淵對我下禁錮一事毫不知情嗎?」
我不敢細想,也不能細想。
鴉川閉眼打坐,我將那匕首收起來,從懷中摸出流光珠,細細研究起來。
這是我在原文中留下的最大伏筆,原本是想留在仙界篇寫的,然而坑還沒填完就穿了過來。
在《仙途》的世界觀設定中,萬物皆在五行之內,皆有五行屬性。
唯有流光珠跳出五行之外,沒有屬性,卻在徹骨冰泉湖下埋藏了太久,擁有龐大到驚人的能力,以至于能在催動時短暫地將周圍一切五行力量切斷一瞬。
但倘若是真正的生死之際,一瞬也足夠扭轉局勢了。
我有心想用神魂力量催動流光珠,試驗一下,又怕鴉川發現,打擾到他療傷,糾結片刻,還是暫時將它收了起來。
一直到第二天黎明時分,鴉川的傷口終于痊愈。
我們在小鎮找了家客棧住下,這是屬于凡人的地界,但也有不少修士,在凡人面前擺出一副傲然的姿態。
「本來消失了一百年之久的魘鬼再次出現,也許意味著位面之戰又要爆發了。」
客棧房間內,鴉川設下結界,然后低聲對我說,
「只是如今的靈界元氣大傷,倘若再遇上大批的位面魘鬼,不一定能如百年前那麼幸運了。」
我深吸了一口氣:
「是不是,如果我能盡快突破至大乘期,進入玄靈秘境,將復蘇之氣散向靈界,讓靈界重新振興,還有可能扭轉局勢?」
鴉川遲疑片刻,點了點頭。
我靜默了一會兒,忽然問:
「蘇若華三百年前飛升到了仙界,然而她在靈界留下了不少信物,位面之戰時你們就沒有嘗試過聯系她嗎?她既然已經飛升成仙,應該能幫大忙才對。」
「……沒有,她飛升后,我再也沒有見過她。」
鴉川微微側過臉去,陽光從另一邊照過來,將他眼中的情緒渲染得一片模糊:
「我于她而言,或者她于我而言,終歸只是過客。何況如今她已成仙,我不該再打擾。」
「所以我與她,真的很像嗎?」
我話音剛落,鴉川忽然湊了過來,那張俊美的臉在我眼前漸漸放大,直至氣息也吐露在我鼻息間:
「你與她并不像,只是容容,我的心意變了。」
他的眼尾是微微往上挑的,一貫的漫不經心在此刻,被難得的莊嚴隱沒。
而大傷才痊愈后的臉色微微蒼白,又被陽光照著,呈現出一種奇異的柔和與魅惑。
一瞬間,我的心跳得好快,艱難地吞了吞口水。
他的聲音輕輕的,含著三分笑意,像是落在我心上清脆作響的玉珠:「容容應該能猜到,我的心意吧?」
11
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去找鴉川,告訴他:
「你找一處金靈石礦脈,幫我沖開流淵的禁錮,正好可將我的修為再提升一些,我想盡快突破至大乘期。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