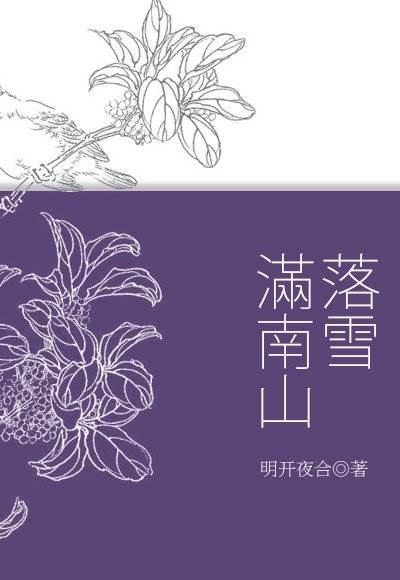《偷風不偷月》 第23章 第 23 章
抵達縵莊, 汽車減速駛北門,在宅院前停下,項明章和楚識琛下了車。
四周線不太明亮, 楚識琛駐足分辨,稀薄的月下樹影婆娑,不到邊際。
他以為縵莊是類似于靜浦的公館, 畢竟項明章的母親一個人住,沒想到是這般幽深廣袤的一莊園。
項明章他:“跟我來。”
楚識琛跟隨項明章踏宅院里, 中式建筑的方正結構,偏現代的新式風格, 沿開放式回廊走到客廳外, 門開著。
里面燈火通明,楚識琛抬手整理頭發和襟, 慢一步進去。
白詠緹坐在沙發上看書, 抬起頭,見來的不止項明章一個人, 不到驚訝。
項明章風輕云淡地說:“媽, 他是楚識琛, 你有沒有印象?”
白詠緹記得楚家有一兒一, 不過上次見面是許多年前了, 楚識琛還小,道:“印象中還是學生, 現在長大人了。”
楚識琛恭謹地問候道:“伯母, 深夜叨擾,實在不好意思。”
白詠緹擺了擺手, 早就聞見項明章上的酒氣, 想起項明章上次來, 提過楚識琛在項樾上班,便猜到九:“是明章讓你加班吧。”
項明章說:“我請他來吃飯,抵加班費。”
楚識琛是客人,去小餐廳顯得怠慢,白詠緹安排他們到寬敞的會客室,一整面落地窗外是石山園景,在夜下別有一番風味。
很快,五道菜上齊,北菇燜蘿卜,茉莉什錦繡球,上湯南瓜苗,中間是甜的梅子鴨和醇香的花雕醉鮑。
總嫌全素不夠味,今天破例多了兩道葷的,項明章姑且滿意,但不妨礙繼續挑刺:“只有菜,沒有湯?”
青姐放下一只小蒸籠,說:“有,解酒湯。”
Advertisement
楚識琛不不慢地著手,心中悉出千萬縷。
這桌佳肴一道比一道細,沒有三五個鐘頭本做不完,提前烹調,說明知道項明章會來。
備著解酒湯,也知道項明章會喝酒。
他們來的途中沒有聯系過,卻這樣了解,只能是習慣使然。大約每年的這一天,項明章為項行昭慶生后都會來陪母親。
蒸籠里鋪著一片荷葉,上面是三只竹笙素餃,白詠緹說:“小楚,吃點面食。”
“謝謝伯母。”楚識琛聽話地夾了一只,咬下一口,“清甜鮮香,很味。”
白詠緹問:“你不嫌素嗎?”
楚識琛說:“我喜歡素一點。”
他并非奉承,平時一直藏真正的飲食習慣,不求口腹滿足,這一餐是他至今吃到最合胃口的東西。
沒多久,餐桌上只余碗筷的聲響,項明章避而不談壽宴有關的事,也不提項家的親朋。白詠緹既不噓寒問暖,對項明章的生活和工作也全無關心。
楚識琛心底納罕,要是換楚太太,一定嘰嘰喳喳聊上許多。
吃完飯,項明章去盥洗室了,青姐帶楚識琛到里面的套間休息片刻。
起居室中,高及天花板的書柜占據了一整面墻,楚識琛掃過,書籍品類紛雜,其中有幾套佛經頗為矚目。
對面的墻邊有一只長形條架,擺著一尊觀音像,楚識琛踱近,明白了白詠緹的淡然疏離是從何而來。
不知不覺得久了,怕冒犯神明,他雙手合十向觀音頷首行禮。
恰好白詠緹進來撞見,好奇地問:“小楚,你信佛?”
楚識琛垂下雙臂:“曾經有長輩希我信,但我做不到。”
白詠緹不意外,說:“年輕人不經風霜,不苦難,自然不會信。”
Advertisement
楚識琛笑了笑,他經過的風霜、見過的苦難,豈是和平年代的人能懂的?
他道:“也許吧,我敬之但不求之,學之卻不信之。”
白詠緹說:“看來你有自己的見解?”
楚識琛一瞬間目深遠,舊日的艱苦景象浮現在腦海中,倘若求佛有用,他用不屈信念、幾世財富、乃至生命爭取的東西算什麼?千千萬萬人拋灑的熱又算什麼?
“談不上見解,淺薄的個人意見罷了。”楚識琛道,“如果庇佑存在,人怎麼會苦?如果不存在,又何必奉若神明?”
白詠緹仿佛被中痛,說:“正是無路可走,所以抓住一點信仰尋求安。”
楚識琛繞回自己的觀點:“擺在這兒不等于抓得住,觀音又觀自在菩薩,不如學其意,得心自在,才是解。”
白詠緹輕聲:“哪有那麼容易解。”
楚識琛從進門就有一種覺,白詠緹樣貌年輕,狀態卻死氣沉沉。
他實在不明白,項明章爭強好勝,并擅長掌控權力,為什麼母親會寡居在遠郊,消極避世。
本不該與長輩爭辯,楚識琛最后一眼觀音:“玉凈瓶的雨不會撒遍大地,普世凡人,終究要靠自己的。”
白詠緹愁忡無言,似乎在琢磨這句話。
項明章洗了把臉過來,白詠緹回神,忘記要從書柜拿佛經,空著手離開了。
項明章問:“你們在談什麼?”
“是我放肆了。”楚識琛玩笑地說,“我問伯母,能不能讓你給我加薪水。”
項明章輕嗤,長一屈在沙發坐下,竭力克制的酒勁兒蠢蠢,太有些脹,他半躺閉上了眼睛。
今夜的鬧劇在眼前翻涌,項行昭的驚愕哭鬧,項琨的怒氣,項環的疾言厲,大伯母和姑父的釘子,堂兄弟的指摘……
Advertisement
一個個裝得孝天,怕老爺子刺激,實則聯手他的逆鱗,他發作,鬧得在董事面前理虧。
項明章頭痛,抬頭住額角的青筋。
楚識琛仍立著,已近凌晨,他準備告辭了:“項先生,早點睡吧。”
項明章說:“如果一覺醒來在沒人認識的地方就好了。”
楚識琛愣道:“沒人認識?”
“嗯。”項明章說,“這兒待煩了,干脆換到另一個世界。”
楚識琛恍惚地說:“也許真有人從另一個世界來。”
項明章哼笑:“是你醉了還是我醉了?”
楚識琛沒接腔,陷在項明章的假設里,荒唐的是他親經歷這種幻想,卻說不清是一種什麼滋味。
半晌,青姐悄悄送來一碗解酒湯。
沙發上呼吸均勻,項明章好像睡著了。
青姐拿勺子送到項明章邊,嘗試幾次本喂不進去,擔心地說:“解酒湯要喝呀,不然酒醒了,胃疼得死去活來,好罪呦。”
楚識琛干脆道:“把他醒。”
青姐訕訕地說:“項先生的脾氣,我不敢哪。”
楚識琛說:“我來。”
他上前挨著項明章坐下,出左手輕輕托起項明章的臉,五指收攏,掐住線條凌厲的下頜,然后用力地錯手一。
項明章吃痛醒來,再晚兩秒種,楚識琛就要灌了。
他近距離著對方,發聲嘶啞:“你在干什麼?”
楚識琛說:“張。”
項明章:“你在命令我?”
楚識琛:“我在照顧你。”
項明章反客為主:“溫一點。”
楚識琛松開手,不伺候了,出大爺的子:“飲酒傷,不自;長了手讓人喂,不自立;過分要求,不自重。”
項明章立刻接了一句:“教訓上司,不自覺。”
Advertisement
青姐急忙調和:“是我要楚先生幫忙的。項先生,趁熱喝掉回臥房休息吧,我幫楚先生也收拾一間出來。”
楚識琛拒絕了,他和項明章非親非友,第一次登門就留宿太沒家教,他是萬萬不肯的。
項明章欠喝完解酒湯,清醒了些,這是他唯一一次帶外人來縵莊,已經是過界,于是司機送楚識琛離開。
回到楚家,一二樓的臥房都黑著,一片安靜。
楚識琛倦了,回房洗澡睡覺。
大半宿過去,黎明遲遲不來,天空飄滿了烏云。
窗簾拉開房間里依舊有些昏暗,楚識琛不急著起床,擰開臺燈看一本明清小說。
手機振,是錢樺打來的。
楚識琛迅速接聽:“喂?”
錢樺的語氣不像之前那麼吊兒郎當,說:“識琛,你拜托我調查的事,我可幫你好好辦了。”
楚識琛合上書,問:“怎麼樣?”
錢樺說:“嗯……有點眉目。”
有“眉目”而不是有結果,說明還有東西可查,既然需要查,那游艇的事恐怕真的存在問題。
電話說不方便,楚識琛跟錢樺約了個地方,決定見面再談。
剛掛線,收到一條微信。
打開,是項明章發來的:“周一早晨的例會取消。”
每周一要去老項樾開會,壽宴上董事們都在場,鬧得那麼難看,這是要冷理了。
楚識琛回復:好的,我會通知那邊。
按下發送,楚識琛沒退出對話頁面,思忖片刻編輯了第二條:昨晚謝謝款待。
幾乎同時,項明章又發來一句:昨晚多謝照顧。
對仗的兩行字結束了聊天容,項明章揣起手機,從宅院側門穿過,沿途的照明燈準時關掉了,自然下的莊園更加蔥郁靜謐。
酒后睡眠昏沉,項明章趁清晨涼爽走一走。
越往南,園林越茂盛,馬場、花房、藏車庫,全部掩映其中,南區的主建筑群只出一片屋頂,周圍的香樟樹不風。
項明章中途改道,想看看之前派人送來的黃秋翠怎麼樣了。
天,無風,淡淡的晨霧揮散不去,項明章散步到湖邊,游魚在碧水中擺尾,養得神。
護林部的老張執勤經過,停下打招呼:“項先生,早。”
項明章問:“今天不休息?”
“習慣了,每天早晨轉一圈。”老張指向遠,“對了項先生,湖岸東邊停船的小屋拆除了,空了一塊地,還蓋新的嗎?”
項明章道:“不蓋了,西邊一間夠用。”
老張建議:“那空地不如栽樹,挨著湖,水土沃。”
項明章點點頭:“你們看著辦吧。”
老張請示:“那就種香樟?”
項明章略一沉,手機相冊里,楚識琛在南京的紀念照忘了刪除,他垂眸著湖面,說:“不,種水杉。”
猜你喜歡
-
完結1324 章
鹹魚穿成年代小福寶
自帶財運的修真鹹魚重生為被罵賠錢貨的小可憐,慘!剛出生慘遭家族拋棄,被鄉下貧戶帶回收養,實慘!嶽晴晴本以為這一世結束鹹魚生涯,不能再躺平亂殺誰知幾位師兄也一起跟來聲名赫赫的律屆閻王聽說過《動我小師妹必遭天譴基本法》嗎?我寫的。富可敵國的跨國總裁看到這座不夜城了嗎?是我為小師妹打下的江山。被稱為和死神搶人的醫界天才亮了亮手術刀,眾人不禁捂住後頸。影視歌三棲發展的流量天王冷笑一聲陷害師妹?讓你知道什麼叫輿論攻勢。嶽晴晴本想再抱師兄們大腿舒舒服服過一輩子,誰知半路卻殺出個程咬……呸……倒黴鬼。離開她就頭疼腦熱彷彿衰神附體。某大佬晴晴,咱們真是天生一對。眾師兄怒滾蛋!別相信這隻披著羊皮的狼,他上一世就覬覦你!
134.5萬字8.18 55092 -
完結627 章

膚淺關係
27歲的舒菀,始終期盼婚姻,忽然有一天她發現,新上司看她的眼神越來越不對了。新上司白天一本正經,晚上露出獠牙。
104.8萬字8 65724 -
完結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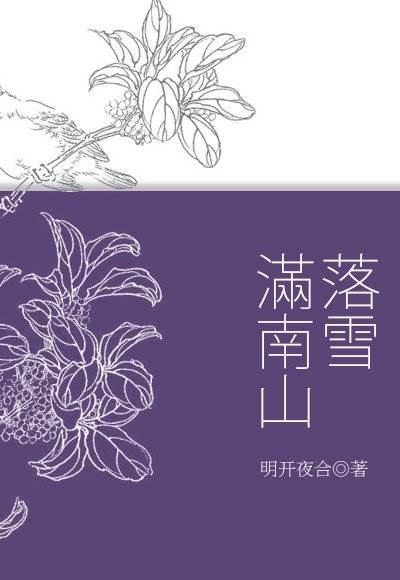
落雪滿南山
[小說圖](非必要) 作品簡介(文案): 清酒映燈火,落雪滿南山。 他用閱歷和時間,寬容她的幼稚和魯莽。 高校副教授。 十歲年齡差。溫暖,無虐。 其他作品:
18.5萬字8 22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