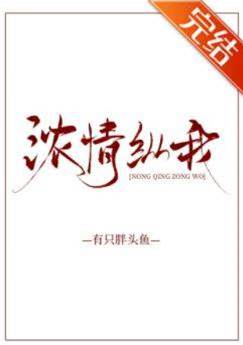《誤刪大佬微信后》 第1章 恩怨
燥熱的盛夏,籃球館沸反盈天。
熱烈的呼喊、毫不亞于窗外如電鉆般刺耳嘈雜的蟬鳴。
椅子上的拉拉隊,穿著彩虹臍衫和百褶,修長的斜斜地擱著,白皙而筆直。
有孩經過旁,目都會不由自主地停頓兩秒。
好漂亮的型啊。
溫瓷曲著子,著已經紅腫破皮的腳后跟,額前幾縷汗津津的碎發落下來,搭在的臉旁。
淡淡的遠山眉微蹙著。
這雙舞鞋是跟拉拉隊的姐妹借來的,所以很不合腳,腳后跟已經被磨破皮了,一陣陣地刺疼。
“溫瓷,下午的酬勞已經轉過來了,你接收一下。”社聯的學姐沖揚了揚手機。
溫瓷打開微信,看到學姐給轉了30塊。
沒有立刻接,反問道:“說好的不是40嗎。”
學姐冷笑道:“跳之前你說你會,結果呢,幾個作都沒跟上節拍。”
“我說我以前學的是古典舞,但你昨晚9點才說缺人、一定讓我急上陣,我練到半夜…”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就給你10塊嗎,小氣那勁兒。”
溫瓷咬了咬牙,堅持道:“談了多,就應該給我多,人不能言而無信。”
“行了,轉了。”
學姐翻了個白眼,罵罵咧咧地轉去場忙碌了。
溫瓷點了確認接收,又緩了好一會兒,才艱難地站起來。
場的氣氛已經沸騰到了頂點,青春洋溢的男們、此起彼伏地高呼著一個人的名字——
“傅司白!傅司白!傅司白!”
大學之后,溫瓷在各種場合、聽各種人提及過這個名字,像是某類風云人…
但,并不關心。
拎著包、撐著疲倦的向籃球館走廊的儲間走去,等會兒匆匆吃個飯,晚上再去便利店兼職。
Advertisement
走廊沒多人,場的歡呼逐漸被阻隔,遙遠得宛如夢境的回響。
溫瓷推開了儲間的門,徑直走到了自己的儲柜里,打開柜門,拿了服準備去更室換裝。
就在經過第二格儲柜時,猛地被嚇了一跳。
儲柜隔間有一對親熱的男。
生背對著,而男人則背靠著墻壁,銳利的側臉廓正好對著溫瓷。
年穿著寬大版型的黑球服,而那一頭灰的流發,越發襯得他的冷白。
夕過頭頂天窗斜斜灑,投下一道橫斜的斑,正好映在年的左手上。
他的左手背無名指部,有黑的字母紋——W
孩抱著他,似乎想要踮腳抬頭去吻他。
年單手隨意地摟著孩纖長的腰,腦袋斜著,眼底有撥的。
在孩就要吻到他薄的片刻,年懶散地偏了頭,似乎不想與接吻。
嗔地罵了一句討厭,卻也不敢進犯。
他偏頭的剎那間,和溫瓷來了個電石火的視線接。
溫瓷拎著白巾的手驀然一。
年眼神宛如蛛般黏著溫瓷,微微挑眉,角勾起了一抹挑釁的笑意。
溫瓷呼吸一窒,加快步伐匆匆離開。
后傳來孩滴滴的嗓音:“你聽到了嗎,外面都在喊你的名字,你卻陪我在這里,我要被們恨死了,好害怕。”
“裝什麼。”
他嗓音,帶著幾分放松的輕。
溫瓷走出了儲室,來到了更間,心臟跳得有些失控。
不是沒有見過談的親,黃昏后的湖畔草坪蒙著眼一腳能踩著兩個。
但那年黏膩的眼神,卻像一撮剛落的煙灰,灑在白皙的皮上。
Advertisement
灼燙之后,便是一抹不掉的黑殘痕。
……
溫瓷換了件干凈的白連,再次回到儲室,將舞鞋放在社團朋友的柜子里。
年早已離開了,只剩那位齊劉海的孩,正和朋友發著語音消息。
外音開著,在寂靜的儲室回響——
“哎呀,差一點,真是難搞,每到關鍵時候他都避開了。”
“霸王上弓唄。”
“我哪有這膽子,那是傅司白哎!誰敢惹。”
“朋友換得比他穿的那些限量款球鞋還勤,就不讓人吻他,留著初吻給誰呢。”
“鬼曉得。”
孩拎著包包在鏡子前拍了照,發給朋友,說道:“花錢這方面倒是大方,就當彌補憾咯。”
……
溫瓷現在的家,位于老城的一棟無電梯居民樓中。
這里沒有綠化幽雅的小區,臨街而建,三樓也不高,總能聽到外面喧嚷的汽車轟鳴聲。
這里與曾經住的南市最高檔的南湖嶼別墅,天壤之別。
家族企業被更強勢的資本吞并,兔死狗烹,眾叛親離。
短短一年時間,溫瓷的生活已然換了一片煙火人間。
曾經為人稱道的小淑,也在一夜間長大,此時也要肩負起父親纏綿病榻、照顧母親的沉重的負擔。
雖然只有八十平的小型三室間,但母親舒曼清卻將屋子收拾得整潔得,柜子上還放了鮮花。
回家的時候,桌上已經擺了飯菜。
一盤番茄蛋炒飯,還是那十指不沾春水的媽媽前不久剛學會菜式。
舒曼清正在柜子邊裝裱著一幅山水畫,溫瓷認出了那是父親的珍藏——《麗水圖》。
見溫瓷回來,舒曼清招呼道:“卜卜,快吃飯,壞了吧。”
溫瓷拿起了筷子,低頭吃了幾口:“媽媽,手藝見長哦。”
Advertisement
“是吧。”舒曼清小心翼翼地放好了山水畫,坐過來拿起匙子舀了一勺,還沒等溫瓷阻止,已經咽了下去。
“咳咳,咳…”
齁得干嘔了一下。
溫瓷無奈地笑著,遞了水給母親,接過來喝了一大口。
“別吃了,外賣吧。”舒曼清皺眉。
“沒事啊,你剛剛吃到沒炒開的鹽了,其實還好。”溫瓷又吃了一大口,“多喝點水就行了,別浪費。”
舒曼清歉疚地看著:“卜卜,媽媽沒能照顧好你。”
“你照顧好自己就好啦,別讓我擔心。”
溫瓷的媽媽是真正的書香世家大人,的一雙纖纖玉指,只會彈箏、作畫和書法,哪里沾染過生活的柴米油鹽呢。
“晚上你要去醫院照顧爸爸嗎?”
“嗯。”
溫瓷趕道:“那等會兒我下班了來替你。”
“別了,你直接回家休息,周一還有課,我在病房有小床,也累不著。”
“好哦。”
溫瓷的父親因為破產和巨額銀行債務,腦管崩裂,搶救回來之后一直于昏迷狀態,也就是俗稱的“植人”。
只有溫瓷和媽媽相依為命,苦苦支撐著這個風雨飄搖的家。
“媽,怎麼把《麗水圖》拿出來了,要帶去醫院嗎?”
“不是,等會兒有買家要過來。”
溫瓷心頭一沉:“這是爸爸最珍的圖呀。”
“但你大學的生活費…”
“我可以申請助學貸款,學費也可以用獎學金抵扣,而且我也可以兼職,這畫不能賣!”
舒曼清搖了搖頭:“你學舞蹈的,不了服鞋子用錢的地方,那點兒助學貸款,哪兒夠啊。”
溫瓷知道,媽媽不管自己多辛苦,都只想讓能夠像以前一樣、面地生活。
Advertisement
但…怎麼可能呢。
從溫家破產的那天開始,就再也不是那朵溫厚水土養育的人間富貴花了。
溫瓷不再堅持,默不作聲吃了晚飯、背了小包要去便利店兼職上班了。
這時,的嬸子蔣玲進了家門。
看到,溫瓷臉瞬間冷了下來:“你來做什麼?”
“我來取畫。”蔣玲拎著lv限量款包包,打扮得宛如貴婦一般,鞋也不便進了屋,后還跟著兩個幫忙抬畫的工人。
“小心著點,這可是真跡,弄壞了要你們好看!”
溫瓷向旁邊靜默的母親,急了:“媽!你要把畫賣給他們家!”
舒曼清抿了抿,仍舊不語。
要知道,當初叔叔和嬸子一家全靠了父親幫扶提攜,才得以從小鎮搬來南市。
叔叔一無所學,初中文憑,什麼都不會,在父親公司里混閑職。
后來公司面臨財務危機,被資本企業傅氏集團吞并的時候,叔叔卻倒戈相向,將公司最機的文件泄給了傅氏集團。
叔叔也獲得了一筆不菲的報酬,一躍為南市商界新貴。
被至親兄弟踩著上位,這樣的打擊,直接引發了父親高病發作,昏迷不醒。
溫瓷是恨了他們一家人,走過來護住了《麗水圖》:“這幅畫不賣,請你離開我家。”
“侄,你想清楚了,你爸都病那樣了,一家人生活沒找沒落的,你又剛上大學,用錢的地方多著呢。”
“這幅畫賣給任何人,都不會賣給你。”
“沒有我,誰來買你的畫啊,一家人等著死吧。”
舒曼清深吸一口氣,沉聲道:“溫瓷,讓開。”
“媽!這是爸最喜歡的山水圖!”?
“讓開!”
蔣玲冷笑著掃了舒曼清一眼:“你這子啊,多跟你媽學學,都到這副田地了還死要面子,這什麼山水圖,能當飯吃麼。”
舒曼清卻從容道:“卜卜,你記住,面的生活從不需要靠外來裝飾,爸爸的審和志趣在他的心里,不在這些圖畫上。”
溫瓷終于不再多言。
蔣玲不太能聽懂舒曼清的話,但能從變不驚的表里看出,是在諷刺呢!
當年從小鎮來南市,參觀溫家南湖嶼的大宅別墅,看到舒曼清在書房寫字。
從容如水的舉止作風,那子書香世家的清雅氣…頓時令到了自卑和愧。
憑什麼,都是一家的兄弟,憑什麼老大的媳婦可以不干活、過這麼好的生活。
憑什麼就嫁了這麼個男人……
所以后來也是慫恿丈夫倒戈相向、搏一把,贏了就是潑天的富貴。
不僅要取代那個人的生活,還要狠狠將踩進泥里。還要讓自己的兒,把的兒也比下去!
今天,蔣玲就是借著買畫的契機,過來看看們的生活,想看們在貧窮的日子里如何痛苦掙扎。
卻沒想到,這人沒有痛哭流涕、沒有消瘦憔悴,一如既往保持著優雅的氣度。
讓人看了就生氣,就討厭!
蔣玲從包里出了一沓現金,惡狠狠砸在了舒曼清的腳邊,現金鋪開散落一地:“拿去吧,好好清點,這可是你們家的救命錢。”
說罷,讓人搬著畫離開了溫家。
溫瓷的手輕微地抖著。
舒曼清卻蹲下來一一撿了錢,遞給溫瓷一沓:“數數。”
溫瓷沒有,眼淚已經含在了眼眶里。
心氣高、不了母親這般辱,卻又…無能為力。
“可真行。”舒曼清從容地數了錢,“三萬塊,給現金,也不嫌沉。”
“三萬塊,你就把《麗水圖》真跡賣了?”
舒曼清睨一眼:“我從來沒說這是真跡。”
“?”
“你爸收藏的那副,早讓銀行收了。”
“那這是…”
“這是我以前閑來無事,隨手臨的。”舒曼清云淡風輕道:“三萬塊就想賣真跡,做夢吧。”
溫瓷心里頓時舒了一口氣。
像蔣玲那樣沒素質的暴發戶之家,自然看不出真跡和贗品的區別,因此,他們也不配擁有真正的藝典藏。
……
夜間,溫瓷守著安靜的便利店,百無聊賴地刷著微博。
微博熱搜頭條,是讓無比刺眼的四個字:傅氏集團。
當初以虎狼手段、吞并了父親公司的資本勢力。南市,沒有人不知道傅氏集團的鼎鼎大名。
溫瓷隨手進了熱搜,頭條就是傅氏集團太子爺的十九生日宴,現場多位明星蒞臨助興,不過這位爺好像并未到場。
眼底著冷意,隨手又往下翻了翻,一個深傅氏集團太子爺的營銷號博文,引起了的注意。
博文容大概意思,像傅氏集團這樣的資本大家族,本應是多子多福,但這位太子爺宛如孤星降世一般。
甭管再努力,傅家都再無第二條脈了。
所以這位爺那是萬千寵,格又是叛逆不羈、桀驁放縱,家里讓他學金融,他偏去考了藝生。
藝考便罷了,文化課還考出了個全省狀元!讓整個南市的重點高校莘莘學霸都震驚了。
一個藝生,搶了他們的省狀元?
類似深的容還有很多,溫瓷懶得多看,直接拉到博文最后,看到了一張照片。
眼,就是傅司白那一頭張揚不羈的灰。
夕下,他倚在路邊攤大排檔的椅子上,挑著下頜,眼神挑釁。
正對著的拍鏡頭…..豎中指。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盜情
她是二十一世紀最負盛名的神偷之一她是黑市上經久不衰的車王神話她一個風一般的女子瀟灑來去,快意人生他是黑道上數一數二的豪門大佬鐵血無情心狠手辣沒想到有人敢太歲頭上動土動了他的財物既然是有人嫌命長了,他就替她來收是情,是愛,是恨,是傷一切撲朔迷離黑幫文,火拼激烈,場面宏大,情節血腥,黑暗情節嚴重,口味甚重,想只看情感糾葛的別進來,偶這裡有的是整個世界黑暗面,裡面的男主絕對不是好人,汗,帶壞小孩子.
48.9萬字8 11592 -
完結7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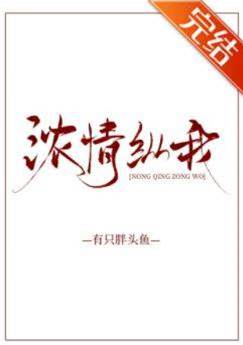
濃情縱我
宋傅兩家聯姻告吹,所有人都以為,深情如傅北瑧,分手后必定傷心欲絕,只能天天在家以淚洗面療愈情傷。 就連宋彥承本人,起初也是這麼認為的。 直到有天,圈內好友幸災樂禍發給他一個視頻,宋彥承皺著眉點開,視頻里的女人烏發紅唇,眉眼燦若朝瑰,她神采飛揚地坐在吧臺邊,根本沒半點受過情傷的樣子,對著身邊的好友侃侃而談: “男人有什麼好稀罕的,有那傷春悲秋的功夫,別說換上一個兩個,就是換他八十個也行啊!” “不過那棵姓宋的歪脖子樹就算了,他身上有股味道,受不了受不了。” “什麼味道?渣男特有,垃圾桶的味道唄!” 宋·歪脖子樹·彥承:“……?” 所以愛會消失,對嗎?? - 后來某個雨夜,宋彥承借著酒意一路飆車來到傅家,赤紅著雙眼敲響了傅北瑧的房門。 吱呀一聲后,房門被打開,出現在他面前的男人矜貴從容,抬起眼皮淡淡睨他一眼:“小宋總,半夜跑來找我太太,有事?” 這個人,赫然是商場上處處壓他一頭的段家家主,段時衍。 打電話送前未婚夫因酒駕被交警帶走后,傅北瑧倚在門邊,語氣微妙:“……你太太?” 段時衍眉梢一挑,側頭勾著唇問她:“明天先跟我去民政局領個證?” 傅北瑧:“……” * 和塑料未婚夫聯姻失敗后,傅北瑧發現了一個秘密: ——她前任的死對頭,好像悄悄暗戀了她許多年。 又名#古早霸總男二全自動火葬場后發現女主早就被死對頭扛著鋤頭挖跑了# 食用指南: 1.女主又美又颯人間富貴花,前任追妻火葬場,追不到 2.男主暗戳戳喜歡女主很多年,抓緊時機揮舞小鋤頭挖墻角成功,套路非常多 3.是篇沙雕甜文 一句話簡介:火葬場后發現女主早跟死對頭跑了 立意:轉身發現新大陸
23.5萬字8 27173 -
完結966 章

白日偷歡:離婚後前夫如狼似虎
結婚三年,她盡職盡責,卻沒換來他半點憐惜。離婚時,她一腳被踹,帶著患有自閉癥不會說話的女兒淨身出戶。拋棄累贅,他才能迎娶他的白月光。再見時,她脫去馬甲,臨江首富之女,跨國總裁頭銜加身,華麗轉身。某天才兒童:“爹地,媽咪要改嫁了哦!”某女:“抱歉,我們早就離婚了。”某總裁:“老婆,不信你去查查離婚證編號。當年我給你的,是假證。”某女:“……”某天才兒童,“……”堂堂總裁居然幹辦假證的事……
87.9萬字8.18 710130 -
完結464 章

心頭肉
狐貍精vs狗男人林與幼收錢辦事,三年來,兢兢業業地扮演著程京宴白月光的替身。第二章:白月光回國。第三章:白月光成了他親嫂子。林與幼:呦呵。我也是你們play的一環嗎?告辭。可是狗男人不知道是退而求其“次”,還是“日”久生出情,開始出現在她身邊的任何地方。“我知道你對我情根深種不可自拔,如果你乖一點,聽話一點,我可以讓你繼續留在我身邊。”林與幼滿臉真誠:“可是我現在比你有錢誒,十個億,買你離我遠一點,行嗎?”程京宴:“……”那如果是我對你情根深種不可自拔,我們還能不能,重頭來過?——沒有白月光,沒有朱砂痣。她一直是他的心上人。——1V1,雙潔,人間清醒隨時發瘋女主和口是心非嘴硬傲嬌男主
84.3萬字8 7909 -
連載1954 章

開局威脅校花,這個反派我當定了
【變態、腹黑、無節操、搞笑、蘿莉,純愛戰士避雷】江澈穿越成了都市爽文中的反派富二代,并且綁定神級選擇系統。開局正好撞見小蘿莉女主在偷試卷?觸發反派選擇!【選擇一
409.5萬字8.33 11268 -
完結170 章

金魚入沼
偶有幾次,江稚茵聽朋友談起:“你沒發現嗎?你男朋友眼睛像蛇,看上去滿腹心機的,但是你一盯着他,他就乖得不得了,好奇怪。” 後來江稚茵注意了一下,發現的卻是別的奇怪的東西。 比如聞祈總是挑她最忙的時候,穿着鬆垮垮的衣服半倚在床頭,漆發半溼,瘦白指尖捻弄着摘下來的助聽器,嗓音含糊微啞: “與其做那個,不如做——” 他的嘴型由大到小,像嘆氣。 江稚茵打字的手一頓,猜到他將說沒說的那個字,及時制止:“現在不行。” “啊。”他耍渾,笑,“聽不到,你過來說。” “……” 在汗溼的時候,她故意盯着聞祈的眼睛,那人卻用手蓋住她的眼,用輕佻的語氣叫她不要多心。 後來江稚茵才知道,朋友說的都是對的。 這個人的心腹剖開後,都黑透了。 原來他從在孤兒院第一眼見到她,就算計到自己頭上來了。
27.4萬字8.18 16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