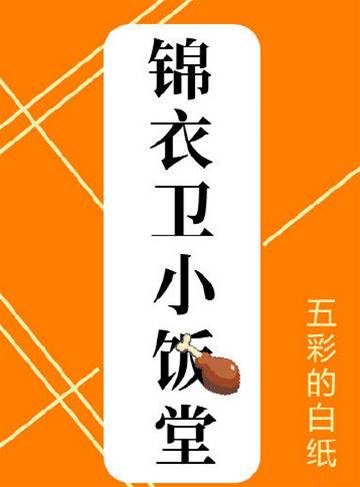《姑母撩人》 第7章 第7章
皎月無言,零落玉宮。隨香浮中,門里進來個婆子,領著兩三個丫鬟在屋里巡視燈燭。
回首見奚桓抱膝坐在榻上僝僽不言,便笑,“我的寶爺,快別提先生了,你那一頓排場,人家已經向總管房里請辭不來了。虧得老爺近日在衙門里忙,暫不得空歸家。倘或回來,不見先生,不得打你!”
“打我就挨著,咬咬牙就抗過去了。”隨著豁然開朗的語調,奚桓梭下榻來,鏘然拂正鵝黃的圓領袍,挑著下吩咐,“點上燈籠,去蓮花顛里瞧姑媽。”
秋蘅正坐在帳中鋪床熏被,不彈,“這都什麼時辰了,好爺,洗洗就睡吧,明兒再去。”
“就此刻去,姑媽想我了。”
眾人嗤嗤發笑,“想你是有糖吃呀還是有銀子花啊?”
吊詭的是,奚桓就是覺,花綢此刻需要他。他固執地抻抻袍子,“要你們多?就現在,點上燈籠,去蓮花顛。”
眾人訕了,悶不做聲地照舊在屋里忙活。見狀,奚桓復架起眉,“我說點燈籠。”
人還是不理他,他心急如焚,鼓著腮展臂一掃,將炕幾上一只紫砂梅花壺脆到地上,冷噙著笑,“不去,我就告訴姨娘,這壺是你們跌的。”
婆子冷不防他唬得一,忙分派四五個丫頭秉燈引路。這般月下夜行,燈前探路,穿越清淺銀河,踅蓮花顛,迎頭是椿娘開的門,奚桓只說悄悄的,別驚姑。
椿娘將其引進東廂,見花綢髻亸鬢松地靠在帳中,單借一盞黃燈在做活計。奚桓舞旋旋地撲到被褥上喊,“姑媽,您怎麼還不睡?”
四下岑寂忽他驚散,花綢擱下針線,使椿娘掛起帳,有些懨懨地笑著他的背,“天都黑了,你怎麼兀突突地跑來?”
Advertisement
“我想您。”他站直了腰,湊到花綢眼皮底下眨眼。一個回合里,聞見屋里一子藥香迷離,又濃眉稍疊,“誰吃藥?嗯?誰吃藥?姑媽,是不是您病了?”
那椿娘在炕幾上倒了盅茶,嬉笑逗他,“可不是病了嘛,打那日從大爺院兒里回來,就咳個不住。想來是在您屋里您給氣的。”
因他來,花綢使喚著再點兩盞燈,屋里燈火漸明,照得一搦細腰枝,暗暗添憔悴,“別聽的,姑媽就是被風吹著了。聽說你父親好些日沒回家,在忙什麼呢?”
奚桓滿心自咎,茶涼在炕幾上也不吃,寸步不離地立在床畔,不敢瞧的臉,“各省的秋稅剛繳上京來,爹在戶部核賬,核了賬,還要與尚書大人向皇上呈奏。奏完,就是核批一年各省各部的用度,還要定下年節里各級員的臘賜,且一陣忙呢。”
“喲,”花綢歪著臉撈他的眼睛,心里有些淡淡喜歡,“桓兒還懂這些呢?”
得了夸獎,他咧著笑,出個黑漆漆的牙也不自知,只顧窺花綢的面,“姑媽,您好些了嗎?”
“托桓兒的福,好了許多了。”
暗風細細的夜,奚桓覺得四周都是黑漆漆的,人間只得他與姑媽這兩枚星辰在黑暗兩端。他把自己靠過去,依偎著花綢,“姑媽,我今晚挨著您睡,行不行?”
真個是八輩子的冤家,花綢心一,許他了靴上爬上床來,椿娘自帶門出去打發跟來的婆子丫頭。
這廂吹了燈,兩個人并頭枕著,綺窗灑進月,奚桓橫著胳膊將抱著,臉埋在肩上。
花綢瞥眼見他兩個眼還泛著,心腸為一池溫水,翻過來摟著他拍,口里唱著,“月牙灣,月牙灣,灣里住著個仙娘……”
Advertisement
窗外果然有一彎月逐寸沉淀下去,不幾日天里,卻有一場熱鬧在日漸結凍的空氣中,怦然炸開。伴著滿府里仆婦小廝肩踵地忙活幾日,終到十月二十這日,車馬盈門,歌舞喧闐。
因是奚府里二老爺奚巒的生辰,奚甯出空來,與其弟梳頭扎幅巾,整到外院廳上,迎拜爵親朋。男客們只在外頭設宴,由兄弟二人陪著,請了百班小戲吹打彈唱。
門亦不清凈,烏寶齋廳設下七八臺席面,排坐著京眾多眷。對過亭子里戲罷,又請了三個倡人在廳番唱著。
正唱一套《西廂》,始見那翰林院侍讀家的元夫人提杯到上席請范寶珠,“尊府里大喜,姨娘必定是連軸轉了好些日,實在辛苦。”
這元夫人眉梢高吊,眼睛斜提,天生一張喜慶臉,提著杯,又向次席扭頭招呼眾人,“咱們白來吃一頓,哪里好意思啊?肖夫人,咱們一道敬姨娘盅!”
下席里拔起來兩位年輕婦人,跟著提杯舉斝,獨敬范寶珠。范寶珠心用得,瞥馮照妝一眼,志得意滿地提杯,“各位夫人只管席上坐,哪里要大家來敬我?不得我挨個兒去敬各位!”
今日穿著大紅泥金通袖袍,帶著金項圈,熱辣辣的火燒一般的,襯得若雪,紅滿面。又因奚甯居高位,眾人只管來敬,簇得灼灼花如繡。
可今日原是馮照妝漢子的生辰,卻范寶珠出盡了風頭,馮照妝哪里氣得過,心照恨,面上仍笑著,提杯科。
席上婦人品曲取樂,噓寒問暖,湊出個玲瓏錦花陣。陣外有各家姑娘小姐自一席,擺在最末。
Advertisement
花綢自然與范韞倩挨著坐,見云鬟惺忪,香腮憔悴,因問起:“我聽說前些時你在家把紗霧打了,被莊大嫂子罰了一場,到底為什麼打?”
韞倩遠遠朝那莊萃裊瞥一眼,又將滿廳里跑的范紗霧恨一眼,湊過腦袋來,“為了紗霧丟了個金兔鎖,非講是我拿的,太太就將將罰跪在祠堂里。后來領著丫頭搜了我的屋子,沒搜出來,才許我起來。”
“我曉得這個事兒,”花綢也在萬艷百芳的上席將莊萃裊淡瞥一眼,“還問到我屋里去過,后來找著了嗎?”
“哄哄的,誰曉得在哪里弄丟的,哪里能找得回來?只好重新打一個罷了。”
花綢笑靨溫,輕聲安,“真是委屈你,白白的將你罰一頓。”
“也不是頭一遭借故整治我,我早習慣了。”
兩個淡淡寒暄,晃見二房里的林媽媽進來,湊到馮照妝耳朵里說幾句。馮照妝面微凝,席上辭了兩句,與那婆子退出廳上,踅進邊上一間耳房里。
甫落在一張扶手椅上,那馮照妝便怒提眼角,“真的?”
“真真兒的!”林媽媽在左落座,胳膊搭在方案上,“陳橋家的親口告訴我聽的。外頭人進來說咱們老舅爺吃多了酒,陳橋家的就往廚房里要一碗醒酒湯,誰只倒秦婆子刺了幾句。說是哪門子的老舅爺,這滿府里,就只老太太那一門娘家親戚。”
那秦婆子正是月琴娘,這老舅爺呢,原是二老爺奚巒的親舅舅,因奚巒是庶出,那秦婆子也懶怠招呼這沒名分的親戚,便借機諷了兩句二房里的人。
馮照妝冷耳聽著,又斜眼問,“還說什麼了?”
Advertisement
“還說:‘什麼老舅爺?咱們家老太太是三公太師家的獨,一向沒有兄弟姊妹,哪里又鉆出個老舅爺來?一到這熱鬧日子,就多是那些數不上名的人來借機打秋風,要吃醒酒湯嘛沒有,黃湯倒有一碗。’您聽聽,這可不是打咱們二房里的臉嘛!”
這林婆子端著腰,學得惟妙惟肖,直點馮照妝怒火。頓一頓,胳膊輕抬,甩甩帕子,冷噙一笑,“哼,好一張,連我與二老爺也不放在眼里。你去找幾個婆子,把捆了打二十板子。”
林媽媽有些顧慮,湊過頭來,“打也打得,只是這秦婆子是范姨娘陪嫁來的人,聽見……”
“就是要聽見,”馮照妝扶一把髻,半婀娜地端起,想起方才席上眾人結范寶珠的模樣,愈發恨得牙,“也讓醒醒神兒,這個府里頭,不是姓范的說了算!”
如是,這林媽媽得了令,只管外頭去上幾個婆子,一陣風似的按到廚房里,綁了秦婆子,撳著就是噼里啪啦好一頓打。
猜你喜歡
-
完結365 章
快穿白月光:男神抱一抱
作為一個老妖怪,呸!仙女,花如錦在得罪了某個老男人後被一腳踹進了八千小世界。 美男千千萬,花如錦撩了一個又一個,到最後才發現,呸!她媽噠都是同一個野男人! 她要罷工!罷工!! 宿主每天罷工八百次,係統冷漠臉:【請宿主端正態度——罷工會單身一輩子的】 至於某個野男人,麵對這個磨人的小妖精那是一臉冷漠,嗬,女人,結果,被小妖精撩上以後,從此節操是路人…… 嗯,阿錦真美。 ————————— 簡而言之,這就是一個坑妻一時爽,追妻火葬場的故事~
33.2萬字7.82 6383 -
完結1806 章
帝色撩人
十四年情深似海,癡心交付,換來的是他江山穩固,她家破人亡。 當她踏著鮮血步步重生,回歸血債的開端…… 「狠毒?你可知親眼看著雙親被野狗分食,是何等痛不欲生?」 在這個世家與皇族共天下的浮華亂世,她是華陵鳳家最尊貴的嫡女。 一手折扇,半面淺笑,藏住滿腹陰謀。 一襲紅裳,七弦著墨,結交天下名流。 當她智鬥族男,顛覆祖製,成為有史以來唯一一位女少主; 當她躋身清流,被名士推崇,成為一代領袖; 鳳舉:「灼郎,我心悅你,你呢?」 慕容灼:「她足下的尺寸之地,便是本王要守護的江山!」 巍巍帝闕,誰將興舉盛世風骨?
175.5萬字8 67322 -
完結2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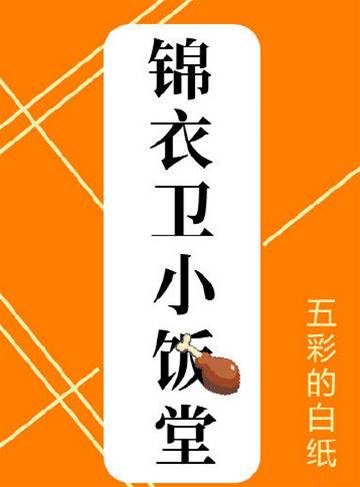
錦衣衛小飯堂(美食)
自從董舒甜到錦衣衛小飯堂后,最熱門的話題,就是#指揮使最近吃了什麼#錦衣衛1:“我看到夜嶼大人吃烤鴨了,皮脆肉嫩,油滋滋的,嚼起來嘎吱響!”錦衣衛2:“我看到夜嶼大人吃麻婆豆腐了,一勺澆在米飯上,嘖嘖,鮮嫩香滑,滋溜一下就吞了!”錦衣衛3:…
77.3萬字8.09 392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