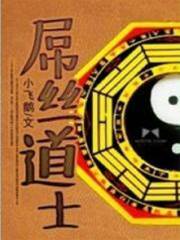《異常生物收容系統》 第一章,臨江市殯儀館
夜冷清,室燈昏暗,窗外有微風吹拂。
晚上11點半,臨江市殯儀館,秦昆摘下手套,長舒一口氣走出間,在供臺上點了三炷香。
“各位安息,我不通經文,改日請位老和尚給你們唸經超度。”
微風捲起火盆的黃紙,火星飛揚,香頭忽明忽暗,聽到秦昆的話,隨後片刻,漸漸平靜。
臨江市殯儀館三樓,外面一片漆黑,空曠的樓只剩下秦昆一人。他著面前漂亮的,臉上的傷口已經被合到平整,於是將慢慢推冰櫃。
走出殯儀館,秦昆朝著門衛招呼道:“曲大爺,我走了。”
收音機裡放著越劇,門衛室的曲大爺頭也不擡說道:“死人不說留,活人不說走,小秦,你在殯儀館也工作快兩年了,以後得注意點。”
秦昆訕訕一笑,表示知道。
附近最後一趟公車也下班了,不過沒關係,秦昆騎著自行車,慢慢悠朝著市駛去,他的夜生活纔剛剛開始。
殯儀館位於臨江市西郊,因爲地偏僻,又有鬧鬼的傳說,幾乎沒有人晚上會開車經過這裡,尤其是夜晚子時,氣最重的時候,即便是膽子大的司機,也會找遠路繞行。大馬路上,秦昆飆的飛快,涼風驅散了夏日的暑氣,一個人獨佔一條公路的覺,還不賴。
滴滴——
一陣喇叭的聲音傳來,秦昆面前的拐角出現了兩道亮,讓秦昆爲之一愣。
這條路到了晚上,遇到司機的況可不多。
秦昆看到一輛出租車迎面而來,停在他邊,司機還是人。
“秦師傅,剛下班?捎你一程?”
秦昆年紀並不大,才22歲,不過16歲便出社會闖,爲人老,再加上職業的特殊,屬於手藝人的行當,認識他的人大多都會稱一聲秦師傅。
Advertisement
“呵呵,老鄺,不用了,我騎回去鍛鍊。你這麼晚跑西郊,接人嗎?”
秦昆笑呵呵地招呼道,同時點了菸。
司機鄺師傅看到火,皺了皺鼻子:“我今晚接了個大大單子,接個人去市裡,給200塊,你真不搭車?不收你錢。”
秦昆揮揮手:“不用了,趕去接人吧。我也先走了。”
鄺師傅見到秦昆不上車,也沒有繼續邀請,“秦師傅,點。煙這東西對可不好!下次順路的話再捎你!”說罷,開車遠去。
秦昆著開往殯儀館方向的車,心中一嘆:老鄺,你特麼都死了三個月了,還這麼敬業,我也是佩服!
三個月前,臨江發生了一起連環車禍,據說是一位出租車司機低糖犯了,一路撞了三輛車,開下立,出租車司機當場死亡。死的就是鄺師父,還是秦昆幫忙把合的。
殮師這一行秦昆已經做了兩年了,他知道有些人死後還是會按照以前的方式生活,這種奇聞異事可能很多人不信,不過在殯儀館幹過的老人都知道,大多數也都見過,所以不足爲奇。
空曠無人的馬路,自行車車速飛快,秦昆一路騎到三環,鄺師傅從後面追上,而過,摁了兩聲喇叭算是招呼。秦昆看到出租車後排坐著一個人,容貌豔麗,皮白皙,臉上有一道疤痕,正是自己剛剛合的子。
子在車窗裡朝著秦昆揮了揮手,出租車揚長而去。
秦昆剎住車,呆呆看著尾煙,突然大道:“老鄺!你特麼給我停車!!”
……
臨江市西鄉街,夜魅酒吧。
白日枯燥疲憊的工作結束,夜晚,屬於喧囂和狂歡。
Advertisement
秦昆格沉默寡言,朋友不多,平日算得上酒吧的常客。
西鄉街是臨江市一條酒吧街,夜文化富,坐在角落的卡座,秦昆著臺上的駐場歌手,表有些無語:特麼的……還真會選地方啊!
臺上是一位新來的主唱,唱著王菲的‘容易傷的人’,音悽迷,眉頭蹙,的音很好,只是這首歌被唱太過哀怨,臺下的人們滿足了,但是喝酒的男士不幹了。
歌聲一落,臺下幾位喝多的男子起鬨道:“妹妹!來一首歡快點的!哥哥給你送花籃!”
那位主唱甜甜一笑:“小妹第一次來,今天先獻上這三首歌,希以後各位哥哥姐姐多多支持。”
說完鞠了一躬,沒理會臺下觀衆的反對,走進後臺。
臺上,一位男歌手接過話筒,聽到男士們罵罵咧咧,趕講了幾個葷段子,又重新將場子暖了回來。
秦昆看到剛剛的主唱走進後臺沒多久,就換了套服裝走出來,坐在他不遠的卡座,於是正了正衫,端著酒走了過去。
“唱得不錯徐姑娘。”
秦昆打了聲招呼,沒經過同意,便在邊坐了下來。
主唱即便帶著濃妝,也能看得出底子不錯,皮白皙,五緻,十指塗著紅的指甲油,鑲著鑽,腳上踩著涼高,筆直的帶著彈。不過唯一中不足的是,的臉上有一道疤痕,即便濃妝也掩蓋不了。
主唱見秦昆的時候,表錯愕,似乎沒想到在這裡能見到他。
“秦師傅,沒想到你也會來酒吧這種地方。”
人的眼神有些戲謔,秦昆著鼻子,呵呵一笑:“工作環境不好,力大,總得找個地方放鬆一下。沒想到今晚恰巧上了你,我們還真有緣分啊。”
Advertisement
人的表有些不自然,不過轉瞬即逝,剎那間,小人的神態流,嗔道:“你今天可是把人家看了,不請人家喝杯酒嗎?”
人態度曖昧,往近坐了一點,寬鬆的長衫垂下,口一覽無餘,秦昆低頭,依稀可以看到口兩粒凸起在長衫中若若現。人和秦昆挨的很近,化妝品的味道混雜著酒味,瀰漫在他的邊,秦昆在這些味道之中,仍能聞到一淡淡的臭氣。
嗯,臭。
面前的主唱,正是晚上坐著鄺師傅出租離開的人,徐姍,也是秦昆今天合的之一。
秦昆可不習慣被一這麼靠著,稍微坐開了點,打了響指來侍應生,點了杯蘭吉娜遞給徐姍。
“徐姑娘,大晚上從西郊打的過來,不是爲了唱幾首歌吧?”秦昆見到徐姍幹了蘭吉娜,纔開口問道。
這一年多來,徐姍算得上他見過的最漂亮的死者之一,長相乖巧,有一種文藝氣質,年紀看起來也不過28歲左右,秦昆想起上好多紋和煙疤,猜得出看起來應該沒有表面上那麼單純。
而且,被人砍了16刀,秦昆不知道這個姑娘惹了多大仇,能被人砍那樣。
今晚看到徐姍被鄺師傅拉走後,秦昆氣的火冒三丈,鄺師傅死就死了,還敢開車到殯儀館拉生意,這年頭到底誰發明的給死人燒車燒手機的,這不是添麼!
徐姍笑著秦昆,因爲臉部被合的緣故,讓笑的極其不自然:“秦師傅,現在的殮師也會管這麼多嗎?我今天是來報仇的,你要攔我嗎?”
徐姍的牙齦有些青紫,牙齒已經變尖銳焦黃,上面滲著漬。著舌頭,瞳孔已經到了針尖大小,出大片眼白,迎著的目,讓人渾不舒服。
Advertisement
秦昆到一冷風撲面,打了個哆嗦。
半夜三更,鬼尋仇,這種事他自然管不了那麼多,他就是個殮師,除了被館長親自誇贊八字命以外沒什麼可以炫耀的地方。和徐姍認識只是工作需要,論起來徐姍還是他的‘客戶’,現在哪個行業不是客戶至上?他的績效獎金還是得死者親屬給評分的,評分低了可沒獎金拿。
“有仇報仇,有怨報怨,徐姑娘,你要弄死個人,我沒法攔你,也不想攔你。不過你已經鬼了,就沒必要披著出來興風作浪了吧?這明天就火化,儀容被折騰爛了,還得我來收拾!我一天這麼辛苦,殯儀館那麼多等著我收拾呢,時間可不能全浪費在你上啊。”
秦昆點了菸,表有些爲難。
徐姍怨毒地盯著秦昆,發現他只提工作的事,似乎一點都沒把自己放在眼裡,小一張,噴出一口黑氣,秦昆的周圍,溫度驟降,他發現周圍一黑,酒吧突然變得空無一人,只剩對面的徐姍,雙瞳流著自己。
臭氣瀰漫,秦昆扇著鼻子,無奈道:“徐姑娘,你這是做什麼?”
徐姍的眼底閃過一抹譏諷:“憑你也想管我?”
秦昆攤開手,表有些無辜:“我真沒想著管你,你乖乖把送回去,今晚你就算把這間酒吧所有的人屠了也不關我的事。”
“那我要是不呢?”
秦昆嘆了口氣,閉起眼睛,食指在額頭豎劃一道痕跡,再睜眼,秦昆那雙永遠打不起神的眸子,突然變得漆黑而冰冷。黑暗迅速退散,周圍又重新恢復嘈雜。
徐姍不敢相信地著周圍,秦昆揮手間就破了自己的‘鬼打牆’,這讓心中變得有些茫然,接著心底升起了惶恐。
秦昆坐到徐姍邊,摟住徐姍的脖子,低聲道:“徐姑娘,不聽話的鬼可不人待見。”
徐姍頓時覺得,秦昆的胳膊像是鐵箍一樣,的自己彈不得,那雙眼睛深邃如淵,徐姍對視了一眼,好似陷進去一樣,腦海傳出劇痛,卻說不出一句話來。
秦昆在徐姍頭頂,大手一抓,徐姍的魂魄直接被拽了出來,立即了下去,靠在秦昆上。
徐姍的鬼魂被秦昆攥在手心,徐姍愕然發現,自己來到了一甕中。
“你也別想著報仇了,給我老實待著吧。”
著秦昆背起自己的,朝著酒吧外面走去,好似來酒吧獵豔的獵人,帶著自己今晚的獵一樣,荒誕而可怖。
一位侍應生跑過來攔住秦昆:“先生,您不能帶出去,是我們酒吧的駐場歌手……”
秦昆側著頭,瞪了侍應生一眼:“滾!”
……
猜你喜歡
-
完結462 章
冥婚難測
我是一個視財如命的女人,老天待我不薄,我終於如願嫁入豪門。可是就從我嫁入豪門開始,一切發生鉅變。被鬼纏身,被迫與鬼冥婚,孕育鬼子,只是可惡的鬼夫,活生生的斬斷了我的大好財路。某天,我剛解決了一隻女鬼,對鬼夫說道,“我不要待在鬼界和一羣鬼女人宅鬥,你乾脆放了我,讓我回到人間,繼續我的財路,將來也好爲你的鬼界做些投資!要不然我就把你的鬼界攪得天翻地覆!”只見這個長得俊逸非凡,散發著幽幽鬼氣的鬼夫,將一疊冥幣塞進我的手裡面,對我似笑非笑,“我也覺得我的鬼界有些鬼甚是無聊,不如我陪你一同攪罷?這些錢你在鬼界盡情的花,沒了找我要,但是休想離開!你是我的妻,此生唯你!”***************
76.3萬字8 7004 -
完結70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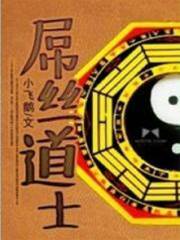
屌絲道士
一個尿尿差點被電死的男人,一個運氣差到極點的道士!他遇到鬼的時候會惹出怎樣爆笑的事端?各種精彩,盡在屌絲道士中。
182.8萬字8 65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