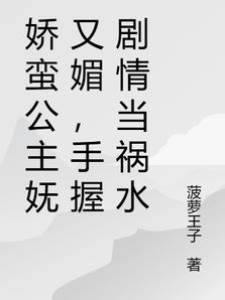《過期暗戀》 第7章 溫柔刀
離圖書館閉館還有十分鐘。
蘇羨音看了眼手機,沒有陳潯發來的消息。
而他的東西還靜靜躺在桌子上。
沒有跟柏谷走,最後以跟同學約好了為由委婉拒絕了他。
他陪著坐到了10點,接了個電話之後離開了。
但陳潯始終沒有回來過,不知道是事太棘手還是已然忘記了自己還有東西在圖書館。
顯然第二個理由說服不了任何人。
還是決定問他一聲,打打刪刪之後,乾脆撥通了他的電話。
「你好?」陳潯那邊聽起來背景有些嘈雜,似乎還在外面。
「我是蘇羨音」讓自己的語氣聽起來盡量輕鬆明快,「你的電腦、書包……」
「嗯,還有水杯,要幫你帶回去嗎?」
「看樣子你好像不會再回來了。」
一個不留神,真心話順著裂開的豁口溜了出來。
「哦,沒事,今天圖書館值班是我朋友,他會幫我收起來的,我到時候自己去拿,就不麻煩你了。」
滴水不的回答,將親疏分得明明白白。
「好。」
空調冷風終於停下,周遭一剎那安靜下來,靜到蘇羨音能聽見自己心口的嘆息聲。
「不過」陳潯在那頭笑起來,「你還沒走嗎?」
是的。
還沒走。
一些的自嘲聲漸漸攏過來,蘇羨音聽他口氣都覺得是某種挖苦。
皺著眉:「什麼?」
「我中途回去了一趟,看到柏谷了,所以就沒過去打擾你們。」
陳潯的笑意里有了清晰的暗示。
以為會跟柏谷去「約會」是嗎?
蘇羨音現在不止是覺得寒意涼涼了,還有燥熱,從腳底升起。
「我是該誇你想得周到嗎?」
「嗯?」
「沒什麼,我要走了,拜拜。」
蘇羨音掛下電話,黑掉的手機屏幕里顯現出的臉龐。
Advertisement
白皙小巧的一張臉化了淡妝,襯得五明凈,眉眼含。
前幾個小時還在為此沾沾自喜的,此刻像是個回到化妝間疲力盡的小丑。
以為會有不同,以為在一步步靠近他。
可與他之間,還是有一條清晰的界線。
-
回宿舍的路上,蘇羨音接到孟凡璇的電話,遲疑了片刻,等著鈴聲唱了一半才慢騰騰按下接聽鍵。
孟凡璇的聲音依舊輕,照例先問了幾句近況,強打神一一答了,不算敷衍,甚至對比對蘇橋的態度,這已經算得上是打起十二分神出的答卷了。
沉默來得悄無聲息,讓蘇羨音好不容易搭建起的友好氛圍搖搖墜。
輕聲道:「有什麼事要跟我說麼,阿姨。」
孟凡璇像是有些不好意思一般,笑了一聲,說:「就是過陣子我正好要去川北出個差,大概三到五天,想著你到時候課業不忙的話,阿姨帶你出去改善改善伙食?」
其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蘇羨音也沒有理由拒絕。
但謹小慎微是孟凡璇對待的時候的基礎,儘管為此已經做出很多嘗試,無數次釋放出友好信號。
孟凡璇依舊如履薄冰,當是個瓷娃娃。
「好呀。」
不自覺帶上了語氣詞。
邊傳來了一聲輕笑,蘇羨音起初未在意,聽見孟凡璇在電話那頭說:「好好,到時候阿姨聯繫你啊,你爸這陣子實在是忙不開,本來他也想要跟我一起來看看你,到現在還羨慕我呢。」
「你跟說這幹什麼……」
蘇橋的聲音聽起來有些距離,不知道是不是又坐在沙發上看新聞。
路燈下蘇羨音的影子被拖得很長,注意到還有個同伴。
側那道影子更長,此刻甚至因為的注視以及停下的腳步而張開了右手的五指,晃了晃。
Advertisement
圓潤而可的一個招呼。
蘇羨音轉過頭,陳潯單手兜,路燈將他的廓勾勒得溫,他個頭太高,被樹葉到頭頂,微低著頭躲著,朝笑了聲。
他夏季好像總有一百八十件不重樣的t恤或者襯衫,件件穿得出彩。
著他,對著手機說:「阿姨我晚點再跟你說。」
掛斷電話,問他:「你怎麼在這?」
他卻像個頑劣的學生,不答反問:「你每天回宿舍都走這麼慢麼?圖書館走到裕華樓,你足足花了10分鐘。」
蘇羨音沒回答,眼睛卻在笑。
一前一後兩個影子,了並排。
陳潯從蘇羨音手裏接過電腦包,問:「所以論文你開始寫了嗎?」
這條路經過一片茂的植被林,蟲鳴聲不斷,9月到底不比盛夏,微風涼涼,蘇羨音手心卻冒汗。
「沒有,我定了題目,然後做別的作業去了。」
陳潯深信不疑。
「你選了什麼題目?你那篇我幫你寫,怎麼說也是我連累了你。」
蘇羨音看向他點頭,在捕捉到他的小表后很快又說:「你該不會在等我說『沒有,這怎麼能怪你呢,我自己寫就好了』?」
陳潯撓眉心的作出賣他,蘇羨音捂輕笑。
「看來你也沒有傳聞中那麼磊落。」
「說起來,這次不僅是你連累我,連帶上次臉頰傷,都有你的參與,我為什麼要跟你客氣?」
說得理直氣壯,心鼓卻已經擂了起來。
與他談判時沒有籌碼,心秤早義無反顧偏向他。
穿過c1棟生宿舍,底下鬧哄哄一團,看架勢像是有人當眾告白,蘇羨音踮起腳尖了一眼。
微涼的在這時從右臉頰的傷口傳來,錯愕回頭,陳潯屈起的食指尖還未撤退,在臉上輕輕一揩,痛和火燒火燎的熱意一瞬間將點燃。
Advertisement
陳潯也像剛回過神,被眼底的震驚神給燙到收回了手,眨眨眼后,他結輕滾:「過敏應該是好了,但傷口看起來像是還沒好全?」
儼然又是那個風度翩翩、友同學的五好青年陳潯。
「要是能好得這麼快,你寫論文確實是虧了。」
他怔了怔,無奈聳肩:「我並沒有要賴賬的意思。」
不遠起鬨聲愈演愈烈,像是表白功,歡呼聲像海浪,一層又一疊。
不知道是誰的手機手電筒也跟著緒一起失控,在空中晃了幾遭,下一個聚焦點就要是蘇羨音的雙眼。
下意識閉上雙眼,眼睛再睜開一條時,沒有直直落眼裏。
聽見陳潯的聲音在頭頂后側響起。
「這些人可真有力。」
他拿開擋在眼前的手,復見明的一瞬間,心口有些泛酸。
好沒出息。
「走吧,我帶你走條小路。」
陳潯拍了拍的肩。
小路指的是橫穿植被林的一條路,蘇羨音猶豫地踩在鬆的泥土上,陳潯回頭了一眼:「放心吧,這條路上連雜草都沒有,這一塊兒學校打算改種櫻花林,10月份就開工。」
「哦,學校負責園林建設的也有你的人脈?」
陳潯被逗笑,挑挑眉說:「你猜。」
「我都答對了我還猜什麼?」
「我只是路過的時候,跟負責工程的園藝師聊了幾句而已。」
陳潯跟誰都聊得來,不是這一刻才知道,卻是這一刻才有深刻會。
「我要是被蟲子咬了,下周的創業作業是不是也可以給你了?」
「好說。」
他今晚好像溫地不像話。
月也清明,氣氛也旖旎。
步伐越邁越慢,希這路越走越長。
陳潯一路將送回宿舍樓下,他們話題沒有斷過,蘇羨音的心跳沒有慢過。
Advertisement
到了宿舍樓下,明晃晃的燈卻照得蘇羨音有些不適應了,那些隨著晚風漂浮而影影綽綽的心事好像也要原形畢,兜不住了。
陳潯:「那我就先走了,你早點休息。」
「好。」蘇羨音木木地說。
他卻笑了,帶點調皮意味,勾勾角:「你怎麼不說『好呀』?」
原來當時那聲笑也是他。
蘇羨音沒惱:「你這是在笑話我嗎?」
「算也不算」陳潯不賣關子了,「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你不會說這樣的話。」
「哦。因為我懟人冷臉還不給人臺階下是吧?」
陳潯本該說「對不起」,卻只是定定著的眼,說:「我可沒說。」
「今天晚上跟你聊得很愉快。」
「晚上確實是有點意外,當時準備拿了東西跟你說一聲再走,因為看到柏谷在跟你說話,我事又有點急就走了。」
「確實該跟打聲招呼的,是我沒考慮周到,不好意思。」
「沒事。」
蘇羨音著陳潯離開的背影,忽然覺得晚上笑話說「好呀」替擋住刺眼的輕傷口的陳潯,又退回了那個安全社距離。
他每一次滴水不理由得當的道歉,都將又推遠了一步。
這夜晚好得像一場夢。
……
陳潯人緣好是公認的事實,當時在南城附高,整個年級只要有人提到陳潯,一定會收穫好幾聲長一聲短一聲的「哦~他啊!」。
男生跟他混一片,生也暗暗折迷於他的芒。
有的人的存在,就是這個學校里最大的「傳說」。
蘇羨音早在高一之前見過他。
那是中考完的暑假,蘇羨音抱著青花瓷盒,經過長途跋涉,睡懵了眼,蘇橋扶著的肩,輕聲告訴這裏是新家。
蘇橋早就託人打理過,房子很大,也很新,但蘇羨音高興不起來。
沉默寡言地隨著蘇橋把行李一件件搬進去,父倆忙空的時候已經是傍晚,滿大汗。
蘇橋說帶出去下館子。
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環境,提不起興緻的心境。
蘇羨音手扶在車窗沿,看著窗外蔚藍的天空,巷子裏有掛著木牌的小賣部,門口有吃瓜納涼的老人,街角還有錯而過的把自行車騎得飛快的學生。
平心而論,南城的夏天很,像畫片里的場景。
但蘇橋帶著來南城,並不是因為這個。
飯桌上,蘇羨音見到了一個陌生的阿姨,孟凡璇。
不是小孩子,基本在見到人被蘇橋要求打招呼時就已經明白了這頓飯的主題。
這頓飯吃得並不算愉快,沒有表現出抵抗,但也不是順從,只是用沉默一次次加深蘇橋訕笑時臉上的壑。
結賬的時候,蘇羨音借口要出去買只筆,跑了出去。
蘇橋先走出來找到,低聲問:「羨音,你不喜歡這個阿姨嗎?」
蘇羨音當時的眼神很冷,疲憊的糟糕的心使口無遮攔:「我喜不喜歡不是不重要嗎?爸爸喜歡才是重點吧。」
「你什麼意思?」
蘇羨音嘆口氣:「我不是反對你,你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但是你是不是太心急了點?媽媽才走了不到兩個月。」
眼眶紅了,音調卻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幾乎是在質問了。
「我不是第一次見這個阿姨了。」
「那天在醫院,我都看見了。」
「你抱著阿姨的時候,怎麼沒有想過我會不會不喜歡不接?你為掉眼淚心疼的時候怎麼沒有想過媽媽在病床上痛得睜不開眼?」
「你是人嗎?」
決堤的不止的眼淚,還有蘇橋的怒火。
長到15歲以來,蘇橋第一次打,脆亮的一掌,白皙的臉上立刻起了清晰的紅印。
「你太不懂事了,羨音。」
蘇橋那時候的眼神未能讀懂,此後的三年,也沒有給過自己去理解他的機會。
有些隔閡就像一匹裂帛,手藝再妙,補過後都不再是原來的樣貌了。
蘇羨音跑掉的時候,聽見孟凡璇著急的聲音在後響起:「橋!你打孩子幹什麼?」
聲音被甩在後,眼淚就掛在兩頰,那是心裏的,說出來也不過是兩敗俱傷,也是慘敗的輸家。
跑累了,也不認識路,跑進一個幽靜的小巷子,就站在牆角,垂著腦袋,平復著呼吸。
不遠有人走的聲音,聽起來是幾個男孩,說說笑笑的。
學生時代是自尊心最強的時候,也是和異相最拘謹的時候。
於是臉不由自主熱了起來,恥包裹著,木著腦袋轉了個面,了一個面壁思過的姿勢。
聽見人越走越近,正在糾結要不要著頭皮往前走一點,還是就站在原地時,一隻好看的手遞過來一包紙。
蘇羨音不好意思接,更不好意思去看來人,只搖搖頭,期盼來人趕離開。
「我真服了」有男生在喊,「陳潯你就別老獻心散發魅力了行不行啊?要遲到了啊。」
就是這一聲,蘇羨音像一隻了驚的小兔子,倉皇間抬頭,陳潯把紙巾塞到手裏,沒有多說話,淺笑了聲小跑著走了。
他把書包斜背在後,一件白的普通t恤,背後有一隻米奇。
他手臂攬住側男生,一行人在巷口轉彎,路燈照亮陳潯側臉的那一刻,蘇羨音地攥住包裝紙的塑料外包裝。
乾淨俊朗的年,高挑瘦削的形掠過路燈,拖著長長的浮影,臉上卻是意氣卻又憊懶的笑意。
蘇羨音疑心自己聽錯,待一行人的聲音遠到聽不見了,才著紙巾按在自己口,確定震天響的「砰砰」聲就來源自腔。
這才後知後覺,剛剛他將紙巾塞到手上時,溫熱的指尖掠過食指第二關節,此刻那裏發燙髮熱。
比暑氣更甚。
的淚,卻已經幹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14 章

豪門老公破產后
阮顏從二十一歲大學畢業之后就嫁入豪門成功產子,過的是無憂無慮的闊太生活,誰也沒想到二十七歲這年,風云變幻。 她那位被稱為商業金童的總裁老公居然賠的連條褲子都不剩了。 一家三口身無分文被趕出來好不容易租到了房子,阮顏才發現了最大的問題,她看了一眼手里牽著即將入學一年級的小豆丁,懊惱道:“完蛋了,幼小銜接班還沒報!孩子讀一年級怎麼辦?” 尤其是小豆丁連拼音都認不全…… 看文提示:1、女主前期就是靠著美貌生子上位,介意請莫點。 2、本文多會描寫幼小銜接教育課文的事情,比較細水長流,旨在讓大家了解孩子多麼需要家長陪伴。 3、適當狗血,增加戲劇性,大家莫介意。
26.1萬字8 9131 -
完結285 章

掌中嬌
陳喋十六歲那年在街邊初遇聞梁,少年手上把玩著帽子,雙眸漆黑,居高臨下站在她面前。半晌,他傾身而下,黑眸對上她視線。“跟我走嗎?”少年說。陳喋真就跟他走了,這一跟就是六年。眾人皆知聞梁桀驁難馴,玩世不恭,卻傳聞家裡有個美人兒,還是電影學院校花,美艷明媚,飄渺跳脫,性子也被他養的驕縱任性。兩人各取所需,在心知肚明中如膠似漆恩愛多年,然後陳喋大學畢業,瀟灑揮手說“再見。”比當年點頭跟他走時更絕決利落。聞梁點煙,在一片青白煙霧中抬眸勾唇,冷冷讚她:“很好。”陳喋走後,聞梁照樣過的風生水起,不受影響。人人都感慨這聞少爺薄情冷血,就是在一起這麼多年也不過如此。卻在某天爆出來的花邊新聞中看到了兩人身影——深夜街頭,當紅新小花旦陳喋狠狠扇了新片最大投資方一巴掌,打的人半晌沒轉過臉。陳喋打完那一巴掌,抬手隨意攏了把長發,風情萬種,溫柔道:“聞總,我想我們早就分手了。”男人非但不怒,反倒倚車舔了下唇,誇獎道:“我的小豹子,動起手來都這麼厲害。”陳喋神色疏離的看著他,沒說話。旁人眼裡向來玩世不恭的聞梁,卻是沉默片刻,眼圈慢慢紅了。他雙手微顫著、小心翼翼的把人摟進懷裡,嘴上念著只他一人知道的小名:“靈靈乖,跟我走吧。”
41.7萬字8 4998 -
完結15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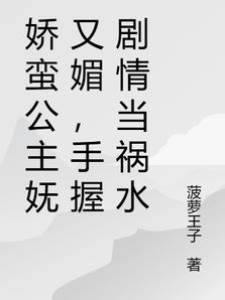
嬌蠻公主嫵又媚,手握劇情當禍水/嬌蠻公主以色爲誘,權臣皆入局
【釣係嬌軟公主+沉穩掌權丞相+甜寵雙潔打臉爽文1v1+全員團寵萬人迷】沈晚姝是上京城中最金枝玉葉的公主,被養在深宮中,嬌弱憐人。一朝覺醒,她發現自己是活在話本中的惡毒公主。不久後皇兄會不顧江山,無法自拔地迷上話本女主,而她不斷針對女主,從而令眾人生厭。皇權更迭,皇兄被奪走帝位,而她也跌入泥沼。一國明珠從此被群狼環伺羞辱,厭惡她的刁蠻歹毒,又垂涎她的容貌。話本中,對她最兇殘的,甚至殺死其他兇獸將她搶回去的,卻是那個一手遮天的丞相,裴應衍。-裴應衍是四大世家掌權之首,上京懼怕又崇拜的存在,王朝興替,把控朝堂,位高權重。夢醒的她勢必不會讓自己重蹈覆轍。卻發覺,話本裏那些暗處伺機的虎狼,以新的方式重新纏上了她。豺狼在前,猛虎在後,江晚姝退無可退,竟又想到了話本劇情。她隻想活命,於是傍上了丞相大腿。但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再也沒能逃出他掌心。-冠豔京城的公主從此被一頭猛獸捋回了金窩。後來,眾人看著男人著墨蟒朝服,明明是尊貴的權臣,卻俯身湊近她。眼底有著歇斯底裏的瘋狂,“公主,別看他們,隻看我一人好不好?”如此卑微,甘做裙下臣。隻有江晚姝明白,外人眼裏矜貴的丞相,在床事上是怎樣兇猛放肆。
27.8萬字8 4517 -
完結140 章

嬌軟美人和她的三個哥哥
沈家滿門英烈,只剩下雲黛一個小姑娘。 晉國公感念沈父的救命之恩,將九歲的小云黛收爲養女,接進府中。 入府當天,晉國公領着雲黛,對他三個兒子說:“以後這就是你們的小妹妹,你們要寵着她,護着她。” 謝大高冷寡言,看她一眼:“嗯,知道了。” 謝二溫柔儒雅,輕搖紙扇:“小妹好。” 謝三鮮衣怒馬,擠眉弄眼:“以後哥哥罩着你!” 面對性格各異的三位兄長,寄人籬下的雲黛怯怯行禮:“兄長萬福。” * 時光荏苒,雲黛出落得昳麗嬌媚,絕色傾城,無數世家公子爲之神魂顛倒。 謝二爲她寫情詩,謝三爲她跟其他公子打架。 他們私心裏,都不想再拿她當妹妹。 就在各路桃花氾濫之際,有大淵戰神之稱的晉國公長子謝伯縉攬過雲黛的腰,帶到謝二謝三面前,平靜宣佈:“叫大嫂。” 謝二謝三:???
61.5萬字8.18 13814 -
完結101 章

撩你成婚
秦家大小姐秦姝膚白貌美,明豔動人,楊柳細腰名動南城,只可惜長了張嘴,驕縱任性,仗着家世誰都不放在眼裏,還單方面宣佈解除和沈家大少沈故的婚約。 秦家投資失利,瀕臨破產,秦姝在名媛圈淪爲笑柄,爲了保住家族企業,秦姝準備接受家族安排,向前未婚夫沈故求助,重新和沈故聯姻。 爲了秦沈兩家聯姻,秦姝對沈故關懷備至,費勁心思追了他好幾個月,也沒得到迴應,決定放手一搏,直接求婚。 晚上秦姝抱了捧玫瑰花,敲開沈故的房門,眼神真摯,“沈總,可以和我結婚嗎?” 男人深邃的眼眸打量着她,嗓音低沉慵懶,“會叫老公嗎?” 秦姝臉一紅,咬咬脣,“我會。” —— 新婚夜,夫妻倆一個在床上,一個在沙發上,各玩各的,不知過了多久,秦姝漸漸支撐不住睏意,床上的男人拍了拍身邊的位置,喊她睡覺,秦姝心裏一緊,強撐着把眼睛睜到最大,“你睡你的,我這個人,生來就不愛睡覺。”
15.8萬字8.18 554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