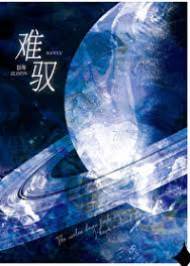《名門豪娶:大叔VS小妻》 第6章 006:順路送你
醫院。
葉傾心躺在病床上,小臉白得明,脆弱又無助的樣子,看著特招人疼。
「沒什麼大礙,就是有些低糖,又了點驚嚇,輸點葡萄糖,睡一覺,醒了就好了。」
醫生說完就退了出去。
低糖?
景博淵眸微斂。
看著葉傾心。
不知道是不是淋了雨的緣故,雖然護士已經幫換下了服,還是有些發抖。
景博淵起,拿了塊讓羅峰買來的新巾,去衛生間用熱水浸,作輕地給葉傾心了臉和手。
巾過的耳際,那塊紅心形的胎記映他的眼簾,他的手微頓,然後又神如常繼續手中的作。
站在一旁的羅封簡直要驚掉自己的下。
跟在景博淵邊十年,他第一次看見景博淵這麼細心地照顧一個孩。
景博淵因為居高位,平日裏嚴肅、不茍言笑,有時候甚至有些不近人,他從來不知道景博淵居然也會有溫照顧別人的時刻。
「看夠了?」
景博淵忽然出聲,聲音平淡,卻嚇得羅封一個激靈。
「看夠了……呃,不是,要不景總先回去休息,我在這守著?明天一早還有會議……」
景博淵默了一瞬,丟掉手裏的巾,說:「去把張嬸接過來。」
張嬸是他私人別墅的傭人。
人照顧人,方便一些。
葉傾心醒來時,已經是第二天早晨。
「葉小姐醒了?起來洗漱,吃點早餐吧。」
陌生的聲音,陌生的環境,都讓葉傾心心生警惕。
Advertisement
不聲四下打量。
房間佈置緻清雅,生活設施一應俱全,像有錢人家的臥室。
「別擔心,我不是壞人。」張嬸看出葉傾心眼中的警惕,笑著解釋道:「昨晚是景先生的車撞了你,也是景先生送你來醫院的。」
又自我介紹:「我是景先生別墅的傭人,姓張,不嫌棄的話我張嬸就可以。」
這裏是醫院?
葉傾心心裏詫異,但是面上沒有表現出來。
不聲又打量房間一遍。
大概,這就是傳說中的VIP病房?
只是……
「景先生?」是哪個景先生?
張嬸笑笑,說:「你一定聽過景先生的名字,景博淵,聽說過吧?他很厲害的……」
拉拉,一頓誇讚,張嬸那語氣,與有榮焉,就跟裏的景先生是的兒子似的。
葉傾心聽得有些頭大,輕輕打斷的慷慨激昂:「我想起來今早有課,我就不打擾了,幫我帶句謝謝給景先生。」
說完利落地找到自己的服,去衛生間換服。
換到一半,忽然想起來自己的服是誰換的?
甩甩頭,一定是張嬸換的,要不就是醫院的護士。
換好服,掬了捧清水簡單洗把臉又漱了口,理了理頭髮,走出衛生間向張嬸告別。
「醫生說你低糖,景先生也囑咐我一定要讓你吃早餐,葉小姐你還是吃點東西再走吧。」張嬸說得很誠懇。
葉傾心看了下牆上的鐘,「真的來不及了,謝謝張嬸的好意,再見!」
Advertisement
看著被關上的門,張嬸搖了搖頭,嘆口氣。
拿出手機給景博淵去了個電話:「葉小姐什麼也沒吃就走了。」
電話那邊淡淡地『嗯』了一聲,就好像說的不是什麼要的事兒。
掛了電話,張嬸又嘆了口氣。
照顧景博淵的飲食起居也有十幾年了,他一直沒個對象,本以為昨晚連夜讓來照顧的是個不同的,怎麼都這麼冷淡呢?
景先生冷淡能理解,他居高位,早就把緒控制得收放自如,但是那個葉小姐,年紀輕輕的小姑娘,聽到景先生的名字居然那麼淡定,還是頭一回見到。
昨夜下了一夜的雨,今晨一早就放了晴。
葉傾心踩著積水,趕往最近的公站。
醫院離地鐵口比較遠。
風吹在臉上,像刀片刮似的。
葉傾心了上的服,驀然愣了一下。
昨晚雨勢不小,在雨中走了許久,服一定了,冬天服厚,只一夜就幹了?
可能是張嬸幫弄乾的。
葉傾心抿了下,不知道細心的是張嬸,還是景博淵……
滴——!
一聲鳴笛忽然在耳邊響起。
葉傾心轉頭。
一輛白路虎停在跟前。
副駕駛車窗緩緩降下,出景博淵深邃立的臉。
男人穿著剪裁合的黑西裝,白襯衫,暗紅格子領帶,細碎的短髮一不地往後梳著,薄嚴肅地抿著,眼神深沉又淡然,散發著三十幾歲的男人特有的持重的魅力。
Advertisement
「回學校嗎?順路送你。」
葉傾心一見到他,就有種見到嚴父的覺,聽到他的話,疑地愣了一下。
順路?
景博淵並沒有打算做過多的解釋,只一探將副駕駛車門打開,說:「上車。」
用他慣用的命令式語氣。
葉傾心這次沒有遲疑,直接上車。
景博淵都已經做到這個份上,要是再推,就顯得不識好歹。
跟他本就不是一個世界的人,自然是沒有共同話題可說,一路上車的氣氛沉默。
鼻尖縈繞著似有若無的香煙味,大概是他之前過煙。
葉傾心有些拘謹。
景博淵或許是看出了的拘束,手打開音樂。
舒緩的音樂在車回開來,葉傾心暗暗吐了口氣,有了音樂,不那麼張了。
快到B大門口的時候,手機響起來。
是景索索。
「心心啊,我聽薇兒說你昨晚沒回來啊?哪兒去了?」
劈頭的詢問,葉傾心一愣,剛要回答,景索索自顧自又說:「等會兒回來上課吧?路過『都一』的時候幫我帶他們家的蟹燒麥和宮廷酸,你哦麼麼噠!」
葉傾心:「……」就知道沒那麼好心關心自己。
掛了電話,一抬眼,正好『都一』的招牌從視線里越過去。
急之下口喊:「哎!停車!」
景博淵急剎車,車停穩后,他轉頭看向葉傾心,「怎麼?」
葉傾心在他的注視下又張起來,「我、我要給我舍友買早點,要不您先走吧,我買完了可以坐公回去,您不用管我。」
Advertisement
說完等了一會兒,見景博淵沒有要開口的意思,不準他心思,只好道了句「再見」,打開車門下車。
踩著積水走到『都一』門口,想起什麼似的,拿出手機撥出一個號碼。
那邊很快接聽,電話里傳來竇薇兒的聲音,「喂?心心,你昨晚哪兒去了?給你打電話也不接,沒事兒吧你?」
葉傾心莞爾一笑,抬手將被寒風吹的碎發順到耳後,說:「我沒事,正要去『都一』給索索買早點,打電話問問你吃早餐了沒?沒吃的話給你帶這裏的燒麥,我記得你也喜歡吃。」
竇薇兒語帶笑意,說:「你沒事就好,我吃過了,不用給我帶,買完就快些回來吧,要上課了。」
葉傾心『嗯』了一聲,掛了電話。
猜你喜歡
-
完結1877 章

老公寵妻太甜蜜
十九歲的蘇安安被渣爹逼嫁給三十一歲的顧墨成。當天晚上她被化成餓狼的顧墨成壓榨得筋疲力盡,「不是說不行嗎?」「都是三十多歲的老男人,也不知道節製。」蘇安安扶著快斷的腰表示不滿。顧先生生氣,又壓了過去,「繼續!」婚後,顧先生開啟護妻寵妻模式。「老公,渣爹又想打我!」「等著!」顧先生惱了,直接把蘇家端了。「老公,她對我下藥,想把我送給其他男人!」
336.9萬字7.79 263966 -
完結186 章

惹草
初識,他是她同學的小叔,不經意的一瞥,淡漠從容,風度翩翩,從此被吸引。 而後,她為生存步步為營,滿腹算計,鐵了心要拉他入深淵。 直至車內熱吻的八卦新聞曝光,全城嘩然。 平日裡自持矜貴的許先生,竟也有淪陷的時候。 圈內好友都調侃,許先生偷偷養了個嬌美人,捧在心尖上護著,誰都碰不得。 風波雲湧起,他為她遮風擋雨、遇佛殺佛;而她亦敢為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隻為守住誓約——與你,歲歲年年。 腹黑魅惑可婊可颯的妖精vs成熟沉穩清冷矜貴似仙官
33.9萬字8 17944 -
完結499 章
離婚后,極品前夫跪求我復婚
做了三年賢妻的裴太太突然要離婚。裴祈:“理由。”蘇閔婕:“你沒達到我的期望,我選擇止損。”當天晚上,蘇閔婕在酒吧玩瘋了。裴祈將人堵在過道里,半瞇著眼睛警告,“差不多就行了,我的耐心很有限。”蘇閔婕更不耐煩:“趕緊簽字,大家好聚好散別鬧太難看!”她被人陷害,一夜之間被推至風口浪尖上,落了個‘海王富太’的名聲。裴祈以為蘇閔婕會來求他,結果,被她和死對頭聯手拉下水。后來,看著各界精英大佬,一個
87.5萬字8 174802 -
完結154 章
嬌攀
岑旎第一次遇見穆格,是在南法的地中海峽灣。男人骨相偏冷,點煙時姿態閒散矜貴,玩世不恭的輪廓卻透着幾分東方人獨有的柔和。“要不要來我這。”他說。岑旎挑眉,“你那有裙子換?”“沒有。”男人回答得理直氣壯,“但可以有。”成年人之間的你來我往,就好像是一場猜謎,不說破也不點透,你我心知肚明。那一晚他開敞篷跑車,載着她一路沿海邊懸崖兜風,彎下腰替她腳套上小高跟。倆人在夜風的露臺前擁吻,火花一擦而燃。普羅旺斯的花海是藍色的,就像初見時候的藍霧。短暫的相處過後,岑旎重歸理智。一時興起的相處,彼此就應該相忘於浪漫的初始地。但岑旎沒想到男人和女人之間,有時候確實有緣份。完全泯於人海後還是碰到了。
23.9萬字8 7407 -
完結169 章

溫先生的心尖月
(蓄謀已久 細水流長 甜寵 雙潔 無虐 年齡差五歲左右)(女主醫生,非女強)*【溫婉清麗江南風美人 & 內斂沉著商圈大佬】容煙出身書香門第,自小跟隨外公生活。聽聞外公給她尋了門親事,她原以為聯姻對象是同為醫生的溫二公子,殊不知卻是接管溫家的溫景初。煙雨灰蒙,寺廟裏,容煙瞥見與她擦身而過的男人。上一次見他還是四年前,可他從不信神佛,為何會出現在這裏?朋友生日聚會結束,溫景初送她歸家。車內,容煙壓住心中疑惑,終究沒問出口。*容煙本是溫吞的性子,喜靜,信佛。她自認為婚後的兩人是相敬如賓,搭夥過日子。而他卻步步誘她淪陷。某日,容煙在收拾書房時看到了寺廟的祈福袋,裏麵白色宣紙上寫著她的名字,似乎珍藏了許久。而此時溫景初正接受電視臺采訪,清肅矜貴,沉穩自持,淡定從容與人交談。主持人問,“溫先生,聽聞您並不信神佛,但為何每年都到靈山寺祈願?”容煙手中拿著祈福袋,略帶緊張的等待著他的回答。男人黑眸如墨,思忖片刻,緩緩啟唇,“因為溫太太信佛。”簡單一句話卻擾亂她的心。
33.1萬字8.09 23285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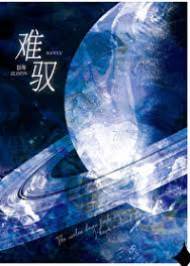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18 110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