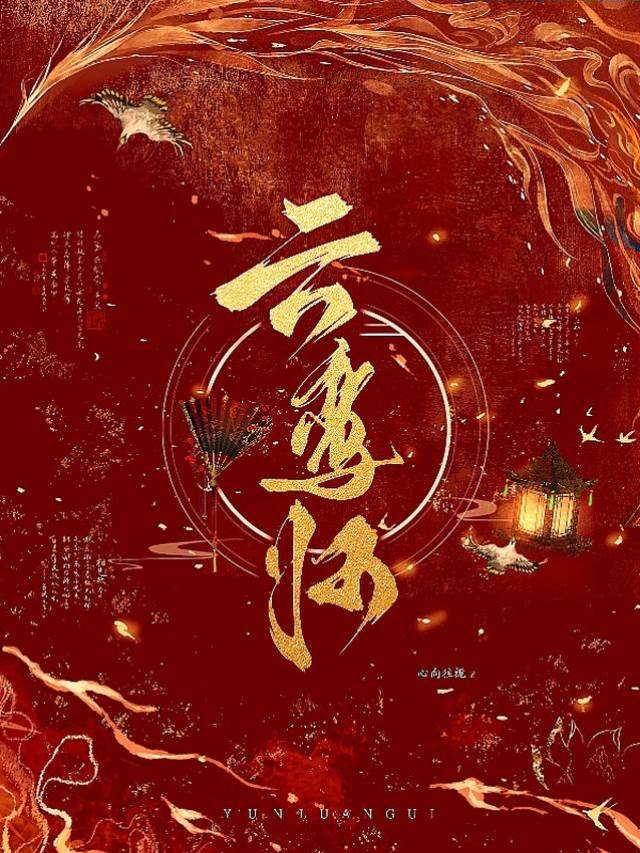《求魔》 [求魔] - 第11節
口,是不是給我施什麽法了?”
酆業冷淡瞥:“我以為你要等被賣了才能察覺。”
時琉有點不好意思:“我不懂修煉,也沒有這方麵的經驗……對了,”想起什麽,轉了轉,“這裏是酒樓嗎?時家的長老來這裏做什麽?”
“酒樓?”
酆業嘲諷地睨了一眼,確定已經離那種低級的幻,恢複清明,他也鬆了手腕,垂手上樓。
隻餘聲音懶散飄進耳中。
“你見誰家酒樓,是著坐著懷對喂酒?”
“?”
遮蔽時琉五神識的法被酆業一收,時琉眼前一切恢複樓景。
酆業領上的是男客這邊。
站在木梯上,放眼下去,單一樓樓下正對著,就有好幾對男在酒桌案後,坐著滾著抱著親著,弄得一桌瓜果狼藉,難蔽。
“!”
時琉懵完,驚啊一聲,捂著薄皮泛的臉慌不擇路就往樓梯上跑。
“砰。”
酆業停在二層木梯口,被撞在後背上。
像隻小飛螢撞到龍尾上,連片鱗片都撼不,自己倒是差點彈跌下去。
一點鬆散笑意被撞得潰散眼底,酆業薄勾了勾,手把沒見過世麵的傻貓崽又拎住了。
視重新給封上。
時琉這才稍稍心安,攀著酆業袍袖下的手臂,像是著柄淩厲的劍骨。
兩人一路上到四層。
四層木梯口有兩個攔著的,酆業懶得多說,在樓外收下的袖珍木牌一抬,兩人立刻作禮讓出空隙。
四層有些不同。
一踏上來,耳旁的靡靡之音就化作清樂,空氣中還飄著墨香,文雅悠揚。
時琉聽得心裏一,拉了下酆業的袖子。
酆業淡漠掃過樓中,然後才鬆了手,撤掉遮蔽視的法。
“這裏不一樣哎。”
時琉驚歎,稍走前些——
Advertisement
長垂的紗簾後,影影綽綽的,可見有子在簾後琴的影,琴曲如訴,撥人心。
這樣的簾子在這層偌大的樓中不止一塊,環作半圈,這樣的子也遠不止一位。
而樓中相對,還掛了兩幅大字——
“風”“雅”。
酆業淡淡掃過幾空了的簾後,又瞥向另一邊,連排客房中閉的房門。
一點冷淡嘲弄掠過他眼底。
恰在這會兒,好奇繞了一圈的小姑娘又通紅著臉頰像被野豬攆了似的飛快跑回來——
後正是某扇閉的房門。
時琉顯然也看見那兩個大字了,停在酆業旁後,憋了口氣,半天不知道說什麽。
酆業垂睨,似笑非笑:“聽見什麽了?”
“……”
時琉繃著紅得滴的臉,不肯說話。
停了幾息,輕蹙著眉看向“風”“雅”兩字,不知道嘀咕了句什麽。
酆業挑眉:“不喜歡?”
“…別扭。”時琉小聲。
“自然別扭。”酆業嘲弄抬眼,“拿來賣弄的,是風塵,風,唯獨不配風雅。”
“嗯!”
時琉深以為然重重點頭。
然後就見青年懶歪了下頭,似乎是想到什麽,他大氅下左手一抬,袍袖垂跌,出淩厲冷白的腕骨。
修長指節輕輕一——
“哢噠。”
一聲清脆的指響。
兩朵猩紅的火苗忽然憑空跳出,刺破“風”“雅”掛畫前無形結界,燒上字幅一角。
嘩。
火舌淩空躥上。
時琉驚著劇烈燃燒的字畫,又轉回來,仰頭看了看側那人。
猩紅的火映在他漆黑瞳底。
灼穿了幽暗滾燙的夜,出裏麵一點瘋狂又冷漠的愉悅。
一眨眼功夫,那魔焰似的火就將兩幅字畫付之一炬,燒得灰都沒剩下。
漆黑眸子裏的滾燙也隨之熄滅。
“走了。”
酆業又恢複平常那副冷淡懶散的模樣,他淡淡轉,朝樓梯走去。
Advertisement
時琉回神,驚得左右張——可偌大四層,來往稀疏的客人,甚至是樓梯旁的守衛,竟然好像沒有一個人看到酆業方才做了什麽。
在原地停了許久,向酆業的眼神更猶豫。
但幾息過後,還是搖了搖頭,甩掉那些雜的思緒,徑直跟了上去。
這通天閣,一層客人過一層。
第五層似是樓花魁的起居所在,隻是此時空,不見人影,除了流連於天欄桿夜的野鴛鴦們,沒幾個在這層停留。
酆業領著時琉一路上到六層。
踏上最後一節臺階,他眼神微幽:“不在。”
“還不在?”時琉回頭,輕聲,“再往上就是七層了,樓外那人說是他們閣主的地盤,非請不能。難道時家長老和通天閣主有關?”
酆業未置可否,徑直踏進了六層。
比起五層極盡奢靡的布置,六層完全稱得上空——
除了角落幾張木質桌案之外,別無長。
沒了遮擋,六層所有客人一目了然,互相都能看個清清楚楚。
沒擺置、沒花魁、沒樂子,尋常客人上來一圈很快就失地原路返回了,整個六層加起來也沒多人。
由此,時琉第一眼注意到的就是一麵牆壁前,聚堆站著的幾個年輕人——
長袍束帶,冠玉佩劍。
怎麽看都是凡界仙門修者的打扮。
時琉正好奇地遠遠著,就對上其中一個四張的男弟子的眼睛。
對方遠看見,愣了下,表頓時古怪起來。
“時蘿?你是怎麽找到我們的??”
時琉一瞬茫然。
……?
這些修者,和這的主人是認識的?
隨著那個方臉男弟子的話聲,圍在牆前的年輕修者中,有好幾位也前後轉過來。幾人見時琉,但都沒說話,表眼神也都或多或地有些微妙。
Advertisement
可惜時琉並未注意,猶豫了下,自覺地沒連累酆業,朝他們走近:“…師兄好。”
——這些年輕弟子和時蘿同為修者,看著都稍長些,時琉自忖這樣的稱呼應該沒什麽問題。
沒想到剛說完,那方臉弟子嘿嘿一笑:“可別啊,我們是萬萬不敢當你師兄的,萬一再讓你借著我們纏上晏師兄,那晏師兄還不得——”
“師弟。”
一個溫和但低的嗓音截斷方臉弟子的話。
年輕修者們不約而同往兩邊讓,空出了通往最裏的牆前,一位月白長袍的青年公子走出來。
若不是所有人以之為首,那時琉大概會以為,走出來的是個沒有修為的儒雅文士——
站在一群氣勢淩厲的佩劍修者中間,獨那人手執折扇,玉骨如竹,一雙長眸溫和斂著。眼神也猶春日江水,滔滔盡藏,隻餘波。
世上竟真有這樣一雙天生便多的眼睛。
時琉訝異地想。
隻是……
為什麽看著這雙眼睛,就總覺得這人有些似曾相識呢?
時琉苦思也沒得結果,隻能安自己,多半是時蘿認識這人的影響。
而此時,青年文士似的公子已經停下,他微微側過,低掃過方臉弟子:“不得無禮。”
袁回的方臉弟子抱著後腦勺轉開:“哪是我無禮了,之前這小姑娘仗著咱們和時家早有盟約,不過就是被師兄你救了一次,都快糾纏到山門來了。”
他悄然白了時琉一眼,撇:“到了幽冥都甩不,可真嚇人,別是在師兄你上下了什麽——”
“袁回。”
折扇輕敲玉骨,青年嗓聲低了三分,“你又想挨罰了是不是?”
“……”
方臉弟子不知道想起什麽,臉都綠了,立刻閉口不言。
時琉尷尬地站在原地。
聽出來了。
Advertisement
這的主人,時蘿,喜歡麵前這個看著就很儒雅隨和的公子,還苦苦糾纏過人家。
但顯然落花有意流水無,搞得人家師弟都看不爽。
可現在連這人是誰都不知道。
這,這該如何是好。
時琉苦惱得不行,扭頭去看封鄴,想求他提示,可這會兒才發現那人早就無關人一樣,繞著這六層形狀奇怪的牆壁轉圈看去了。
連求救的眼神信號都被徹底無視。
時琉無意識鼓了鼓腮。
小姑娘站在原地,支吾半天,雪白側頰都憋得微紅,還是沒能說出一句完整的話來。
折扇公子瞥見了,正覺無奈又好笑,剛要開口替解圍——
“對、對不起,這位師兄,”時琉終於艱難憋出了說辭,“我,我前幾日隨族中曆練,不小心了點傷,傷了嗯,腦子。”
時琉終於憋完自己的謊,敢抬頭去看折扇公子了,“敢問師兄,如何稱呼?”
折扇停在掌心,那雙溫多的眼眸詫異地著時琉。
——
大概也是沒想到自己能親耳聽這樣拙劣的謊言。
好在這位公子心善,沒笑。
但他後麵那個方臉的顯然不太善良,撲哧一聲就樂了,轉回來捧腹:“時蘿,這才幾日不見啊?你又換了個新法子糾纏我們師兄?編你也編個不離譜的啊——玄門第一公子,晏秋白,你們時家還有不認識他的??”
“……?”
時琉這次是真懵了。
——晏秋白?
在茶館聽書裏聽到的那個第一仙門的天之驕子,將來要和時璃定下婚約的,晏秋白?
“再讓我聽一遍那個稱呼,袁回,你就在寒水澗練上百年再下山吧。”
晏秋白回過,“時蘿師妹,袁回玩笑之言有失分寸,冒犯之,我代他向你道歉。”
時琉堪堪回神,下意識抬手,擺了擺:“不……”
“道歉?”
像俯在極近的耳邊,有人低低一嗤,嘲弄語氣薄涼得人心裏一冷——
“道歉有用麽。”
著驀地沉冷下去的話尾,錚的一聲清鳴。
時琉聽過,知道那是一道笛音。
可笛音如劍。
“轟——”
無形劍風轟過袁回畔,牆上陡然拓出一道尺長白痕。
與之同時。
驚傻了的袁回呆呆站著,半角袍袖卻平整如割地,慢慢裂開,飄落。
玄門一眾年輕弟子此時才剛回過神,全都著地上的那片角,臉大變。
唯獨正前,晏秋白手中折扇不知道什麽時候打開了一半,那雙如春水般的眸子此刻微微浸涼,他斜過臉,向時琉的後——
翳裏多了一道影,像憑空出現。
該是極快的。
可那人肩上玄黑大氅紋未,連袍角都不曾有一風拂。
終於有弟子反應過來,大惱拔劍:“閣下什麽人!出手為何如此不留麵?可知我們是玄門——”
“噓。”
翠玉長笛隨手一拂,在酆業掌中
猜你喜歡
-
完結520 章

九重紫
窦昭觉得自己可能活不长了。 她这些日子总梦见自己回到了小时候,坐在开满了紫藤花的花架子下摆动着两条肥肥的小腿,白白胖胖像馒头似的乳娘正喂她吃饭……可当她真的回到小时候,人生又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九重紫》,讲述一个重生的故事!
148.6萬字8 38130 -
完結311 章

夫郎家的贅婿首輔
黎大是西坪村數一數二的富戶人家,妻子早逝,膝下只留了個獨子哥兒黎周周。 「掙那麼多錢有什麼用,只有個哥兒」 「哥兒是要嫁人的,錢都是給了外人了」 黎大將村裡說閑話的罵了回去。 「我家周周是要招上門婿的」
163.9萬字8 16445 -
完結122 章
回到丈夫戰死前
【正文完】翁璟嫵十六歲時,父親救回了失憶的謝玦。謝玦樣貌俊美,氣度不凡,她第一眼時便傾了心。父親疼她,不忍她嫁給不喜之人,便以恩要挾謝玦娶她。可畢竟是強求來的婚事,所以夫妻關系始終冷淡。而且成婚沒過多久永寧侯府來了人,說她的丈夫是失蹤許久的永寧侯。情勢一朝轉變,怕他報復父親,她提出和離,但他卻是不愿。隨他上京后,侯府與京中貴眷皆說她是邊境小城出身,粗俗不知禮,不配做侯府主母,因此讓她積郁。
38.4萬字8.18 21582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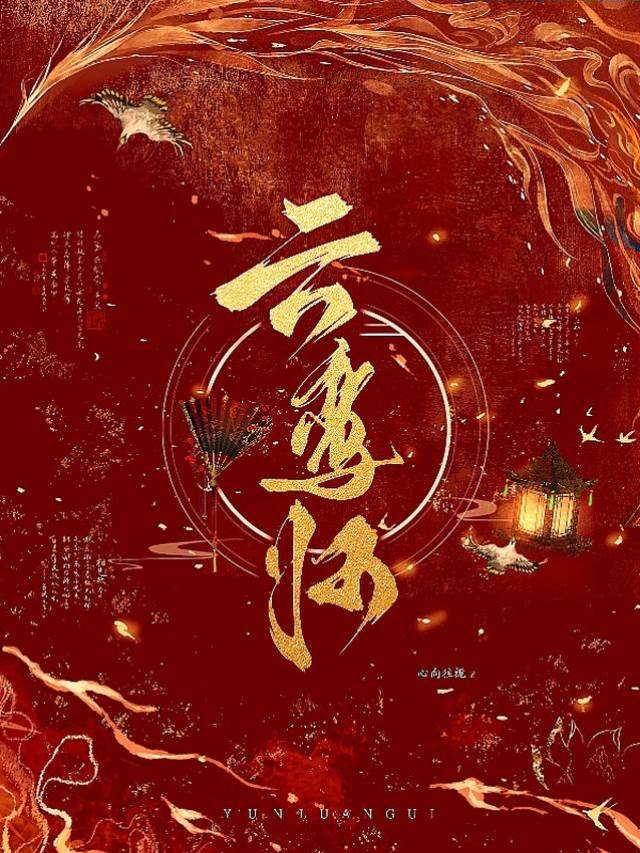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1130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