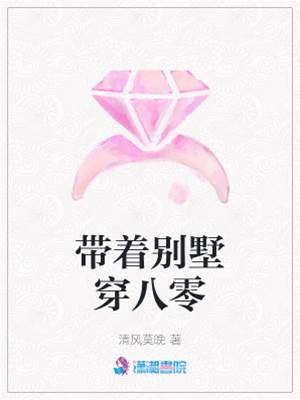《馥欲》 17.淫媚而又清高
宴會場的停電隻持續了很短的時間,所有來賓的恐懼都尚且沒來得及發酵開,隨即便恢復供電,回到了剛才燈火通明的狀態。
工作人員進來解釋剛才那一瞬間因電不穩導致斷電,新郎和新娘接過旁人遞來的話筒向所有來賓道歉。
這一小曲就這樣落幕,舞會環節結束,晚宴秩序恢復,誰也沒有注意到方才的舞池中悄無聲息地空出了一塊地方,了兩個人。
二樓,男人懷裡抱著已經若無骨的小人,直接闖進一間空的休息室反鎖房門,低頭重新與吻到一起去的時候手索著旁邊燈的開關,不耐煩地全數按下。
昏暗的房間頓時一片大亮,兩人激烈纏吻,寧馥被宋持風半推半抱著往裡走,禮服的後拉鏈已經敞開,只剩下兩纖細的吊帶還勾在瘦薄的肩頭。
隔壁的房間就是休息室的臥室,但宋持風就連走進去的耐心都沒有,直接將人在了靠外的沙發上。
齒的狂風暴雨間,寧馥雙隔著禮服被男人握進掌心,作又急又狠。兩吊帶經不起折騰,就這麼可憐地折在了宋持風手裡。
宋持風卻對此毫沒有半分憐憫,手將上禮服往下一扯,寧馥口一片刺眼的白便暴在他眼前,只剩雙頂端被嚴嚴實實地封在之下。
他俯下,一邊的一邊吻脖子,扯下握巍巍的雪白,連帶著嵌在小人雪白上的兩點玫紅一並欺凌,拇指將的尖兒狠狠摁進裡打轉兒。
寧馥微微側過頭去躲了躲男人烘人的呼吸,臉又被強地掰回來,再以雙承接他挑逗的吻。
到最後寧馥避無可避,舌尖被他纏上,被吻得香汗淋漓,春水漾,間一片泥濘。雪白上全是男人凌的指痕,綿雪仿佛要化在男人手中,尖兒如同盛開的紅梅,在男人指尖綻放出靡的豔麗。
Advertisement
是被就得心神恍惚,眼前蒙上了一層模糊的水,雙被人打開時水黏連花瓣,壯的抵在外,頭部被一圈吮住。
兩人皆是火焚,鼻息也重得如同息,在空氣中比他們更快一步纏綿起來。
宋持風所有自律克制在這副景面前全都了空談,小臂暴起青筋,後腰繃塊,嘶啞聲音出的名字:
“寧馥——”
被從頭到尾貫穿的瞬間,寧馥張了張卻是沒出聲,舒爽得將所有呼吸都化作一聲短暫的喟歎。
一時之間,寬闊的休息室裡,充斥著的曖昧聲響。
攪,拍打,空氣的度大到驚人,仿佛將這一室響化作洪流,將沙發上合的一雙肢席卷其中。
男人猩紅的幾乎全部都沒了小人的雙間,被那滾燙的致包裹得眉頭不斷收。
頭頂在深,那裡全都是水,源源不斷的一大包被他堵死,麻地泡著他的頂端,他神魂震,心魂搖。
“你別這麼深……”
他膝蓋跪在沙發上,一雙手卡在寧馥的腰,將的屁抱起來,繼續發力狠。
寧馥的後腰在沙發上懸空,背拱一座煙雨江南中線條婉又堅韌無比的石橋。
“不喜歡深的?”
兩人的目在空中匯,熾灼地纏在一起。
如同剛才兩人還難分難舍的舌與急促又激烈的鼻息。
的依舊白皙如雪,細膩如玉,除去被他弄玩的雙,那些的痕跡幾乎只在的眼角眉梢淺淺浮現。
每一挑眉一抬眼,盡是青的嫵風,卻又仿若不可及的遠生姿搖曳的一抹豔麗。
那雙眸中的冰被融化,晃著漣漪,只是宋持風仔細進去,那漣漪之下的卻是這天底下至清之水。
Advertisement
明明就被他在下,每一滴水都是為他而流的。
一雙漂亮的眼睛裡卻好像看不見他,沒有,只有。
而又清高。
當這兩種可以稱之為兩個極端的神態同時出現在一個人上,宋持風的火在中幾乎要炸裂開來,哪裡還能再給習慣的時間,後腰發力拔出,再往裡頂的時候已如紅了眼的狼。
“我倒覺得是還不夠深。”
要不然哪還能讓是這副表。
沒有商量的余地,赤紅的柱狀如同燒紅的鐵,破開的口,搗開的,將的水攪一腔沸騰的膠,嚴合地將他們粘合在一起。
寧馥被一次一次從頭到尾貫穿,脆弱的宮口屢撞擊,從未有過的激烈驗脖頸發僵,後脊完全抻直繃,連帶著整個腦袋都往後仰了過去。
呼吸不斷抖,如同從繭蛹中掙扎而出的蝶,卻好像恥於出聲來一般咬住了下,任由他伏在上如何疾風驟雨地,聳,都只是急促地呼吸。
房間裡一時之間聽不見任何人聲,只有囊拍打在上的聲音,伴隨著攪水,壁,與此起彼伏的息。
搖搖墜又堅不可摧的才最激起人毀滅的。
宋持風手著的,咬牙往裡頂,下頜線條繃,凌厲,額角瞬間蒙上汗氣,眼神也變得銳利。
男人握住的,手指陷那種致命的,將肆無忌憚地在手中,下半不斷地衝撞,拍打聲如同愈發急促的雨點。
他是真發了狠,後腰繃鐵,一下一下仿佛恨不得將囊都一並送進的裡,水被拍打,拉,還來不及斷,便又在男人下一次頂的瞬間消失不見。
Advertisement
下人被得渾發抖,兩道好看的柳眉擰在一起,白的面頰呈現出出來的霧面,細細一看全都是汗。
那種的汗氣在兩個人之間發酵,宋持風爽得發瘋,腰眼酸麻一片,他憋足一口氣咬著牙搗進深,頭頂住深小口,總算得松口,在高出來的同時,小小地啊了一聲。
寧馥短時間高出來此刻微微失神,手抵在男人的口,被中的飽脹撐得不住發出難耐的輕哼,雪白口鎖骨如同漾開漣漪的水面,輕輕抖。
男人猩紅的巨幾乎全部被吞食進深,口被撐開,邊緣近乎明。
水裹挾著細的泡,緩緩流進中間,在皮上留下清晰而又的。
已經得到了短暫的滿足,而宋持風卻依舊如同一頭野蠻的,難耐並且永遠無法餮足的,剛才那一陣狂轟濫炸般的只不過是讓他嗅到了與的氣息,蘇醒了過來。
男人手指直白地的指間,將小人的手扣過的頭頂,下半又開始了新一肆意而蠻橫的撞擊。
寧馥大腦完全陷了空白,雙幾乎在這樣的衝撞之下沒了形狀,只剩下如水般晃的波,浮於之上那些凌的痕跡則更像是水面幾道綺麗且不真切的斑。
“嗯……哈啊……”
,息,囊的撞拍打,周而複始,無休無盡。
事後,爽到渾最後一力氣都用幹了的寧馥被宋持風抱進浴室,清洗乾淨後外面已經有人送來了新的服。
換服的時候想起剛才做的時候手機響了幾下,只不過當時沒空去管,現在才開始擔心是不是時慈發消息過來。
Advertisement
宋持風一眼便看的想法:“不會是時慈。”
“你怎麼知道?”
寧馥拿起手機,低頭一看,還真的不是。
“因為他第一次宣講很不理想,所以第二次安排在下周五了。”
宋持風抬手,把鬢角一縷發起,撥到耳後,手指描繪著耳廓的廓,了誠實的小耳垂,泰然地對上小人驚訝的目,語氣平淡:
“寧馥,我說過,只要你開口,就行得通。”
*
加更你們是想0:00還是明天20:00?
猜你喜歡
-
完結1069 章

贈你一世情深
我愛了他整整九年,整個少年時光我都喜歡追逐著他的身影,後來我終於成為了他的妻子,然而他不愛我,連一絲多餘的目光都不給我留。 …
199.8萬字8 286644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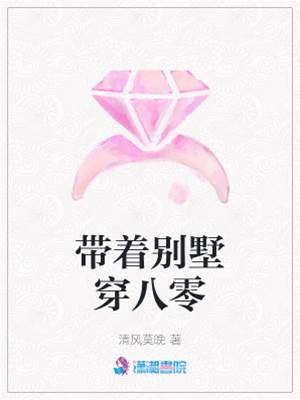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6488 -
完結180 章

正經養崽四年後,豪門親爹找上門
【雙潔】【甜寵】【養狼崽】獨自帶崽的第四年,孩子親爹找上門了。穿著講究的男人站在門邊,問她。“你是尚希?”“…是。”“我是幼崽的父親。”男人霸道強勢:“跟我走,不用想著拒絕、反抗那些沒意義的事情。”尚希盯著他那張和兒子酷似的臉,慢悠悠哦了一聲。其實她壓根兒…也沒想過拒絕、反抗啊。—辜聞明麵上是豪門辜家掌權人,暗地裏是狼人族家主,他在一次發情期提前三天,和走錯房間的純人類女人發生了關係。狼人族一生隻會有一個伴侶,但他討厭三心二意不忠的純人類,拒絕去找她。某一天,他聽到了幼崽呼叫聲。他才知道那個純人類生了幼崽,狼人幼崽正在經曆骨骼發育艱難期。為了幼崽,他把那母子倆接回家住。一開始,他冷冷地說:“我對你沒興趣,我們隻是孩子的父母。”“我隻在意我的幼崽。”兩人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幼兒園。一起參加學校旅舉行的親子活動。一起參加家長會。某一天,尚希去約會了。男人震驚發怒才發現自己的心意。他以帶幼崽出玩為由,斬斷她所有約會。他頻繁搜索:怎麼追求人類女人。他送樓、送車、送包、送飛機……都沒用。約定到了,女人帶著幼崽離開。傲慢的狼人家主,辜家掌權人徹底慌了
35.2萬字8.33 85939 -
完結198 章

退婚當天,我和渣男死對頭領證
父親入院,哥哥被未婚夫親手送進監獄。寧惜一怒退婚,當天便和渣男死對頭到民政局領證。她原本以為,這婚姻就是一場交易。誰想到,便宜老公太黏人。吃飯要她陪,出差要她陪,心情不好還要她哄睡……知道男人心里住著一個白月光,寧惜取出準備好的離婚協議,想要還對方自由。“離婚?”男人一把撕掉離婚協議,“我告訴你寧惜,我江律只有喪偶,沒有離婚。”寧惜……說好的白月光,說好的所愛另有其人呢?“白月光是你,朱砂痣是你……”男人一把擁她入懷,“自始至終都是你!”
35.7萬字8 4678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