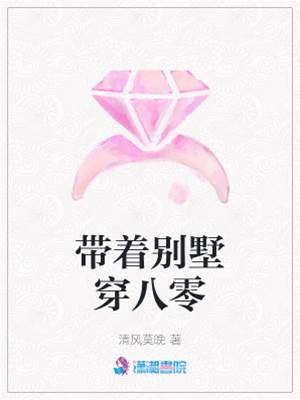《那就不要離開我》 第17頁
容嶼心里突然有點兒不是滋味。
是不是因為他天天讓閉……留下了什麼后癥。
“那個……”他想說,信寄沒寄到都不重要了,反正你人現在在我這里。而且事實上,只要你沒有忘記我,我就很開心了。
但……
容嶼咬牙切齒。
說不出口。
“我是想說。”站在原地艱難地做了很久思想斗爭,他垂眼,表有些不自然地,攤開另一只手的掌心,“我給你剝好了。”
——里面安安靜靜地,躺著兩顆剝開的草莓糖。
——
“那你說的這個事兒呢,就得從很久很久之前,倪倪走之前說起了。”
“倪倪小時候吧,遇到過一個特別垃圾的老師,總是針對——哦,這麼說可能容易被誤解,那個老師吧,喜歡針對所有長得好看的生。所以也算不上獨獨針對,倪倪只是眾多被針對的姑娘中的一個。”
“然后倪倪這個人呢,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小時候實在被家里人保護得太好了,所以一天到晚傻不拉幾的,覺得全世界都是好人……當然了,我這話你不要跟說啊。后來有一次,一個人坐公車上學,在車上遇到一個小——沒的東西,別人的來著。”
Advertisement
“結果你猜怎麼著?倪歌特別缺心眼,直接沖上去拽著那個人,說他是小。”
“你想想,那公車上的小都是團伙作案,怎麼能放了?所以一下公車,就被人拖小巷子里了。”
聽到這里,黎婧初忍不住驚訝地:“然后被打了一頓?”
“那哪兒能!”宋又川慶幸,“恰巧那時有大人路過,就把救下來了。”
黎婧初嘆氣:“那就好。”
“這事兒發生之后我們都心疼壞了,清時哥恨不得天天把倪倪送到教室座位上。結果,你知道那老師怎麼?那老師吧,天天拿這個笑話,到跟人講,‘我們班上有個姑娘在公車上犯蠢,差點兒被人打了一頓,簡直笑死我’。臥槽,你說氣不氣人?”
宋又川現在回憶起來,仍然恨恨的,“我們都覺得特別莫名其妙,差點約著清時哥,把那老師拖到小巷子里打一頓了。”
“不過那時候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倪倪太弱,不發燒進醫院。所以治病要,我們就也沒怎麼跟那老師較勁。”
Advertisement
……
黎婧初盤坐在沙發上,饒有興致地聽宋又川講過去的事。
搞清事完整的來龍去脈,問:“這些事,阿嶼他們全都知道嗎?”
“知道啊。”宋又川說,“從那時候起,他倆天天一塊兒上下學。”
黎婧初眼底流出羨慕:“真好,我也想要個青梅竹馬的小哥哥。”
宋又川打趣:“你現在可以去談,談個小哥哥。”
黎婧初笑著作勢要打他,被他躲開。
風過堂穿過,兩個人影投在門上。若有所覺,抬起頭,容嶼剛好推門而。
后面還跟著一團尾。
“怎麼去了這麼久?”宋又川接過飲料,順手開了一瓶,“你倆去找椰子樹了?”
容嶼角,沒搭理他。
宋又川回過頭,一臉嫌棄地嘖嘖嘖:“看看,看看嶼哥這滿面紅。出門買個飲料,樂得像街頭撿了個媳婦兒似的。”
容嶼懊惱,終于抬腳踢他:“滾。”
另一頭,黎婧初親昵地湊過來:“倪倪。”
Advertisement
“嗯?”
“我剛剛聽又川,講了你小時候的事。”
倪歌微怔,然后慢吞吞地“啊”了一聲。
“事都過去了,那個老師現在也不教你,你……”
倪歌突然開口,含糊不清地打斷:“沒關系。”
“什麼?”
“跟你沒有關系。”
“……”
黎婧初愣住。
容嶼角微不可察地彎了彎,拍拍自己旁邊的座位:“坐過來。”
“好。”倪歌沒再看黎婧初,里含著兩塊糖,捧著腮幫拱過去,像一團富足的倉鼠球。
一群人坐定,宋又川新開了一局游戲。
卡牌放在容嶼左手邊,他越過子去取,惡趣味地摁住容嶼的手腕,接不到半秒,被對方一把甩開:“滾!別老子手。”
“干嘛啊你?”宋又川愣了一下,“反應這麼大,剛剛心不還好的?莫名其妙。”
容嶼繃著臉坐在原地,視線落在倪歌小而瑩潤的耳垂上,半天沒有說話。
他覺得,他可能有點變態。
Advertisement
但是怎麼辦——
剛剛幫剝過糖。
現在連手指,好像也是甜的。
——
國慶過后,全校開始備戰期中考。
高三已經用月考和周考代替了期中期末考,所以容嶼毫無力。
但倪歌每天都張兮兮。
績不差,中考能在之前的省份排到省前三百,但北城的考試制度和題型都和南方不太一樣,有點水土不服。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1069 章

贈你一世情深
我愛了他整整九年,整個少年時光我都喜歡追逐著他的身影,後來我終於成為了他的妻子,然而他不愛我,連一絲多餘的目光都不給我留。 …
199.8萬字8 286855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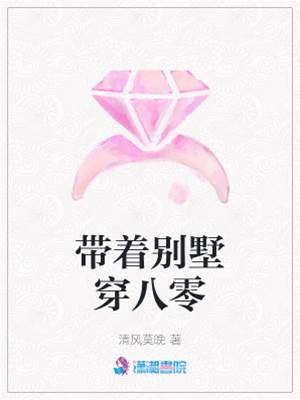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7214 -
完結180 章

正經養崽四年後,豪門親爹找上門
【雙潔】【甜寵】【養狼崽】獨自帶崽的第四年,孩子親爹找上門了。穿著講究的男人站在門邊,問她。“你是尚希?”“…是。”“我是幼崽的父親。”男人霸道強勢:“跟我走,不用想著拒絕、反抗那些沒意義的事情。”尚希盯著他那張和兒子酷似的臉,慢悠悠哦了一聲。其實她壓根兒…也沒想過拒絕、反抗啊。—辜聞明麵上是豪門辜家掌權人,暗地裏是狼人族家主,他在一次發情期提前三天,和走錯房間的純人類女人發生了關係。狼人族一生隻會有一個伴侶,但他討厭三心二意不忠的純人類,拒絕去找她。某一天,他聽到了幼崽呼叫聲。他才知道那個純人類生了幼崽,狼人幼崽正在經曆骨骼發育艱難期。為了幼崽,他把那母子倆接回家住。一開始,他冷冷地說:“我對你沒興趣,我們隻是孩子的父母。”“我隻在意我的幼崽。”兩人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幼兒園。一起參加學校旅舉行的親子活動。一起參加家長會。某一天,尚希去約會了。男人震驚發怒才發現自己的心意。他以帶幼崽出玩為由,斬斷她所有約會。他頻繁搜索:怎麼追求人類女人。他送樓、送車、送包、送飛機……都沒用。約定到了,女人帶著幼崽離開。傲慢的狼人家主,辜家掌權人徹底慌了
35.2萬字8.33 87854 -
完結198 章

退婚當天,我和渣男死對頭領證
父親入院,哥哥被未婚夫親手送進監獄。寧惜一怒退婚,當天便和渣男死對頭到民政局領證。她原本以為,這婚姻就是一場交易。誰想到,便宜老公太黏人。吃飯要她陪,出差要她陪,心情不好還要她哄睡……知道男人心里住著一個白月光,寧惜取出準備好的離婚協議,想要還對方自由。“離婚?”男人一把撕掉離婚協議,“我告訴你寧惜,我江律只有喪偶,沒有離婚。”寧惜……說好的白月光,說好的所愛另有其人呢?“白月光是你,朱砂痣是你……”男人一把擁她入懷,“自始至終都是你!”
35.7萬字8 472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