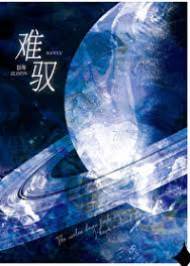《天鵝頸》 第 9 章 09
09
《天鵝湖》這支芭蕾舞劇里有兩只天鵝。
一只是白天鵝。
另一只是黑天鵝。
今兮被他們天鵝公主,指的是黑天鵝。
原因很簡單。
那年賀司珩的生日宴上,今兮穿著的是條黑的禮服。
賀司珩把今兮送回到父親邊,沒多停留就走了。
宴會正式開始前,大家都被到父母邊,唯獨江澤洲和周楊,拿了杯果酒,找到站在角落位置的賀司珩,靠了過去。
話題還停留在他們送給賀司珩的生日禮,周楊沾沾自喜,“我的眼可以吧?這車全球一共就四輛。”
賀司珩晃了晃手里的酒杯,面倦冷疲乏。
而江澤洲忽然用手肘撞了撞周楊。
周楊被撞得手心不穩,酒灑了一點兒出來,他跳腳:“我的服,你干嘛!”
江澤洲朝宴會廳某揚了揚下,“那個是不是你剛剛送過去的的?”
賀司珩眼輕抬,循聲過去。
隨著他的話,周楊也沒在意自己的服,看了過去。
來參加賀司珩生日宴的人,除了親戚,大多是賀的生意伙伴。以聯絡為由,他們把自己的孩子也都帶了過來,生居多。
藏著的那點心思,就差明擺著說出來——
想和賀家攀上點關系,最好,是親家。?
“說來真是奇怪,宴會廳的孩兒你都見了個遍吧,唯獨這位——”江澤洲說,“爸倒是一點兒都不想和你家親上加親。”
“你爸也是奇怪,那麼多歪瓜裂棗他都能介紹給你認識,整場宴會里最漂亮的這個,倒是不愿意介紹給你了。”周楊著下,思索。
“最漂亮?你家小橙子聽到可不得氣死。”
“氣死怎麼了?實話還不樂意聽了。”
“不過都是學芭蕾的,怎麼我覺得,上的氣質,和你家小橙子的,不太像啊?”
Advertisement
周楊煩:“你能別一口一個‘我家小橙子’嗎?我和關系可不怎麼樣,整天跟在你倆后一口一個洲洲哥哥,一口一個阿珩哥哥,看到我?——直接喊我的名字,拜托,除了緣這層擺不掉的關系,我和真不。”
他們嘰嘰喳喳個不停,賀司珩一句沒參與。
好半晌,管家過來找他:“爺,要跳開場舞了。”
賀司珩把酒杯放到侍應生的托盤里。
他蹙起眉,“不是說了這個環節取消嗎?”
管家沒回答,只是刻板著臉,說:“先生讓我您過去。”
賀司珩眉間皺著。
管家:“爺,不要讓我為難。”
他看了他一會兒,眼底冷霜蔓延,未幾,還是拔離開。
江澤洲抓住管家:“張叔,阿珩和誰跳開場舞?”
周楊對他的記表示無語:“之前不是說了嗎,和小橙子。”
江澤洲:“他不是拒絕了嗎?”
說到這兒,他樂不可支,“為此,小橙子還哭了一下午,眼睛腫的跟被人揍過似的。”
“是哦,”周楊一臉疑,問管家,“張叔,那阿珩和……”
“今家大小姐。”管家的視線穿過人群,落在不遠,并肩站著的人上。
賀司珩站在人群中,站姿筆。
他是今天的主人公,上穿著的西裝是量定制的,襯得他形落拓闊,袖口金包邊,更顯設計致華麗。西裹住修長雙,整個人如青松般。
不知道那邊說了什麼,他們只看到賀司珩眉間延展著躁郁。
但他還是手,遞給站在他邊的生。
琉璃燈閃爍,全場視線都集中在他們上。
最后,只剩他們頭頂一盞燈。
音樂聲起,賀司珩手搭在今兮的腰上,隨著音樂的旋律跳舞。
沒有排練過,但是異常的合拍,全程,都沒踩到過對方的腳。
Advertisement
江澤洲:“是我的錯覺嗎,我怎麼覺得,他倆穿的像是裝?”
都是黑的服。
今兮禮服不是常見的緞面款,是層疊薄紗拼接設計,薄紗里摻了金,照耀下,像極了黑暗銀河中閃耀的群星。
仰著頭,神疏離冷淡,沒有半點兒因為和賀司珩共舞的喜悅。
江澤洲說:“你覺得不覺得,像只天鵝?”
周楊不認同:“你也說小橙子像只天鵝。”
江澤洲:“還不是因為跳芭蕾,每天每天就穿著白子,整天說自己像是白天鵝,我這不得配合著點兒?”他話鋒一轉,“但這位不一樣,看著,就像只天鵝,還是黑的。跟你家那弱弱被風一吹就倒的盜版天鵝,完全不一樣。”
看著太傲,沒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也不想討好任何人。
江澤洲非常認同自己這個想法:“黑天鵝公主。”
周楊思忖了下,也認同了:“是哦,還真像只黑天鵝的。”
一曲結束。
宴會廳里響起雷鳴般的掌聲。
賀司珩和今兮面對面站著,收回手。
他們從舞臺中心離開,回到人群里。
賀司珩說:“抱歉。”
指的是,邀請跳開場舞的事。
今兮愣了下,顯然沒料到他會說出這聲抱歉。邊和他年紀差不多的男生比比皆是,只是大多目中無人,別說紳士,最基礎的待人接都做不到,趾高氣昂的樣子,仿佛全世界都得聽他們的話。
賀司珩這種云端的人,難得的,有這樣周到的。
恍神間,今兮和路過的人撞了下。
頭上綁著的蝴蝶結原本就垂垂墜,此刻,沿著垂順的長卷發落,掉落在地。
“那個……沒事的。”渾然未覺,扔下這句話,急匆匆離開。
賀司珩腳步停下。
Advertisement
他撿起地上的蝴蝶結發帶,直起時,今兮已經不在他邊,回到父母那兒去了。
他盯著手心里多出的蝴蝶結,眼里曳出一笑來。
還,
真像是一份禮。
蝴蝶結都有。
這算什麼?
拆禮?
之后,他回到江澤洲和周楊那兒。
江澤洲朝他眉弄眼:“說說,和天鵝公主跳舞是種什麼驗?”
賀司珩:“天鵝公主?”
周楊抬著下:“剛取的名兒,怎麼樣,好聽吧?”
賀司珩冷哼了聲,他不發表任何意見,只說:“無聊。”
不論賀司珩怎麼說,反正,那天之后。
江澤洲和周楊,談起今兮,總用“天鵝公主”這個稱呼代替。
后來今兮和他們了后,也問過他們為什麼這麼。其實還有一句沒問,為什麼明明都是跳芭蕾,是天鵝公主,而周橙,不是。但沒問,因為他們看上去,和周橙并不絡。相十多年還不絡,還是堂兄妹,有趣的關系。
二人沒瞞,直截了當地告訴原因。
黑天鵝公主。
一就是這麼多年。
結果沒想到,今天黑天鵝變了黑騎士。
周楊疼得心都在滴。
一伙人看熱鬧看的痛快,紛紛恥笑他,“大話放的太早咯。”
“年輕人不懂事,不知道社會的險惡。”
“這哪兒是不知社會的險惡,是不知道有多可怕。”
“……”
“……”
唯獨賀司珩和今兮被蒙在鼓里。
從話語里,賀司珩能大致猜出他們嘲笑周楊,原因和他有關,“怎麼回事兒?”
周楊一臉吃屎的表。
還是江澤洲把那個賭說了出來。
賀司珩眉梢輕抬,聲音無起伏:“拿我當賭注?”
“額……這個,”周楊走今兮邊的人,坐在邊上,低聲音:“就是因為你,都什麼年代了給我搞救英雄,害得我輸了這麼多錢。”
Advertisement
他眉弄眼:“幫我搞定他,救命。”
今兮很無辜:“英雄救多俗套。”
周楊眼地看著,“姑,當我求你了。”
今兮忍不住笑。
金的臺面上擺滿了麻麻的酒杯,中間還有個果盤,邊上一盒叉子。今兮從里挑了個叉子出來,叉了塊哈瓜,送到賀司珩邊。
賀司珩不為所。
仰著頭,在時時亮的環境里,這張明艷人的臉,眼似黑,又似銀河。酒吧里,酒和香水雜,味道有些辨不清。但上的味道,賀司珩卻能一秒捕捉到。
很淺淡的香。
太濃烈的東西,只有被震撼到時,帶來剎那的快。
而寡淡的東西,像是長久縈繞在耳邊的風,揮之不去,百轉千回,令人舍不得、放不下。
對視幾秒。
今兮嘆了口氣:“吃不吃?不吃我自己吃了。”
賀司珩張,咽下那塊哈瓜。
他問:“怎麼幫我擋酒?”
不止他想知道,邊的周楊也很想知道,這到底是哪兒出了差錯?
今兮:“醫生不能喝酒。”
賀司珩不是不能喝酒,是因為工作質——病人偶爾會有突發狀況,他得保證自己時刻于大腦清醒的狀態。不喝酒,是作為一名醫生,他必須如此約束自己。
賀司珩:“所以你代我喝?”
今兮:“就三杯酒,喝了又沒什麼。”
周楊:“不是,什麼就三杯酒?你知道這酒濃度有多高嗎?就你那酒量——”
“——我酒量怎麼了?”今兮眼神沒有半分便宜,語氣淡淡地,莫名有種睥睨天下的氣勢在,“十個你都不夠我喝的。”
“哦豁,年輕人口氣不要這麼狂。”
江澤洲話:“就是,上一個這麼狂的,已經要付一年的酒錢了。”
周楊:“……”
猜你喜歡
-
完結1877 章

老公寵妻太甜蜜
十九歲的蘇安安被渣爹逼嫁給三十一歲的顧墨成。當天晚上她被化成餓狼的顧墨成壓榨得筋疲力盡,「不是說不行嗎?」「都是三十多歲的老男人,也不知道節製。」蘇安安扶著快斷的腰表示不滿。顧先生生氣,又壓了過去,「繼續!」婚後,顧先生開啟護妻寵妻模式。「老公,渣爹又想打我!」「等著!」顧先生惱了,直接把蘇家端了。「老公,她對我下藥,想把我送給其他男人!」
336.9萬字7.79 263978 -
完結186 章

惹草
初識,他是她同學的小叔,不經意的一瞥,淡漠從容,風度翩翩,從此被吸引。 而後,她為生存步步為營,滿腹算計,鐵了心要拉他入深淵。 直至車內熱吻的八卦新聞曝光,全城嘩然。 平日裡自持矜貴的許先生,竟也有淪陷的時候。 圈內好友都調侃,許先生偷偷養了個嬌美人,捧在心尖上護著,誰都碰不得。 風波雲湧起,他為她遮風擋雨、遇佛殺佛;而她亦敢為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隻為守住誓約——與你,歲歲年年。 腹黑魅惑可婊可颯的妖精vs成熟沉穩清冷矜貴似仙官
33.9萬字8 17948 -
完結499 章
離婚后,極品前夫跪求我復婚
做了三年賢妻的裴太太突然要離婚。裴祈:“理由。”蘇閔婕:“你沒達到我的期望,我選擇止損。”當天晚上,蘇閔婕在酒吧玩瘋了。裴祈將人堵在過道里,半瞇著眼睛警告,“差不多就行了,我的耐心很有限。”蘇閔婕更不耐煩:“趕緊簽字,大家好聚好散別鬧太難看!”她被人陷害,一夜之間被推至風口浪尖上,落了個‘海王富太’的名聲。裴祈以為蘇閔婕會來求他,結果,被她和死對頭聯手拉下水。后來,看著各界精英大佬,一個
87.5萬字8 174872 -
完結154 章
嬌攀
岑旎第一次遇見穆格,是在南法的地中海峽灣。男人骨相偏冷,點煙時姿態閒散矜貴,玩世不恭的輪廓卻透着幾分東方人獨有的柔和。“要不要來我這。”他說。岑旎挑眉,“你那有裙子換?”“沒有。”男人回答得理直氣壯,“但可以有。”成年人之間的你來我往,就好像是一場猜謎,不說破也不點透,你我心知肚明。那一晚他開敞篷跑車,載着她一路沿海邊懸崖兜風,彎下腰替她腳套上小高跟。倆人在夜風的露臺前擁吻,火花一擦而燃。普羅旺斯的花海是藍色的,就像初見時候的藍霧。短暫的相處過後,岑旎重歸理智。一時興起的相處,彼此就應該相忘於浪漫的初始地。但岑旎沒想到男人和女人之間,有時候確實有緣份。完全泯於人海後還是碰到了。
23.9萬字8 7408 -
完結169 章

溫先生的心尖月
(蓄謀已久 細水流長 甜寵 雙潔 無虐 年齡差五歲左右)(女主醫生,非女強)*【溫婉清麗江南風美人 & 內斂沉著商圈大佬】容煙出身書香門第,自小跟隨外公生活。聽聞外公給她尋了門親事,她原以為聯姻對象是同為醫生的溫二公子,殊不知卻是接管溫家的溫景初。煙雨灰蒙,寺廟裏,容煙瞥見與她擦身而過的男人。上一次見他還是四年前,可他從不信神佛,為何會出現在這裏?朋友生日聚會結束,溫景初送她歸家。車內,容煙壓住心中疑惑,終究沒問出口。*容煙本是溫吞的性子,喜靜,信佛。她自認為婚後的兩人是相敬如賓,搭夥過日子。而他卻步步誘她淪陷。某日,容煙在收拾書房時看到了寺廟的祈福袋,裏麵白色宣紙上寫著她的名字,似乎珍藏了許久。而此時溫景初正接受電視臺采訪,清肅矜貴,沉穩自持,淡定從容與人交談。主持人問,“溫先生,聽聞您並不信神佛,但為何每年都到靈山寺祈願?”容煙手中拿著祈福袋,略帶緊張的等待著他的回答。男人黑眸如墨,思忖片刻,緩緩啟唇,“因為溫太太信佛。”簡單一句話卻擾亂她的心。
33.1萬字8.09 23348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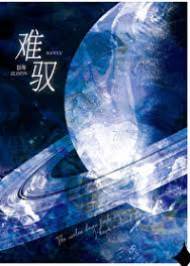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18 110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