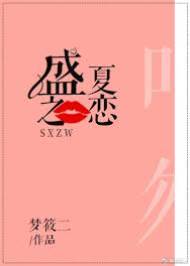《上嫁》 第6章 彼此都有感覺
車駛進酒店,程禧跟著周京臣上樓。
行政套房在33樓,頂層。
周京臣挨著落地窗坐下,手指有一搭無一搭地輕叩桌沿。
也叩在程禧的心上。
獨的時候,他是若無其事的,不自在的是。
男人在這方面,確實比人開放。
“司機買了豆漿,你洗完澡出來喝。”
房間靜謐得落針可聞。
微妙至極。
周京臣審視了好半晌,室溫越來越高,他解了領帶隨手一扔,“去洗。”
程禧跑進浴室,反鎖了門。
腳底有些發飄。
和周京臣之間縈繞著一剪不斷理還的氣氛。
不小心捅破,會一發不可收拾。
程禧將保暖掛在門把手,擰開淋浴,發現沒帶浴巾,重新開門出去,“你車裡有巾嗎——”
周京臣抬頭,四目相對,程禧才意識到他在通電話。
“你和人在一起?”周夫人耳力靈敏。
“嗯。”
逮了個正著,他沒否認。
他邊沒有下屬,包括工作助理和生活書都是男的,周夫人也知。
下屬相久了,難保生出上位的心思。
一旦冒險朝他下手,目標勢必是一步登天,母憑子貴當週太太,不單單是幾個錢了。
電話那端靜默了一會兒,“你在什麼地方?”
“酒店。”
“沒回自己家?”
“沒有。”
“你還算有分寸。”
周夫人倒是有心理準備。
Advertisement
他忙於公務清心寡慾,畢竟是氣方剛的歲數,偶爾有一兩晚忘,也正常。
“什麼職業?”
周京臣長疊,了線的摺痕,“學生。”
程禧嚇得屏住呼吸,生怕周夫人再聽到一丁點的聲音。
“年了嗎?”
“二十。”
周夫人在商場裡,有妝廣告的廣播,很嘈雜,“那姑娘已經同意見面了。”
“您安排日子。”
周京臣的態度既不期待,亦不反,一切水到渠,平和接。
周夫人略加思索,“安排在兩天後呢?”
他仍舊嗯。
“那你要注意分寸了。”周夫人不願節外生枝,“該給學生的補償,寧可多給,別給,最忌諱糾纏,你馬上兩清,從此斷了。”
周京臣平靜掛了電話,向程禧,“在床上的封袋裡。”
怪不得他從後備箱拎了一個袋子,原來是裝巾的。
周到。
會照顧人,不濫,要財有財,要型有型,沒有哪個人不。
“酒店的用品不衛生。”周京臣眼神意味不明停留在上,“你得病了,我也遭殃。”
程禧耳朵嗡嗡作響,短暫的失聰了。
周京臣的意思很明顯了。
只要時機合適,彼此都有覺,他不排斥這段危險忌的關係。
“見面的日子定了嗎?”
“定了。”
程禧挲著封袋的拉鍊,眼前浮現出那姑娘姣好風的面龐,“你喜歡漂亮的?”
Advertisement
“不然呢。”周京臣轉手機,螢幕在拇指的反覆下忽明忽暗,“你喜歡醜的嗎。”
力氣大了,拉鍊崩開,合不攏了。
捂住歪歪扭扭的拉鎖。
“漂亮重要,不是最重要。”周京臣倚著沙發。
程禧垂下胳膊,“家世最重要。”
“你這樣認為的?”
微微側過去。
周京臣逆著落地窗的,紗簾也擋住了亮,他眉目神黯淡。
程禧步伐很輕進浴室。
......
周京臣批閱完最後一摞檔案,仰起頭活泛著肩頸。
餘不經意一瞥,程禧披著長髮,在晾巾。
細白修長的腳脖子淤青褪去,戴著小鈴鐺的腳鏈,像他吃的春筍尖。
他印象這鈴鐺的節奏很好,尤其是雙架在他肩膀,一下接一下,他撞,鈴鐺撞他,他狠,鈴鐺也狠。
配合他顛得。
簡直是無言的。
周京臣站起來,了襯,鎖骨泛起一片的紅。
他背過,脊骨劇烈波,連同皮帶擱在沙發上。
浴室響起急促的水聲。
水流開到最大。
程禧翻著酒店的環球旅遊雜誌打發時間。
“巾。”周京臣。
走近一些,“沒有新的巾了。”
花灑聲很衝,沖淡了男人的音量,“你用過的那條。”
像是繃的一弦,不控制地一抖。
“程禧?”周京臣又。
Advertisement
攥住架上溼漉漉的巾,門推開三分之一,水霧撲面,周京臣出手,水痕沿著他勁瘦的臂彎線條慢慢流下。
抓住巾,也順勢抓住。
和在車裡幫取暖握手的含義不一樣,現在他是男人,是人。
一個赤著,溫度滾燙的男人。
回手,背在後。
隔著半明的磨砂門,周京臣的廓雄渾自然的凸起。
“拖鞋。”
程禧去門口,拆了一雙新的拖鞋遞給他。
室蒸氣燻騰,悶得要缺氧了。
“還需要什麼嗎?”
周京臣接過鞋,“不需要。”
程禧如釋重負逃離。
十分鐘後,司機買回來早餐,又給一個正方形的紙盒,“是周總工的。”
原封不放在那一摞批完的檔案上面。
司機前腳離開,周京臣敞開門,“小楊,給我。”
程禧捧著一杯甜豆漿,“司機走了,你要什麼?”
浴室沒有了水聲,傳來的字字清晰,“有盒子嗎。”
“有。”
“我要。”
盒子的標籤掃過手腕,程禧本能去看,男士純棉抗菌。
一條三角的,一條四角的。
心複雜。
周京臣氣質肅穆正經,也有不為人知的,的一面,野的一面。
他的尺寸不適合三角,包不住。
起反應了之後,四角都差點撐破。
周京臣穿好子,拭著髮梢走出浴室,“你在想什麼。”
Advertisement
程禧有一種被識破的尷尬,“想昨天考試的答案。”
“撒謊。”周京臣的眼睛如同一個鉤子,深邃莫測,直勾勾的。
勾得心起伏。
“司機買錯了,我沒穿過那個。”
程禧低頭,不搭腔。
“太窄,會。”
他拿熱巾敷臉,舒緩神。
這條巾洗澡時過私部位。
周京臣埋在巾裡的樣子,聯想到另外一幕,臊得面紅耳赤。
“你...”言又止。
“你喜歡?”周京臣打斷。
程禧一怔。
“見過男人穿嗎。”
搖頭,又點頭。
“在哪見過。”
燈和,照得周京臣也比往日溫許多。
程禧如實說,“游泳館。”
周京臣住一縷長髮,捋到耳後,整張面孔完全在燈下。
“會遊嗎?”
這次實實在在搖頭,“沒學會。”
“我教你。”周京臣似有若無地控耳垂,他指腹有繭子,不薄不厚,糙糙的,是長期工作磨礪出的。
他過的每一寸,極度的敏。
程禧一顆心好似要竄出嚨了。
片刻,周京臣攤開掌心,是一枚小小的珍珠卡子。
“太馬虎。”
洗頭髮忘了取下卡子了,來去和髮攪繞住。
還渾然不覺。
“謝謝。”
程禧卡住碎髮,小珍珠緻圓潤,額頭也小,周京臣又看了一眼腳上的鈴鐺鏈兒,腰椎驀地麻了下。
他眼底一陣暗湧。
猜你喜歡
-
完結254 章

懷孕后,渣總送我入匪窩換白月光
【虐文+虐身虐心+追妻火葬場+靈魂互換+偏執】陸景深永遠不會知道,沈凝的心先死在他白月光突兀的電話,後絕望在他親手將她送給綁匪,只爲交換他的白月光,更不知,他的白月光挺著和她一樣大的孕肚出現在她面前,她有多怒不可遏和歇斯底里,甚至崩潰,還有當她遍體鱗傷出現在搶救室時,那些冰冷的儀器一點點掏空她如破布娃娃的身體,而他,置若罔聞的眸色終於讓她的淚水決堤。“陸景深,我真想挖出你的心看看是什麼顏色。”他冷哼:“該挖心的人是你,再敢動若霜,我定讓你生不如死。”呵呵,陸景深,但願我們一別兩寬,永不相見,即使地獄,我沈凝也不想再看你冷厲嗜血的臉龐分毫半寸!
46.5萬字8.18 30942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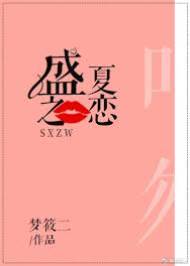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8.18 7712 -
完結319 章

婚後重生,賀少寵妻成癮
賀家賀大少以強勢狠厲著稱。 賀翊川為人霸道冷情,似乎任何人都激不起他的興趣,如同佛子一般,婚後禁慾半年之久。 娶她不過是受長輩之命。 遲早要以離婚收場,蘇溪也這麼認為。 哪知一次意外,兩人一夜纏綿,賀翊川開始轉變態度,對她耐心溫柔,從清心寡欲到溝壑難填,逐步開始走上寵妻愛妻道路! 兩個結婚已久的男女開始經營婚姻的暖寵文! 劇情小片段: 「賀翊川,你今晚怎麼了?你醉酒後可太能折騰人了。」 聽到她耐不住的抱怨聲,賀翊川拾起掛在他脖頸上的小手,輕輕地揉了揉,聲音低啞富有磁性:「今晚高興。」 「為什麼?」 「因為方俊傑他們祝我們新婚快樂,生活幸福。」他一字一句的啟唇,低沉清朗的聲線,清晰分明的灌入她耳中。 聽到後,蘇溪扶住他的手臂,將上半身和他的結實的胸膛拉開一些距離,昏黃的燈光斜照在她明亮的瞳孔里,清澈見底。 「你說該不該高興?」 男人清墨般的眼眸與她四目相對,薄直的唇角邊含著似有若無的笑意,眼神直勾勾地凝視著她。 蘇溪指尖在他手心中微微蜷縮,心跳也不由加速,語調輕緩柔和:「高興。」
52萬字8 10606 -
完結140 章

不言而遇[破鏡重圓]
入職君杉研究所不久,楚言就想辭職了。 她的親閨女指着她的前男友周慎辭大喊:“麻麻,我要這個帥叔叔當我拔拔!” 周慎辭眉梢微動,幽暗狹長的眼眸裏浮着意味不明的情緒。 楚言不合時宜地想起了四年前那個潮溼的夜晚。 光線昏暗,男人身上只隨意披了件浴袍,指尖是還未燃盡的香煙。 猩紅的火光晃動,低沉的聲音略顯沙啞:“楚言,我只問一次,你想好了嗎?” 那時的楚言躺在床上,背對着周慎辭,眼角的淚早已將枕頭浸濕。 可她卻還是佯裝灑脫:“嗯,分手吧。” - 周家是京市是頂級豪門,長子周慎辭更是在商界出了名的縱橫捭闔殺伐果斷,渾身上下都透着生人勿近的氣場。 誰也想不到,他竟然會在大庭廣衆之下蹲下身子,讓一個三歲小孩給他戴上粉紅凱蒂貓的夾子。 “念念,想不想換個新爸爸?”周慎辭溫柔試探。 楚禕念大眼睛一眨一眨:“可是,追媽媽的人好多,要排隊呢。” 周慎辭悄悄把棒棒糖塞進楚禕唸的手裏,道:“好念念,求求了,幫爸爸插個隊吧。” - 小劇場: 某日,總裁辦公室內,平日裏總是乾淨整潔的辦公桌如今一片混亂,隱晦地暗示着剛剛荒唐的不可說。 周慎辭有力的雙臂撐在楚言兩側,將她禁錮在狹小逼仄的空間內,高大挺拔的身姿充滿了壓迫感。 他倨傲地睨着她,語氣冷淡又肆然:“爲什麼不戴戒指?” 楚言擰眉頂嘴:“做實驗不方便。” “戴上。”周慎辭語氣不容置喙。 楚言不服:“有什麼好處?” 周慎辭垂眸,深雋英挺的五官是上帝親手雕琢的藝術品。 “剛給你批了三間全設備頂配實驗室。” 楚言明眸閃動:“不夠。” 周慎辭挑眉,繼而淡聲開口:“那再加一個,今晚不撕你睡裙。” 楚言:“……”
19.5萬字8 30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