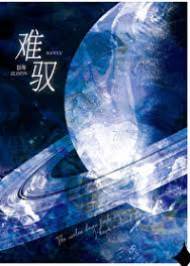《二婚嫁京圈大佬,渣前夫瘋了》 第011章 商少崢,我們離婚吧
商北梟起。
拿著一次紙杯接了一杯水。
他端著水杯。
這位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天之驕子,人中龍,第一次會到束手無策。
他若是直接給花昭灌水。
怕是還沒解。
就先嗆死。
商北梟黑著眼眸走過去,把花昭從床上拉起來。
誰知道,人乎乎的。
仿佛沒有骨頭的章魚。
東倒西歪。
額頭還差點磕在床頭櫃上。
商北梟心中越發煩躁,他應該讓周彥過來理花昭的。
輕提了口氣。
商北梟主坐在床邊,讓花昭靠著自己。
不省人事的人倒是不怕死,直接窩進了他的懷裏。
靠著他的膛,像是被他攬在懷裏一樣,比單純靠著他的側舒服太多。
商北梟眼神中流出嫌棄的暈。
他一手開花昭的。
另一隻手端著紙杯,送到邊,花昭像是沙漠中缺水的駱駝,迫不及待的喝了兩口。
就閉上,不喝了。
商北梟要放下。
花昭卻纏纏綿綿的抱住了他的腰,仿佛回到了和商崢熱的時候,生病被他照顧,“商崢,我不舒服。”
商北梟:“……”
他魯的拉下花昭的手,把按在了床上,塞進被子裏,頭也不回的走出去。
Advertisement
人真是世界上最麻煩的東西。
……
老人家也很快從急救室被推出來。
醫生和周彥代,“有點腦出,不過不是很嚴重,右胳膊摔骨折了,老年人骨質疏鬆,骨頭很脆,要好好的養著,盡量不留後癥。”
周彥一一答應下來。
他轉看到商北梟,急忙上前,“六爺,我給阿行打了電話,他在路上,等下接您回去休息,我在這兒等表醒了再走,臺風天,醫院沒有多餘護工了。”
這次,商北梟倒是沒拒絕。
他走的時候。
剛好經過花昭的病房。
他沒有往裏麵看一眼,長闊步離開。
花昭是早上六點多醒過來的。
掙紮著酸痛的子爬起來,頭疼裂,好像被上千針紮進了裏麵。
雙手抱著額頭。
昨天晚上,絕又悲慘的一幕幕,在腦海中像是放電影一樣,鋪展開。
外婆……
花昭想到外婆,迅速起,穿上鞋子,向病房外麵走。
推開病房門。
迎麵。
商崢扶著寧薇薇,寧薇薇也穿著病號服,兩人有說有笑的走著。
花昭麵如死灰。
商崢看到花昭的第一眼,迅速放下了攙扶寧薇薇的手。
慌慌張張。
Advertisement
臉都漲紅了。
兩隻手似乎想不到往哪放。
寧薇薇關切的問道,“嫂子,你這是……你怎麽也住院了?”
商崢上前兩步。
他拉住花昭的手,“怎麽了?怎麽住院了?”
花昭抬眸,眼尾染上了一層薄薄的猩紅,控製不住哽咽,“昨晚你開著我的車去找了?”
商崢低聲下氣的說道,“昭昭,昨晚薇薇小區停電,那個混賬前夫進去打,要不是我去的及時,怕是要出人命了,事發突然,我來不及跟你解釋。”
花昭用力甩開他的手。
商崢慌的開口,“昭……”
他還沒說出口。
迎麵一個掌打上去。
打偏了他的臉。
眾目睽睽之下,被掌摑,這是商崢活了二十六年來,第一次。
他舐著腮幫。
嚐到了一腥味。
商崢頗有些氣惱,他低聲嗬斥,“花昭,你瘋了!你就沒有一點同心?”
花昭幾乎站不穩。
扶著牆壁。
目灼灼又狠厲,好像是被火焰燒過的花朵,破敗不堪,“你同心泛濫,你去關照你的小青梅,你憑什麽開走我的車?商崢,你最好祈禱我外婆無事,要不然我不會放過你的。”
花昭扶著牆壁,一步步走遠。
Advertisement
商崢心裏咯噔一下。
仿佛……
有種握在手裏的沙子,正在緩慢溜走的覺。
他心生懼怕。
立刻追了上去,“昭昭……”
寧薇薇一個人站在原地,咬了咬瓣,莫可名狀的笑了笑。
果然沒錯。
原來男人喜歡的,都是床下乖的,床上的。
早知如此……
還有花昭什麽事?
不過也沒關係,屬於的一切,會一點點的搶回來。
寧薇薇眼神中迸發出勝券在握的。
沒去追商崢。
追上去,就是不懂事了。
一個人朝著病房走。
——
骨科病房
外婆還在睡,值班護士告訴了花昭老人家的況,花昭才鬆了口氣。
如釋重負。
商崢明白了事的經過,他愧疚的半跪在花昭麵前,懺悔,“對不起,昭昭。”
他猜到外婆可能是摔了一跤。
甚至猜到可能是磕破了傷口,流了點。
可是萬萬沒想到況這麽嚴重。
商崢心裏悔恨不已。
花昭疲憊的眼神,本沒有落在他的上,“商崢,你去陪寧薇薇吧,我累了,你不要打攪我。”
商崢拉著的手,用力的打在自己臉上,眼眶通紅,“昭昭,你打我,你打我吧,都是我不好。
Advertisement
我沒有陪著你麵對困難,我還誤解你,你想怎麽打我都可以,但是你別不理我,好不好?”
花昭自嘲的勾了勾,“商崢,我現在沒有心和你爭辯誰對誰錯,你走開可以嗎?”
商崢握花昭的手,額頭在的膝蓋上,“昭昭,給我機會彌補,讓我留下來幫你照顧外婆。”
花昭用力出手。
沒有再同他說一句話。
一直到外婆醒過來,商崢第一個跑到床邊,端茶送水。
隔壁病床的老人家以為商崢是外婆的孫子,直誇這孫子孝順。
外婆笑的合不攏。
一邊任由商崢喂粥,一邊滿臉自豪的說,“不是孫子,是我外孫婿。”
隔壁的爺爺更是羨慕的眼珠子都快黏在商崢臉上。
誇外婆有福氣。
誇花昭有福氣。
商崢很矜持的說道,“能娶到昭昭是我的福氣,孝順老人更是應該的。”
外婆吃了飯。
心疼的看著兩人,“我沒事了,你們回家休息,你看你倆熬的,眼睛都紅了。”
商崢急忙說,“讓昭昭去休息,我留下來照顧外婆。”
老人家哎呀呀的說道,“誰也不用留下來,我自個兒照顧得好我自個兒。”
心疼這倆孩子。
商崢想了想,給外婆掖了掖被子,“外婆,我找護工照顧你,你不許推辭,你若是不要護工,那我隻好留下來親自照顧你了。”
外婆無奈,隻能妥協。
商崢又迎來了整個病房裏的爺爺的謬讚。
花昭在旁邊,譏諷似的勾了勾。
商崢笑著走過去。
握住花昭的手。
為了不刺激到外婆,花昭沒有立刻甩開。
雖然一瞬間有了應激反應,但是被自己狠狠的下去了。
直到出去病房幾米遠。
花昭才重重的甩開了商崢的手,“商崢,我們離婚吧。”
猜你喜歡
-
完結1877 章

老公寵妻太甜蜜
十九歲的蘇安安被渣爹逼嫁給三十一歲的顧墨成。當天晚上她被化成餓狼的顧墨成壓榨得筋疲力盡,「不是說不行嗎?」「都是三十多歲的老男人,也不知道節製。」蘇安安扶著快斷的腰表示不滿。顧先生生氣,又壓了過去,「繼續!」婚後,顧先生開啟護妻寵妻模式。「老公,渣爹又想打我!」「等著!」顧先生惱了,直接把蘇家端了。「老公,她對我下藥,想把我送給其他男人!」
336.9萬字7.79 263966 -
完結186 章

惹草
初識,他是她同學的小叔,不經意的一瞥,淡漠從容,風度翩翩,從此被吸引。 而後,她為生存步步為營,滿腹算計,鐵了心要拉他入深淵。 直至車內熱吻的八卦新聞曝光,全城嘩然。 平日裡自持矜貴的許先生,竟也有淪陷的時候。 圈內好友都調侃,許先生偷偷養了個嬌美人,捧在心尖上護著,誰都碰不得。 風波雲湧起,他為她遮風擋雨、遇佛殺佛;而她亦敢為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隻為守住誓約——與你,歲歲年年。 腹黑魅惑可婊可颯的妖精vs成熟沉穩清冷矜貴似仙官
33.9萬字8 17944 -
完結499 章
離婚后,極品前夫跪求我復婚
做了三年賢妻的裴太太突然要離婚。裴祈:“理由。”蘇閔婕:“你沒達到我的期望,我選擇止損。”當天晚上,蘇閔婕在酒吧玩瘋了。裴祈將人堵在過道里,半瞇著眼睛警告,“差不多就行了,我的耐心很有限。”蘇閔婕更不耐煩:“趕緊簽字,大家好聚好散別鬧太難看!”她被人陷害,一夜之間被推至風口浪尖上,落了個‘海王富太’的名聲。裴祈以為蘇閔婕會來求他,結果,被她和死對頭聯手拉下水。后來,看著各界精英大佬,一個
87.5萬字8 174871 -
完結154 章
嬌攀
岑旎第一次遇見穆格,是在南法的地中海峽灣。男人骨相偏冷,點煙時姿態閒散矜貴,玩世不恭的輪廓卻透着幾分東方人獨有的柔和。“要不要來我這。”他說。岑旎挑眉,“你那有裙子換?”“沒有。”男人回答得理直氣壯,“但可以有。”成年人之間的你來我往,就好像是一場猜謎,不說破也不點透,你我心知肚明。那一晚他開敞篷跑車,載着她一路沿海邊懸崖兜風,彎下腰替她腳套上小高跟。倆人在夜風的露臺前擁吻,火花一擦而燃。普羅旺斯的花海是藍色的,就像初見時候的藍霧。短暫的相處過後,岑旎重歸理智。一時興起的相處,彼此就應該相忘於浪漫的初始地。但岑旎沒想到男人和女人之間,有時候確實有緣份。完全泯於人海後還是碰到了。
23.9萬字8 7407 -
完結169 章

溫先生的心尖月
(蓄謀已久 細水流長 甜寵 雙潔 無虐 年齡差五歲左右)(女主醫生,非女強)*【溫婉清麗江南風美人 & 內斂沉著商圈大佬】容煙出身書香門第,自小跟隨外公生活。聽聞外公給她尋了門親事,她原以為聯姻對象是同為醫生的溫二公子,殊不知卻是接管溫家的溫景初。煙雨灰蒙,寺廟裏,容煙瞥見與她擦身而過的男人。上一次見他還是四年前,可他從不信神佛,為何會出現在這裏?朋友生日聚會結束,溫景初送她歸家。車內,容煙壓住心中疑惑,終究沒問出口。*容煙本是溫吞的性子,喜靜,信佛。她自認為婚後的兩人是相敬如賓,搭夥過日子。而他卻步步誘她淪陷。某日,容煙在收拾書房時看到了寺廟的祈福袋,裏麵白色宣紙上寫著她的名字,似乎珍藏了許久。而此時溫景初正接受電視臺采訪,清肅矜貴,沉穩自持,淡定從容與人交談。主持人問,“溫先生,聽聞您並不信神佛,但為何每年都到靈山寺祈願?”容煙手中拿著祈福袋,略帶緊張的等待著他的回答。男人黑眸如墨,思忖片刻,緩緩啟唇,“因為溫太太信佛。”簡單一句話卻擾亂她的心。
33.1萬字8.09 23320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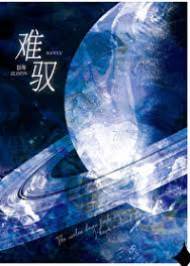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18 110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