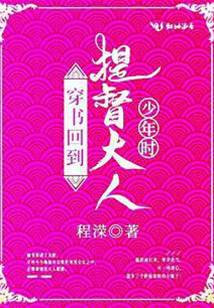《錯嫁皇妃帝宮沉浮:妃》 第七章
這些巽國的兵,除了任自己的發泄,肆意凌辱人之外,還會什麼?
哪怕皇家俸祿,都這麼無恥。
夕依舊明地笑著,見他們迫不及待地上炕來,手輕輕一組,語綿綿:
“噯,你們倆,難道,真要一起嗎?呃?”
矮個子的兵瞇瞇地道:
“那你說誰先呢?”
夕以手掩,撲哧一笑,青蔥般的長指先一點矮個子的兵,瞧他喜形于,那治著貝殼澤的指尖旋即一移,往那猴腮臉又一指,未待猴腮臉竄上前來,的手卻就勢手繪,拖住下頷,語音低:
“若我點了,豈非有失公平,不如——”
的眸華掃了眼前兩個難耐的男子,復輕輕一笑,帶著幾分曖昧地道:
“你們比試一下,誰的武藝高出一籌,我,就先委與誰,因為,金真的子,素來,都只藝高的男子。”
“好!”矮個子應道,旋即拔出佩刀,指向猴腮臉,“孔二,來,哥們比較一下。”
猴腮臉瞇了一下他的綠豆眼,有些猶豫,但抵不住當前,只能道:
“李四,先說好,點到即止。誰先點中對方的要害,就誰贏。”
“好說。”
“慢著。”夕止道,“你們這麼比,被門外的聽到,萬一,以為發生什麼事,沖了進來,豈不是,人又多了?”
“哈,還是你想得周到。”矮個子哈哈一笑,復走出艙門,不一會,便有他的聲音傳進艙,“我和孔二切磋一下武藝,誰勝誰先嘗,你們幾個,在外面好好搜搜,看有沒有掉的。”
“好。”
隨著幾名兵不懷好意笑著應聲,矮個子已鉆進船艙,并掩好艙門,待猴腮臉拔出佩刀,刀刃相格間,發出清脆一聲響。
Advertisement
夕著,邊的笑意剎那變得冷冽。
纖長的手指看似不經意地過上的褶皺,實際,則是到枕后,常年在海上捕魚為生的漁民,都會在手可及防的利,以防,不期而至的海盜。枕后薄巧的小刀被牢牢握在手心,隨后悄悄掩于后。
比試中的倆人,看樣子,手是不相上下的,或許,需要一個額外的推進,才能快點見勝負吧。
是的,要他們快點見勝負,這點,才是要的。
忍著部的不適,緩緩移至塌邊,輕輕解開襟,不過才解了第一個系扣,出頸部更多白皙的,那正對向的矮個子兵眼里的意更濃,只這一濃,手上的招式緩了一緩,恰被猴腮臉的刀格過,眼見著,那猴腮臉的刀徑直向矮個子刺去,夕仿若未見一樣,繼續接下一個口子,但,這一次,的手停在那扣上,眸底眉梢都蘊了笑地凝向矮個子兵。
矮個子心神一曳,猴腮臉的刀已點到他的襟前,他一驚,忙使刀不管不顧地朝猴腮臉刺去,猴腮臉本按著規矩,點到,即住了刀,未料想到一招,才想避開,子被別人從后面用力一踢,不由自主地向矮個子的刀劍撲去。
那一刀,正中他的要害,他一聲都來不及吭,倒在了地上。
他的下,蜿蜒出一條濃郁的水,那麼濃,那麼腥,讓夕覺到一陣惡心,可,不會在懼怕。
不聲地回退,臉上的神是惶恐的:
“你——你——“
矮個子兵握住刀的手在瑟瑟發抖,剎那消逝的無語無蹤。按著巽朝的法令,他殺了同隊的兄弟,必是要被死的。”別,別!“他慌忙地丟了刀,要捂住夕的。
Advertisement
怎麼會呢?
本不會。
的手一,明亮的刃閃過,只聽輕微地‘噗’地一聲,匕首的鋒尖,沒矮個男的腹中。
矮個男的眼底晃過不可置信的神,但,旋即籠上的,是死亡的灰霾。
是的,他死都不會想到,自己堂堂的七尺男兒,會死在一個看似弱的子手上。
何止他沒有想到呢?
若是放在前幾日,夕都不會想到,自己竟會殺人!
雙手,沾上的是,別人,猶帶著溫熱的鮮。
清楚,這一刀刺下去,是直抵他的心臟。
那個位置,都沒有記錯。
驟然撤開手,那深及沒刃的匕首在矮個男子的上,他徑直向后倒去,連悶哼一聲的機會都沒有。
兩個未的男子,就這樣,悉數斃命。
沒有人會就自己,面對在一次貞潔不保的景,唯有自救。
求他們,是本沒有用的。
不得手,他們決不罷休,得了手,還是會按著命令,殺了和阿蘭。
所以,只有先他們一步,將他們殺死。
屬于,命定的劫數,一次就夠了。
既然,的子已經不干凈,何妨手上也沾滿鮮呢?
努力地吸進一口氣,努力是自己驚的心平復。
心狠手辣,又怎樣呢?
沒有誰,在經歷這些后,還能保持純真善良。
不知道,甲板上還有多兵,以的能力,對付兩個,已是極限。
移下床,瘸瘸地行至阿蘭旁邊,用力掐阿蘭的人中,阿蘭悠悠地醒轉過來,忙用手輕掩阿蘭的,道:
“阿蘭,聽我說,不要沖,附近如果還有金真族的人,去找他們,避過這一時再說。”
阿蘭的眸底有著明顯的淚,夕知道,阿蘭不僅想殺了那兩個兵,還想沖到甲板上去看他父母。
Advertisement
只是,這無疑是最不明智的。
眼下的形,能逃命就是大幸。
其余,報仇之類的,除了生生陪進一條命,或許再被辱之外,更逞論其他呢?
“快走。”
說完這句話,松開捂住阿蘭的,阿蘭沒有喊,只是淚流了下來,一顆顆地濺落,隨著夕側,走到窗邊,阿蘭朦朧地目,看到躺在艙的那兩尸時,的表是驚愕的。
艙有一窗子,因著窗的狹小,窗下只有窄窄的船邊,跳下去,是直通海的。
借著漸濃的夜,從這里跳下去,一阿蘭的水,應該是可以險的。
夕努了努,指向那窗子,急促地示意阿蘭快走。
阿蘭咬了咬牙,站起,抹干眼淚,走到夕旁,牽起的手,輕聲:
“要走一起走。”
“別說孩子話,你先出去,找到人,再救我。”
夕的聲音很低,的了傷,又不會游水,本是不能用這法子逃的。
阿蘭不依,手抓住夕的手,用力推開窗,趁著甲板上的兵還沒有反應時,就攜著夕一并跳下船去。
夕來不及拒絕,也知道,這下壞了,沒有想到這個丫頭的義氣,反壞了事。
其實,早就想好自己的退路,阿蘭逃走后,就沒有顧忌,那樣的話,僅需將艙底的閥子打開,讓水溢進來,到時,兵忙著套路,又豈會再顧得了呢?
抱著穿上的救生用的浮塊,指不定,還是能逃得。
可,這一跳,顯然,是出乎意料,倆個人落水,加上不懂水,靜太大,頃刻間就被甲板上的兵察覺,他們大喊著,而,阿蘭家小漁船的旁邊,赫然停著一艘家較大的船。
此刻,那艘船率先向們撐了過來。
Advertisement
阿蘭的水縱是極佳,因一手攬著夕往前游,自是快不起來,眼瞅著就要被那兵追上。
正在這時,突然,但聽慘聲連連,接著是有人墜落海中的聲音,阿蘭覺到眼前一黑,海水似乎變一汪黑海時,驚愕地抬起眼睛,看到,今日的海上,起了不可思議的濃霧,霧里,一艘遍通黑的船若若現,傳上,揚著一面同樣黑的旌旗,旗上沒有任何花紋,純粹的黑,只在中央有一道的月牙,仿佛沁出一汪來,深紅詭艷。
而現在,這艘黑的穿上,出無數枚箭,其中還夾帶數支火箭,但,這些箭并沒向他們,目標恰是們的后。
阿蘭攬住夕的手一滯,黑船上,早下一條銀,不容阿蘭躲避地,纏住的子,阿蘭依舊攬著夕,銀一提,借著這一提,倆人一并被擄至船的甲板上。
銀,是鋼索纜線,勒著,有點疼,但,卻是大船的必備,也因此,他們得以從海里,避過接下來的一場劫。
夕撲在甲板上,看到,甲板也是黑的,如墨一樣的黑,黑到死氣沉沉。
眼前,突然出現紅閃耀,下意識地抬起臉,漁船和船都著了極大的火,火焰里,可看到,有人影痛苦地掙扎,隨后,一個個跳進海里。
火,熄滅了。
月華暉照下的海水,卻洇出大片的來,慘聲,更甚方才。
那洇著大片水的海里,有一種魚鰭劃過,劃過出,鮮一大片一大片地漫出!
“鯊魚——”阿蘭的口發出一聲驚恐地聲,接著,阿蘭猛地站起,徑直撲到船欄上,撕心裂肺地道:
“阿爹,阿媽!”
雖然,夕不清楚鯊魚有多麼可怕,但,瞧得見,跌海里兵,被這些兇猛的魚悉數吞噬。
那片海水里,只有著危險意味。
爬起,用力拽住阿蘭的手臂,阿蘭的父母在甲板之上,倘若之前,還有一些存活的希翼,現在,無疑是連最后一份希翼都被殘忍地毀去。
“阿蘭,堅強一點!”拍著一頭扎進懷里的阿蘭的后背,除了這句話,真的不知道能說什麼。
與至親的生離死別,經歷過。
除了自己走出來,其他人能幫的真的很。
阿蘭的哭泣不再有聲音,一個人,若悲痛到極點,反而會哭不出來,或者,連哭都不能夠。
一如曾經一樣。
“來人,把金真族的姑娘帶到下艙去,另一個,關到艙底。”們后,突然傳來一看似頭領的斥話聲。
阿蘭驚覺從夕懷里抬出頭來,轉攔住要來帶夕的兩名著黑勁裝的男子:
“不,是我姐姐,也是金真族的姑娘!”
“小姑娘,莫當我們是傻子,語音上還是聽得出來。”那頭領嗤地一笑,不屑地道。
金真族隸屬西域,西域與三國接壤,故而,有部分族民在三國的邊境縣鎮生活,也因此,學會了漢語,可,即便如此,終究是帶著濃重的口音。
這,也是夕一醒來,就覺得阿蘭帶著濃重口音的原因。
而夕自是襄親王府的郡主,當然不會帶著有濃重的口音。
“阿蘭,不要。”夕怕阿蘭與他們起什麼爭執,輕輕拍了拍的手,遂轉回子,迎向來人。
只這一轉,但聽得,那個穿著古怪族服頭領樣的人驚呼一聲,這聲驚呼,十分地突兀,接著,他傖然跪倒于地,雙手向空中,那種姿態,就好像蒼勁的老樹,努力延展自己的枝干迎向一樣:
“謝長生天!將我們的族長又還給我們!謝長生天!”
說完這句話,他跪叩于地,他后,一并排枕著黑男子,也隨著他的作,悉數跪下。
阿蘭的長得大大的,有些莫名其妙,夕的容卻是淡然不驚的。
就站在那,目凝視這些跪倒于地,拜叩的族民。
許久許久,那頭領方起,步子蹣跚地行至夕跟前,一張遍布皺紋的臉上,淌下兩行淚來:
“族長,等了這麼多年,您總算回來了,風長老見到您,一定十分欣。這麼多年,這麼多年啊!”
夕著他,心下,清明。
他將認錯了。
的母親,也就是被囚在旋龍中的子,恐怕正是眼前這些族民的族長。
據手札里的時間推斷,眼前的族民,不是金真族那麼簡單,絕對不是。
“可否借一步說話?”
夕啟,語音平和。
“當然,族長,這邊請。”那張布滿皺紋老臉的男子,了一下淚水,迎著夕往上面的艙行去。
那些跪叩在的黑勁裝男子,這才紛紛起,依舊如雕塑一樣,樹立在船欄的四周,接著,一聲尖銳的嘯,那些海水的魚鰭,都往一個方向聚攏,接著,不見。
阿蘭長大的稍稍合攏,早有黑男子,將帶往底艙。
這是一艘很大的船,上面就建有三層,底下,還有底艙。
在那時,這樣的船,除非是帝王乘坐的船輦能有如此大的氣魄。
由此可見,這麼多年來,苗水族不僅沒有真的銷聲匿跡,反而,逐漸壯大起來,至于金真族,恐怕,正是命于苗水族。
夕漸漸想明白這些,唯一沒想到的,是的親生母親,會是苗水族的族長。
不過,手札中提到過一句,母親曾認為的錯,錯在于的份,錯在于容貌。
這麼一聯想,的確,有什麼份是大錯呢?
在二十年前的會盟結束后,苗水族慘遭三國夷族,除了,族長這一個份之外,不做他想。
進得第三層的艙,頭領引著往正中一個艙室行去,剛進室,就看到,地上鋪著一塊似乎很猙獰的魚皮,頭領見夕的腳步滯了一滯,忙笑道:
“看我都糊涂了,族長很討厭這類兇猛的制的皮毯。”
說罷,道:
“來人,迅速撤下這些鯊魚皮!”
本來守著艙室的兩名男子即刻上的前來,將這塊鯊魚皮抬了出去,底下,出的木板,依舊是選黑的,正中,有一點的月牙,和那飄揚的旗幟上的圖案完全一樣。
這,難道就是苗水族的族旗嗎?
夕對此事沒有一點印象的。
室四壁,皆是暗黑的,有些抑的詭魅。
此時,唯有一點的燭影搖曳,映出些許的亮。
“族長,您坐。”那頭領的聲音里,知道現在都是按耐不住的激。
夕止住步子,卻并沒有坐,直睨向那頭領,道:
“為什麼認定我是族長?你之前也聽出來,我的口音并不是你們的族人。”
“族長被他們關旋龍這麼久,口音潛移默化,又有什麼奇怪呢?是我們辜負了族長的托付,連累族長了這十九年的苦!”
說罷,頭領就要跪伏于地。
夕一手扶住他,輕聲道:
“倘若我說,我并不是你們的族長呢?”
“怎麼可能,普天之下,族長的容貌是唯一的。”
“如果我說,我是的兒,你信嗎?”
頭領臉上的神隨著夕這一句話略略僵了一下,他大著膽子細細端詳了夕一眼,沉聲道:
“可否容我瞧一下您的手腕?”
夕為假猶豫,出雙手手腕,朝向頭領。
在室的暗黑背景下,就著燭影曳紅,夕左手的手腕上,清晰地映現出一道月牙形的痕跡。
猜你喜歡
-
完結25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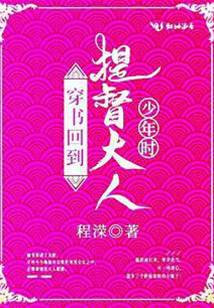
穿書回到提督大人少年時
她書穿成了女配,可憐兮兮地混在公堂的男男女女中,正等著知縣大人配婚。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按照劇情她注定是炮灰,超短命的那種。 她不認命,急切的視線在人堆裡可勁兒地扒拉,終於挖掘出他。 夭壽呦,感情這小哥哥,竟是男二! 連女主都無法覬覦的狠人! 這位爺有秀才功名在身,卻被至親算計,入宮成為殘缺不完整的太監。 他生生地熬過種種苦難,任御馬監掌印太監,最後成了人人敬畏的提督大人。 他曾顛沛流離,人人嫌惡,也曾位高權重,人人討好。 成為看盡人生百態,孑然一生的權宦。 但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壽終正寢! 只要她抱緊他的大腿兒,定能擺脫螞蝗般的至親,待日後做了大宦官之妻,更是吃香的喝辣的,還不用費勁巴拉的相夫教子。 小日子簡直不要太美好,撿大漏啊! 他一朝重生,再回少年時,尚未入宮,更未淨身。 眼下,他還是小三元的窮秀才,父暴斃而亡,母攜家資再嫁。 他浴血歸來,渾身戾氣,可一時善心,就多了個嬌嬌軟軟的小娘子! 說啥他這輩子也不淨身了,好好地考科舉,走舉業,給她掙個誥命夫人做,再生幾個小崽子玩玩兒……
44.7萬字8 23161 -
完結1578 章
這個娘娘有點懶
【她拒絕皇上的冊封,從此走紅後宮! 】不靠譜的爹死得早,青梅竹馬的男人是個陳世美,慘被拋棄的蘇幼儀入宮當個小宮女,不想被嚴肅臉皇上一眼看中。 「聽說你很漂亮?」 蘇幼儀白眼一翻,好好的大皇子不務正業,天天跟人吹噓她漂亮,這下可怎麼辦……
284萬字8 19268 -
完結391 章
王爺今天又在失寵
【蘇爽甜+穿越女強+團寵1v1雙潔】 傳聞瑾王楚千玄殺伐果斷,是個連太子都要敬三分,囂張跋扈的主兒。 然而他卻被將軍府那心狠手辣的流氓嫡女給強了! 起初: 楚千玄陰著俊美臉龐,咬牙切齒:“白燕飛,敢如此折辱本王,本王定要將你挫骨揚灰! “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白燕飛撂下裙子睡完就跑。 後來: 楚千玄邪邪逮住想溜的小女人:“不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么? 跑什麼跑? 繼續! ” “......” 楚千玄抱住她低語:「真香! ”
72.1萬字8 15748 -
完結942 章

特工二小姐:毒妃好俏皮
她一朝穿越成鄉下小米蟲。吶尼?姐姐暴亡,還要把自己也送給變態當玩物?百變小魔女化身千面人,追查殺姐真兇,兵部侍郎欺負我無父無母小孤女!姐鬧得你家破人亡!丞相之子變態?姐讓你不得好死。咦,世子爺不是病弱的廢物麼?怎麼暗地里好強大?
157.1萬字8 4196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