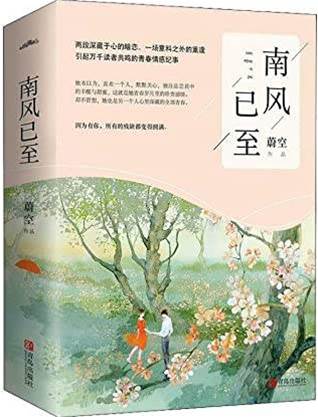《他從火光中走來》 第59章
那天是萬里晴空。
可追悼會門口的人卻覺得烏云罩頂,背后冷風肆意。
林陸驍從始至終目都沒在上停留過一秒,哦,有一秒,目快要及時被他及時剎住收回。
孟國弘在林陸驍轉走后,目瞥了眼南初。
后者的眼睛就跟長在林陸驍上似的,恨不得給他刨個出來,他搖搖頭,到底是沒說什麼,進了堂。
這幫人也有段時間沒見林陸驍,想著等林陸驍跟老隊長說完話,要不要過去打個招呼,又猛然想起南初跟隊長的事兒,事就有點尷尬了。
當初輿論發時,他們選擇沉默,如今,也沒資格再說任何一番話,更沒資格去探聽八卦。
劉夏翰率先開口,“走吧,我們進去。”
眾人都去看南初。
南初倒是坦率,也不避諱,就直勾勾去瞧林陸驍的背影。
那表,與其說眷不舍,倒更多是欣賞一件完的景。
嚴黛一把將拽進去,“別看了,進去吧。”
南初坦然笑笑,最后深深地看了那人一眼,轉跟進去。
……
林陸驍雙手抄在兜里,靠著門口的大樟樹跟老隊長聊天,也許是見到老故人了,姿態難得松弛。
老隊長退休后倒越發神了,眉宇依舊軒昂,說話中氣十足,林陸驍沖他笑笑,眼勾,氣頓顯,“我怎麼瞧著您又年輕了?”
老隊長不吃這套,冷哼:“你倒是沉穩了不。”
林陸驍笑笑,目瞥開,沒作聲。
老隊長:“我前陣去過隊里,孟說你去了鹿山,你小子又犯錯誤了?”
“沒吶。”他懶洋洋的。
老隊長用指頭了下他的太,著別忽然深長起來:“還記得你剛下隊那年?二十三還是二十四?嚯——那子,張揚跋扈,我要你爹給你掄起來打!是時候了,該找個靠譜的定下來了,別整天這麼吊兒郎當的晃著,男人最好可就在這麼幾年。”
Advertisement
說完,又嘆了口氣,“小九兒這孩子也是可惜。”
林陸驍低頭,默然。
都可惜。
老隊長拍拍他的肩,“行了,進去吧,送小九兒最后一程。”
……
追悼會在三點舉行,時間還沒到,大家都在靜等。
里頭掛著黑橫幅,堆滿花束,人多,卻安靜,大家都不敢大聲說話,仿佛怕擾到安靜躺著人。里頭都是悉的面孔,但不是敘舊的時候,點頭示意過,則安靜立在一側。
南初轉首之間,看見林陸驍跟著老隊長進來,站到邵一九的邊上。
邵班長眼睛通紅,剛哭過,林陸驍拍他的肩,以示安。
邵一九:“這次回來待幾天?”
林陸驍眉目清淡,目落在靈堂中央的棺木上:“明天回去。”
“這麼趕?”邵一九驚了下。
“嗯,不好請假。”
“一年滿能回來嗎?”
“不知道。”
這事兒還真不知道,組織上原先調派是一年,但往往被派出去的基本都待了兩年,加上那邊領導也提過讓他再留一年。
邵一九失落,“啊。”
林陸驍照著他腦門就是一記,“啊什麼,在哪兒待不一樣?別我不在就懶,等我回來,一個個查。”
兩人談聲音低。
南初在一旁聽得清楚,好久沒聽他這麼細碎地說話聲,雖不是跟說,竟覺得十分滿足。
十分鐘后,追悼會正式開始。
原本氣氛還沒那麼抑,結果看見小九兒的時,所有人都忍不住,就連南初就沒忍住,眼淚豆大一顆顆往下掉,用手抹掉,發現越越多。
吸了吸鼻子。
林陸驍在旁站著,大概是聽見靜,下意識側頭看一眼。
自己眼眶也是憋的通紅。
被人打,沒哭;被人黑,沒哭。
Advertisement
分手也沒見哭。
還以為這人天生淚腺不發達。
這麼看來,如果躺在里頭的是他,興許還能哭上兩嗓子。
想來又覺得自己愚蠢,角不自覺掛上一抹自嘲。
告別儀式結束,小九兒被推進火化房火化。
原本單位打算將小九兒葬進烈士陵園,但小九兒的爺爺堅持要帶小九兒的骨灰葬回老家。
一個小時后。
骨灰從窗口送出來,著那深棕的四方盒子,滿頭蒼蒼白發的八十歲老人兒再也控制不住,哭倒在地,悲慟長喊:“小九兒,跟爺爺回家吧——”
“別在外面漂泊啦——”
……
追悼會結束。
安排六位藝人離開的保姆車已經在殯儀館門口等。
南初出去的時候,林陸驍站在車旁跟一個士兵在說話,手里捻著一煙,金的籠著他,肩上勛章在發,他側面廓十分朗,眉眼間已不似里頭那麼凝重,帶了些懶散。
士兵似乎是他軍校的戰友,激地拉著他說話。
“你現在在哪兒啊?”
林陸驍:“鹿山支隊。”
“你怎麼跑那兒去了?離我們這兒十萬八千里吧?”
“還行,坐火車得一天吧。”
“前陣兒老楊結婚你怎麼沒去啊?咱宿舍那幾個兄弟就你丫沒去,老楊念叨半天,人說了,等你結婚有的好的!”
他低頭笑笑,“等到了那天再說吧。”
兩人說話被打斷。
徐亞跟劉夏翰上車的時候了聲林隊,林陸驍停下來,轉頭看他們,“嗯。”
南初站在他后,距離大概兩步。
他背影高大,剛好幫遮了刺眼的。
“林隊,我們走了。”
六人一個個道別。
他一一點頭,表倒也珍重,就跟普通戰友似的。
Advertisement
南初是最后一個。
重逢以來。
林陸驍第一次把目正式落在上,那雙深黑的雙眼,在日下顯得特別亮和深沉。
他雙手抄在兜里,靜靜著。
難得沒皺眉,沒抿,看上去還有耐心地等的告別。
南初站在車門邊,一黑,長發跟綢緞似的散在后,及腰。
遲遲沒有開口。
不說,林陸驍的目就無法轉開。
這詭異的沉默竟然達了好幾分鐘,可誰也沒有催他們。
車里五人只是沉默,也有點驚訝,原本以為這兩人只是干柴烈火,可現下這形,連傻子都能看出來,這空氣中流的曖昧太讓人不舍了。
如果不去想當時的場景。
那氛圍曖昧,總覺得下一句話從南初里蹦出來的應該是——我們結婚吧。
半空中有片枯黃落葉翩翩墜,南初目隨著那葉子轉。
葉子落到車頂上,南初吸了口氣,抬頭去看他,一雙黑眼明亮,聲音清脆道:“再見啦,林陸驍。”
然后轉上車。
頭也不回。
風起。
落葉重新被卷起。
南初尋到靠窗位置坐下。
目轉出去,瞧見那片葉子剛好落地,再也沒吹,仿佛生了,一切塵埃落定。
后方的男人,雙手抄在兜里,忽而著角笑出聲,那笑里頗自嘲。
他的耐心。
這輩子就在這人上耗了。
……
林陸驍在第二天回了鹿山,同時接到上級調令派遣期延長一年,他本人倒沒什麼異議,似乎樂意這個結果的。只不過今年值要提出回家一趟,不然老頭兒過年寂寞。
秋的時候。
趙國找到了朋友,變得格外膩歪,特別是晚上通電話的時候,躲在被窩里哼哼唧唧,被林陸驍丟枕頭還不肯停。
Advertisement
不過無所謂。
趙國把這都當做是來自單狗的嫉妒。
有了的滋潤,趙國人倒是越發意氣了,跟媳婦兒打電話時,時不時叮囑兩聲:“哎,老婆,你要是得空也幫我兄弟介紹介紹,你那誰誰誰不是還單嗎?我這又一兄弟,賊帥,三十了。”
趙國媳婦兒不信,他那兄弟見過幾個,長得都賊眉鼠眼的,哪有賊帥的,“三十了咋還沒朋友?”
趙國:“我這兄弟太敬業了,畢生力都獻給國家了。”
趙國媳婦兒呵呵一笑,自然是不信,結果有一次,跟趙國開完房間,趙國進去洗澡的時候,無意間在他手機里看見林陸驍的一張照片,當時拍的是另一個室友,剛好林陸驍靠在床頭看書當了背景。
“這人誰啊?”
“就我那三十的兄弟啊,牛。”
“這條件會找不到朋友?”
趙國頭發,說:“都說了他敬業。”
“……”
結果,林陸驍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況下,被相親了。
一個周末,趙國拉了林陸驍去自己家吃飯,結果沙發上坐著倆姑娘,一個趙國媳婦兒,一個趙國給他介紹的相親對象。
那姑娘看見林陸驍,先是上下一掃,審度地看他兩秒,然后滿意地沖趙國媳婦兒點頭。
林陸驍能保持最后的風度,沒有甩開趙國的手離開,是因為趙國說了一句,“我媽知道你要來,特意給你做了一桌菜,你走了我找誰個吃?”
趙母的熱是他無法抗拒的。
飯桌上,那姑娘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林先生,你是北潯人?”
林陸驍低頭飯,冷淡一聲,“嗯。”
姑娘第二句:“有房麼?”
他勾勾角,頑劣心態又上來了,“沒有,買不起。”
趙國媳婦兒打圓場:“正常啦,北潯那地方房價多高呀。”
姑娘頗憾地看著他,“那車呢?”
林陸驍:“有一輛。”
姑娘驚喜,“也行。”
“兩個的,很久沒騎了。”
“……”
戰線被拉長,姑娘不依不饒:“你父母做什麼的?”
林陸驍夾了塊放進里,說:“打工的。”
至此。
姑娘就有點意興闌珊了。
吃晚飯,林陸驍跟趙國在臺煙,“怎麼樣,那姑娘?”
林陸驍叼著煙,雙手抄在兜里,一只腳懶散地踩在臺欄桿的石階上,“一般。”
“這他媽還一般?說句實話,那姑娘比我媳婦都好看!”
林陸驍含著煙,哼笑一聲:“那是你沒見過好看的。”
趙國一聽就不樂意了,義正言辭地勸他,試圖給他“歪曲”的思想,掰過來:“驍哥,咱可不是這樣,你要按照明星的標準找朋友,那你就是提著燈籠都難找,找媳婦兒主要是過日子,人回過日子就行了,太好看了,放家里,咱也守不住哇……”
屋里。
趙國媳婦兒問表妹,“你覺得怎麼樣?”
表妹想了想,“除了長得帥點兒,條件這麼差,還是個消防隊的,在他山里,你也看到了,要房沒房,要車沒車,又是個外地人,還不如你們家趙國呢!”
趙國媳婦兒抻了臉:“怎麼,你想要我們家趙國不?”
表妹噘,“我只是打個比喻,我怎麼說也是一碩士畢業,工作也比他面,除了父母都是農民,別的條件我都比他好太多了,這不是委屈我了嗎?”
“行,你要不喜歡再議。”
表妹想想覺得那人還帥的,一聽要回絕,急了,“別,要不跟他試試?”
+++++
夏末,南初接了一部戲,《炮轟前男友》。
同組演員還有嚴黛,進組第一天就兩人就在門口見了,到也沒什麼好話,平時見面互懟慣了,眼下你一句“你又胖了?”我一句“你是不是又去打玻尿酸了?”
而后用力在對方臉上一擰,以示友好。
南初跟嘉禾解約之后,嚴黛了沈宗手下的藝人,兩人在片場休息的時候,偶爾會吐槽。
“真不知道你以前怎麼過來的,沈宗整個就是一臺榨機你知道麼?給他一個橙子,就他那分貝立馬能給你炸!”
說完,嚴黛還形夸張地模仿起來。
南初坐在椅子上,手邊攤著一本圣經,“榨機?嗯,這詞新鮮。”
“哎說認真的,沈宗都這把年紀了,還不找朋友,你說他是不是gay?”
南初低頭翻經書,搖搖頭:“不像。”
嚴黛意興闌珊,本以為能抓個大料,下次沈宗再吼就威利。
拍攝進行半個月。
兩人突飛猛進,嚴黛上哪兒都要問南初去不去,平時說話又喜歡跟南初抬杠,連劇組工作人員都迷糊這兩人的關系。
到底是敵是友?
拍攝進行到一半時,編劇給劇本加了個新角,頭天晚上下了夜戲,徐智藝進組。
因為徐智藝的臨時加,原本屬于嚴黛的戲份忽然被減了一半。
這天,嚴黛跟徐智藝有一場捉在床的戲,原意是嚴黛撲過去把徐智藝按倒在床上,然后了的意思,大致就是意思一下,個肩什麼的,結果嚴黛不知道是不是用勁用猛,劃拉一下給人整件襯衫給扯下來,兩對白就這麼赤的暴在鏡頭前了。
嚴黛忙坐起來,點頭哈腰態度良好地給人道歉,“智藝,沒事吧,我真不好意思。”
徐智藝瞥一眼,冷淡搖頭,不聲把服穿回去。
之后,有人來探徐智藝的班,在換裝室發生了點不可描述的事,一道小哥去收服裝的時候,聽見里頭咿咿呀呀人的,還有男人重的息,面紅耳赤的往回趕。
剛好被前往換服準備下一場戲的嚴黛和南初聽了個正著。
嚴黛說:“來我們現在推門進去,嚇不死。”
南初興致缺缺。
嚴黛:“哎,當初可是把你的事兒出去的,你就現在去門口錄個音發給那些營銷號料,你都不算過分。”
南初笑笑:“你平時多吃點核桃補補腦吧。”
“你什麼意思?”
“夸你呢。”
“你當我傻呢?”
“是啊。”
瞧瞧,瞧把聰明的。
嚴黛哼一聲。
徐智藝在娛樂圈的生存方式確實是所不齒的,嚴黛這人還有原則,再沒有片約,再不紅,也不會靠去換取任何資源,這是看不起徐智藝的一點。
如果是以前。
南初也許會自認倒霉被人捅一刀就算了,反正也不在乎。
早年拍戲的時候,有個導演說過那時的南初像個黑天鵝,其實不夠準確,那時的南初更像是白天鵝。
而如今,從外表到骨子里的南初,才是真真正正的黑天鵝。
報復一個人最佳的方式。
努力企及想要拽在手心里的東西,你永遠比先有,而人家拼命往上爬時,你不費吹灰之力直接登頂,看著,嫉妒和發狂瘋長,卻不能耐你何。
秋的時候。
徐智藝被了一把黑料,陪睡艷照,網上還流傳三分鐘種子小視頻,徐智藝微博底下淪陷,“正義”的網民們又集殺到徐智藝的微博底下實行“道德裁決”。
不堪目的話語,要多難聽有多難聽。
徐智藝三天沒出通告,把自己關在家里,漠然看著手機里的一切,眼淚早已淌干了。
猜你喜歡
-
完結563 章
於他掌心驕縱
傳聞,臨川市一中有一位高冷學霸。 眼高於頂,恃才傲物,這些形容詞都不足以形容他。 聽說被他拒絕過的女生,能排隊到法國! 直到某一天,眾人看到了那一幕。 小姑娘紅著眼睛,走到男神的跟前,扯住他的一角襯衣衣襬,擦著眼淚。 “……” 眾人覺得這女孩下一秒應該就要離開這個美麗的人間。 小姑娘聲音哽咽,帶著鼻音“他們不喜歡我,是不是我哪裡不夠好?” 那位傳說中的高冷學霸,聲音格外溫柔,耐著性子哄“那是他們冇眼光。” 小姑娘仰起頭,黑白分明的眼睛帶著水光“媽媽也不要我了,他們都不要我了。” “我要。” “……” 最初相識。 男人冷淡而又孤傲“既然住在同一個屋簷下,那就約法三章。不要敲我門,不要說認識我,不要叫我哥哥。” 後來…… 男人將試圖逃跑的小姑娘禁錮在牆角“怎麼不叫哥哥了?” “叫一聲哥哥,哥哥疼你。” 1v1,甜寵文
95.8萬字8 42105 -
完結1208 章

一胎二寶:總裁爹地蜜蜜寵
慘遭未婚夫設計陷害,她丟了公司,一無所有,被逼得背井離鄉。五年後,她帶著一對雙胞胎歸來!麵對五年前的仇人,兩個萌寶果斷找了個大帥哥給她撐腰,可是,為毛這個大帥哥和她兒子長的一模一樣?冰山大總裁傲慢的扔下一紙契約:「女人,我們談談孩子的撫養權。」「不談,孩子是我的!」某男直接把契約換成結婚證:「好,孩子是你的,你是我的!」--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231.2萬字8 38426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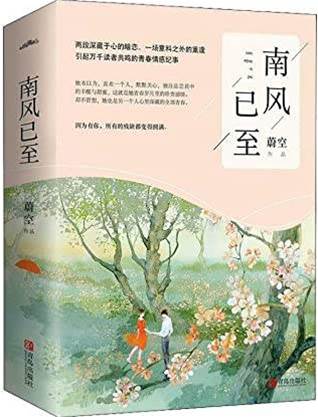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225 -
完結520 章

封少的隱婚丑妻
她將他從植物人狀態救醒,他不嫌棄她容顏盡毀,婚后寵她入骨,她以為余生都是幸福,后來,他的白月光回來了!她身懷有孕,不想離婚。而他絕情至極,步步相逼。直到一場車禍,一尸三命。他瘋了!從此不分晝夜坐守在洛云初的墳墓前,多年后,一個美艷凌絕的女人帶著可愛的雙胞胎兒子從他面前路過……他不顧一切地抱住了她。“初初,別離開我!”
93.8萬字8 94359 -
連載604 章

三個幼崽殺瘋了,我負責吃瓜
江綰嫁墨書硯三年,連手都沒碰過, 她一氣之下把墨書硯給辦了,然後溜之大吉。 六年後,她帶着三個可愛萌寶迴歸, 翻身成爲赫赫有名的神醫,還公然住進前夫家。 墨書硯一臉冷淡,“你是不是對我賊心不死?” 江綰嗤笑,“你可真是想多了,我追求者無數, 犯不着在一棵樹上吊死!” 後來,著名影帝、珠寶商、金牌律師…… 各界大佬,紛紛追在江綰身後, “江小姐,你孩子缺不缺後爸?” 墨書硯終於慌了,一手將這片‘森...
107.6萬字8 40146 -
完結162 章

西棠
許西棠是許家領養的女兒,和晏家少爺有婚約。 後來,晏少爺很識時務地放棄她這個養女,選擇了許家回歸的真千金並與之訂婚,養父母於是安排她另嫁。 那樁婚事她不願意。 走投無路的訂婚禮前夕,她得知晏少爺的小叔晏西岑從東京飛回國,於是,她懷揣著一份無法言說的心
49.1萬字8 592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