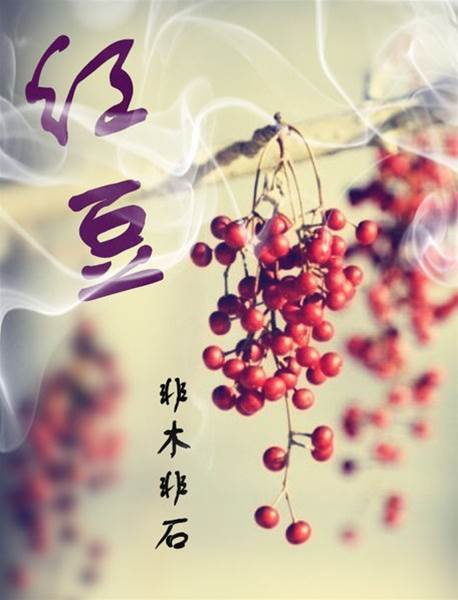《給你甜度滿分的我》 第20章 甜度20%
賀隨蹲下,修長的手指撿起碗里的手機, 指骨抵住機輕輕敲了敲馬上要死的臭妹妹的發頂, 漆黑的眼底無波無瀾:“死誰也不死你。”
兩人靠的近, 姜稚月有意屏住呼吸,可上那酒味依舊濃烈。
的腦子變得暈乎乎的,蹲久了胃里翻騰起一惡心。
賀隨從錢夾里拿出張整錢放進鐵碗, 拎起孩的手臂離開, 到路的另一側, 他松開手, 眼前是黑漆漆的發頂, 對方自知理虧不敢抬頭直視他。
賀隨剛開始是有點生氣,但不知怎得, 看見像被拋棄的小孩兒蹲在那的時候,那氣突然消散了。
尾酒的后勁兒上頭, 姜稚月頭重腳輕, 腦袋一沉直接把頭抵在面前人的口。
賀隨沒躲, 任由那顆堅的隕石墜落進他懷里。孩茸茸的發頂輕輕蹭了蹭他的服,聲音:“學長, 我沒喝多, 我真的——只喝了一點點。”
“姜稚月。”他第一次認真地﹑完整地的名字, 三個字經過低沉的嗓音過濾,自帶迫。賀隨停頓幾秒,拖長音調說,“你不是很聽話啊。”
姜稚月起脖頸, 意識混沌不清,印象里只有爹會用這種語氣訓。
姜別到的時候,看見的就是這副說不清道不明的親畫面。他狐疑地拽過姜稚月,然后更加狐疑地看向好友:你竟然不推開?
那似有若無的木質香消失,取而代之的氣味偏向茶樹的香。
姜稚月的腦袋換了個膛抵住,“爸爸,你怎麼換香水了?”
姜別的臉很不好,拉開的腦袋冷聲道:“你換了個爹。”
“……”
賀隨靜靜站在一旁,“你們直接回家?”
Advertisement
姜別點頭:“謝了,你也回寢室吧。”
賀隨垂眸,從口袋中掏出一個致的盒子,“小朋友的生日禮。”
姜別一愣,表有些不可置信,自從流回國后,他發現賀隨越來越有人味了。
盒子里是一條手鏈,款式簡約,只鑲嵌著一顆通晶藍的石頭,看不出材質,不過賀隨送出手的東西價格定然不菲就是了。
姜別闔上禮盒,側頭意味深長睨了眼副駕駛上的孩,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多想了,總覺賀隨的人味是他妹激發出來的。
姜稚月從上車后開始昏睡,一路睡到目的地,車子上緩沖帶劇烈顛簸,猛然轉醒。
邊的人惻惻看著:“還知道醒啊。”
姜稚月深以為如果再晚醒那麼一分鐘,今晚就得睡在家里的車庫。置架上放著致的禮盒,語氣揶揄湊過去:“哥哥,你找朋友了?”
姜別沉默兩秒,用同樣的語氣懟回去:“你男朋友送的。”
姜稚月先是一怔,瞬間識破他的詭計,于是將計就計擺出一副可惜的表,“你見過他了啊,我還想改天一起吃頓飯的。”
這次到姜別怔愣住,一時間反應不過來,角得逞的微笑來不及斂起。
姜稚月眨眨眼:“他帥不帥,是不是很溫,有錢嗎?”
姜別緩緩打出一個問號:?
“我連男朋友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哥哥你竟然都見過了。”手拿過禮盒子,晚上只和賀隨見過一面,禮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誰送的。
所以,哥誤以為是妹夫的那個人,想都不用想就能猜到是誰的臉。
姜別眸沉沉,屈指敲了兩下方向盤,憋出一句穩住氣勢的話:“最好不是。”
Advertisement
姜稚月好不容易消停了的想法因為他這句話又冒出來,難不哥真的對至好友有其他方面的意思?所以聽到男朋友疑似賀隨時,表沉宛如煤炭。
姜別往后靠進椅背,不清緒開口:“你能想象賀隨別人哥嗎?”
姜稚月沉思半刻,毅然決然搖頭:“想象不到,但知道很驚悚。”
“那不就得了。”
姜稚月每年的生日通常是在家里過,但今年父母相攜去國外出差,家里只剩下和哥。儀式不能,姜別拜托家里的阿姨做了一桌子的菜,應父母要求,在他們經常坐的位置上擺放兩臺平板,吃飯時進行視頻通話。
場面一度很詭異,白邊框的平板電腦顯示兩個人頭,兩個人頭還面帶笑意。
姜稚月對面是媽媽,當夾起一塊辣椒炒時,母親溫的提醒聲響起:“小稚,吃辣椒,你嗓子容易啞。”
姜稚月默默收起筷子,專注地低頭喝粥。
姜別對面是父親,男人一向沉默寡言,吃飯時要求小輩食不言寢不語,將爺爺古板的格繼承了百分之百。
到了切蛋糕的時間,姜別關上燈,除了蠟燭的亮,姜稚月手腕上的那顆珠子泛起熒。
賀隨送的那條手鏈上鑲嵌著螢石,也就是俗稱的夜明珠。
姜別意興盎然打量那顆珠子,通明無雜質,賀隨的手筆可真夠大,要是哪天他真出手,他這臭妹妹不一定能穩住不心。
姜稚月輕輕那顆珠子,冰涼,模糊的視野出現這抹微,竟然覺得……異常安心。
周一下午有課,姜稚月次日上午回學校,剛到宿舍樓底就被部長一個電話去學生會。
A大的校籃球選拔賽進行至最后一賽段,建筑學院對陣數學與統計學院。比賽安排在周一下午五點鐘,誠邀廣大校友前去聲援。
Advertisement
姜稚月被書到現場幫忙,同樣沒課的梁黎也在現場。兩個小姑娘搬不桌子和計時牌,杰打發們去標注座區號碼。
姜稚月本想和梁黎一同去倉庫拿號碼牌,不等開口說話,梁黎就垂著頭繞開走了。
姜稚月了,沒住,帶著一肚子疑問往育館的倉庫走去。
倉庫臨近更室,經過半敞的大門時,瞥見里面的人,賀隨單手拉住衛的擺,起一個弧度,被服包裹住的線條出,背弓起,肩胛骨凸顯而立。
姜稚月急忙捂住眼,背過提醒他:“學長,你沒關門!”
幾分鐘前有隊友換完服出去,大概沒有隨手關門的好習慣,只是沒想到被撞見了。
賀隨迅速套上隊服,兩條手臂在外面,白球服用紫滾邊,襯得他皮更白。
過窗簾罅隙傾斜而,纖塵在和的束間浮。
男生單手撐住門框,俯向前:“可以睜眼了。”
姜稚月捂住眼睛的手指悄悄移開一小個隙,出左眼端詳眼前的人,確定他并非半狀態,長吁一口氣放下手。
姜稚月有點后悔,竟然沒有拍的好習慣。
自從上次去過游樂場,陸皎皎天天在耳畔念叨賀隨長賀隨短,有次被念叨煩了,姜稚月頗為無奈用一顆糖堵住了好友的。
如果能用一張這樣的照片去換半天安靜的時間,穩賺不虧。
賀隨不知道打得什麼算盤,垂眸時注意到孩手腕上的手鏈,是他送的那條。
姜稚月順著他的目往下,視線定格在自己的手腕,耳尖一熱,悄悄將手進袖里,“謝謝你的禮,我很喜歡。”
賀隨站直,慢條斯理佩戴護腕,不經意掀起眼簾笑著說:“所以特意當面來謝我?”
Advertisement
姜稚月一噎,總不能說是來幫忙湊巧遇見,那豈不是太尷尬,而且的確想當面謝謝他。
賀隨勾,再次俯和孩對視,試圖在眼底找出一猶豫或者是窘迫,結果對方不避不讓回視他。
姜稚月抿了抿角,長睫輕著:“這次不是,等下次我專門來見你。”
賀隨臉上也看不出憾,略微一挑眉:“杰讓你們這些小生干活?”
姜稚月替部長辯解:“不是搬東西,安排下位置而已。”
賀隨垂眸睇,目測了下小姑娘的高,隨后抬步往對面的倉庫走,不忘提醒跟上。
倉庫暗,無數個高架子并列擺放,一進門就有霉味散發出來,夾雜著煙塵格外嗆鼻。
賀隨輕車路找到第五排的架子,拉開一把木質長椅放在桌上,作輕快邁上去。
凳子疊加椅子,勉強能夠到最上層。
姜稚月看著搖搖晃晃的凳子,十分不放心:“學長,要不我來?”
說不準輕一點,椅子能稍微穩固一點。
賀隨單手撐住架子最高的隔板,翻找箱子里的號碼牌,一年之久沒打掃過,隔板上積攢著一層厚厚的灰塵。
“要幾個?”他淡聲問。
姜稚月只好握住凳子,幫它加固穩定,“五個。”
賀隨找出一到五的號碼,穩穩當當站回桌上,然后輕松一躍落地。他遞過去,神松松散散,開玩笑的語氣:“你去問問杰,他是想讓你飛上去嗎。”
姜稚月接過號碼牌,掏出兜里隨帶的巾干凈表面。低著頭,又出一張干凈的紙巾,小聲說:“我可不會飛。”
賀隨彈開落在手背上的塵土,正要轉離開時,后的孩拉住他的手腕。
姜稚月手中攥著巾,低頭幫他干凈手背,的表認真極了,像清理一件致的工藝品。男生的手修長有力,指骨凸顯,他比其他人白許多,皮下埋藏的管清晰可見。
潤的自手背傳來,與握住他手腕的指腹形強烈的溫度對比。
賀隨靜靜歪著頭,看一點點將手上的灰塵干凈。
到最后,他意興盎然彎起角,“幫姜別過手嗎?”
姜稚月回憶幾秒,腦袋慢慢抬起來一點兒,不太理解他這句話的意思,“……沒有過呢。”
半秒未過,男生眼底笑意涌,聲音一如既往的低沉,但帶著不易察覺的愉悅:“這麼看,是我賺了。”
偌大的空間安靜空,賀隨的聲音被四周墻壁彈回沖進耳中,莫名勾得耳尖發。
姜稚月睜大眼,語氣有種討好的意味在里面,“學長,你千萬別和他說!你也知道他那個人,太小心眼了。”
賀隨難以想象平時姜別都是如何對待他妹,以至于提起他,姜稚月總是警惕再警惕。賀隨是獨生子,大概一輩子也會不到那種親近帶著嫌棄的相方式。
比賽下午五點開始,姜稚月下課后匆匆趕到比賽場地,彼時賽程進行過半,作為學校里唯一一隊能與建筑院打比賽不會輸太慘的隊伍,數院死死咬住分差,臨近最后一場,比分竟然被打平。
姜別沒上場,套著短袖坐在冷板凳上玩手機。他瞥見悄悄溜進觀眾席的影,掏出手機發消息:【帶水了嗎?】
姜稚月看到消息的時候很無語,翻開書包,里面一瓶農夫山泉還有瓶依云,姜別的臭病非依云不喝,繞到室外籃球場才買得到。
不過他連場都沒上,有什麼資格要水喝!
姜稚月低頭擺弄手中的水,還沒控訴完,賽場上突然傳來砰的一聲響,接著周圍先是寂靜半秒,隨后響起喧鬧的議論聲。
抬起頭,目驀然滯住——
靠近三分線區,賀隨單膝跪在地上,一只手著左腳踝,他背對線,側臉被刷上晦暗的影。而林榿則是拽住對方員的襟,憤怒的與他爭辯著什麼。
裁判上前勸阻,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競技運造的傷不可避免。
林榿猛地松開對面男生的領子,眼眶猩紅:“他故意的,你們都瞎嗎?”
聲音近乎嘶吼,整個半場都可以聽見他話中的容。
為了取得勝利,數院的人采取卑劣的手段,若放倒全場負責得分的MVP,下半場將會穩贏,然后代替建筑院參加申城大學生籃球聯賽。
陸皎皎憤憤扔掉手中的加油橫幅:“怎麼能這樣啊?”
姜稚月握住礦泉水瓶的手攥起,一言不發直勾勾盯著場上的眼神讓人不清緒。
賀隨跪下的那一秒,的心被狠狠揪起,那種皺的酸并不陌生,味過一次。
姜別上初中參加跆拳道比賽,對方趁他不注意狠狠用腳踢向他的頭,造輕微腦震住院三天。
原本老師們以為只是同學間的玩鬧。
但所有學生都清楚知曉,一個太優秀的人風頭太盛,容易被人妒忌,被仇恨。
之前是姜別,如今是賀隨,他什麼時候……能輕而易舉牽的緒了。
姜稚月嚨艱,不知該表出何種表,和旁的舍友代一聲,繞過比賽場往校醫離開的方向走。
臨時休息室,賀隨將傷的腳踝搭在椅子邊,皺眉等待校醫理妥當。
校醫配上消腫的藥水,仔細檢查過后不太放心:“我建議去拍個片子,踝骨錯位需要重新固定。”
賀隨凝眉,“這麼麻煩?”
校醫被他氣笑了,“傷的是你的腳,疼起來你還嫌麻煩不?”
林榿守在旁邊,雙手叉腰氣得不輕:“我就看見他們想搞你,三個聯防你一個,到最后使絆子踹你一腳,烏鲅魚。”
賀隨眼簾垂落,拿起一旁的冰袋進行冰敷,“你們最后一場好好打,得對得起他們的良苦用心。”
林榿半晌沒吭聲,他抬頭過去,視線越過男生清瘦的形廓停在休息室門前。
姜稚月靜靜站在那,外面有風灌進來,發頂豎起的兩呆被吹得左搖右擺。孩黑白分明的眼睛直勾勾盯著他,就是不說話,也不知道在那站了多久。
校醫出去車送病號去醫院,比賽馬上開場,林榿磨磨蹭蹭回到場地繼續和惡心的人打比賽,干凈的休息室中只剩他們兩個人。
姜稚月慢吞吞走到他旁邊坐下,拉開書包拉鏈掏出礦泉水遞過去:“學長,你喝水。”
賀隨腦袋上頂著一塊白巾,額發有些潤,連打三場力消耗不,一向直的脊背微微弓起。
賀隨看出的擔憂,挑起眉稍安:“摔了一跤而已,不至于看見我就要哭出來吧。”
姜稚月不吭聲,替他擰開瓶蓋,“我哪有。”
頓了下,也覺得自己的緒來得莫名其妙,猶豫補充道:“……就是想打人。”
賀隨屈起膝蓋,手肘支著膝蓋骨,聲音變得格外,怕小姑娘繃的緒,“現在不太行,等我傷好了讓你打。”
一直耷拉著的那顆腦袋終于愿意抬起來。
視線與對上,賀隨用沉靜的眼神看著。
孩的眼睛大而有神,眼尾微微下垂,笑起來時像一彎月牙,目永遠干凈純粹。
定格幾秒,賀隨先移開眼,“聽你哥說,你們倆小時侯學過跆拳道?”
姜稚月強裝鎮定的肩線松懈,低低嗯了一聲。不等補充上自己只是個辣這樣謙虛的話,就聽見男生低嘆道:“那我打不過你。”
不是。什麼時候說要打他了。
姜稚月后知后覺,他純屬想讓消氣,思及此,好不容易平復的呼吸再次屏住,心跳漸漸失去原有的頻率。
賀隨卻不曉得此刻孩的心理活,他垂下眼皮,很輕的笑了聲:“小朋友,記得手下留。”
作者有話要說: 很久以后,就【小朋友】這個昵稱賀家夫婦進行激烈辯論。
試論,賀隨遇到姜稚月時,二十一歲已過生日。
姜稚月十七歲馬上到十八歲,所以差四歲不到。
四歲一個,都可以叔叔了。
于是,小稚:好的,賀叔叔:)
——
更了一萬字哦,寶貝們就原諒我昨天沒更叭=v=
以后日更,基本在晚上九點十點左右。
猜你喜歡
-
連載1496 章
盛寵嬌妻:傅少,別上癮
「這姿勢怎麼演?」「躺著,我教你。」拍一場替身戲,沈未晞成了令人聞風喪膽的傅家掌權者→傅錦寒的女人。被最親最信任的人背叛又遭遇失身,她決定綻放實力活出自我,一心虐渣追尋夢想,並杜絕男人,然而傅錦寒強勢闖入她的生活。從此,沈未晞身軟腿軟心也暖,渣渣虐得爽翻天,愛情事業雙豐收。某天,傅錦寒求婚,沈未晞笑得像個小妖精:「沈影後的聘禮很貴喲。」傅錦寒給她戴上獨一無二的鑽戒:「我就是聘禮!」沈未晞:「這輩子,你都不許後悔!」傅錦寒摁住了她:「人、心、傅家、影視圈都是你的。現在就造個寶寶,五重保險。」【雙C,1V1,HE,甜寵】
215.5萬字8 17230 -
完結1542 章
霍爺家的小祖宗甜又野
傳說霍家四爺薄情冷血,不近女色,被迫娶了個又聾又啞的廢物嬌妻,嫌棄得第一天就打算扔去餵老虎。當夜,被吻得七葷八素的小女人反壁咚了霍爺。 “聽說,你嫌棄我?”他的小嬌妻清眸微瞇,危險又迷人。清冷禁慾的霍爺面不改色:“嗯,嫌棄得要命。” 見到她第一面起,他就知道,這是個要他命的妖精……
175.7萬字9.09 6651931 -
完結12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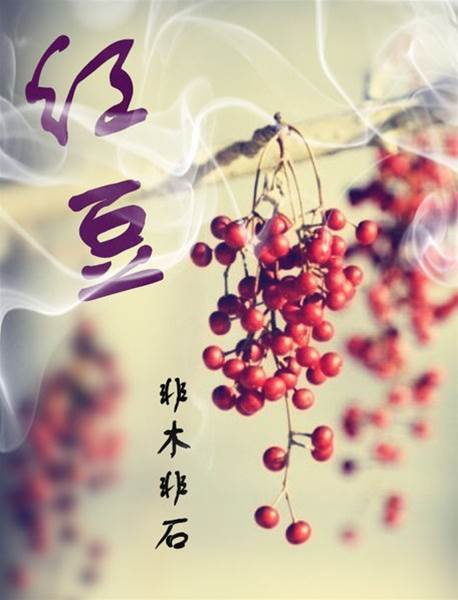
紅豆
他捏著手機慢慢把玩,似笑非笑說:“看,你守著我落兩滴淚,我心疼了,什麼不能給你?”
30.6萬字8 7556 -
完結118 章

遲一分心動
【追妻火葬場】年少的時候舒予白喜歡上了一個女孩兒跟她告白女孩兒頗為糾結地說:「你別這樣,咱們還要做朋友的」 長大后和女孩兒做了很多年朋友的舒予白決定放棄她另尋對象結果——相親時:相親對象壓低聲音抱怨:「隔壁桌的小姐姐一直盯著咱們看,她想幹什麼啊」 約會時:「小舒,你覺不覺得,後面好像有個女生在偷偷跟蹤咱們?」 開房時:舒予白捏著房卡開門發現某個聲稱和她是一輩子的好朋友的女孩兒穿著弔帶裙縮在床上黑白分明的眼睛安安靜靜地看著她...#裝直一時爽,追妻火葬場*雙潔,彼此是初戀*日更,每晚10:00前更新立意:在逆境中前行,不念過往,不畏將來。
7.3萬字8.18 53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