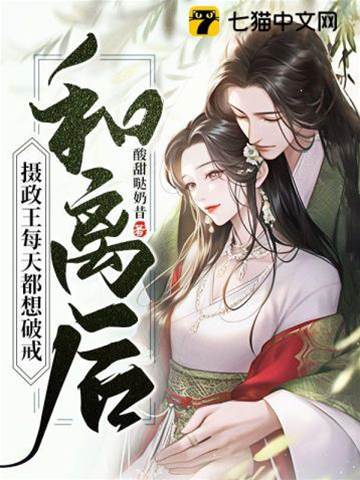《掌上齊眉》 第362章 堂審
除此之外,刑部大堂旁邊設下一隔斷,立著一面檀木雕花繪著仙鶴山水的屏風。
那屏風之后像是坐著什麼人,只是被屏風遮掩之后,又在旁邊角落,不被人察覺。
堂前衙差當界,外面圍滿了百姓。
朱門之外更是人頭攢,不人不進堂前,只能踮腳朝里探頭看著。
“怎麼來了這麼多人?”
“哪能不多,這審的可是豫國公呢,他勾結北狄,殺害朝中那些大人,還干了很多喪盡天良的事,照理說幾個月前就該審了,可一直拖到了現在。”
“聽說他不是握著陛下把柄嗎?”
“我知道我知道,好像是先帝詔,說是先帝爺當年想要傳位的不是當今圣上,而是另有旁人,好像連先帝爺也是被豫國公害的……”
蘇錦沅和蕭云鑫他們站在堂前,耳邊全是小聲議論的聲音。
先前“詔”的傳言鬧得太盛,再加上慶帝一直不肯下旨嚴審豫國公,讓的豫國公握著他把柄的謠言越發喧囂于塵,以至于京中幾乎無人不知。
此時哪怕堂審之前,周圍無數衙差看著,也有人低了聲音說著此事。
“你們說,先帝爺當初真的傳位給別的人了嗎?”
“那誰知道,說是當年就豫國公和蕭老將軍在呢,那蕭老將軍已死,就留下豫國公……不還有人說,先帝爺就是被人謀害的嗎……”
“噓!你不要命了?!”
有人膽子小,連忙扯了說話那人一下。
人群安靜了一瞬,說話那人也是臉微白,到底沒膽子議論更多,片刻后再說話時,就已經說起了今天堂審上,豫國公的那些事兒。
梁德逑坐于公堂之上,約能夠聽到外面傳來的那些議論聲,雖然聲音很小,可是“詔”,“傳位”這些詞兒卻依舊落進了耳中。
Advertisement
“梁大人。”
旁邊大理寺卿樊宏康臉有些青,“該開始了。”
要是再讓這些百姓議論下去,他怕回頭陛下知道了,這些百姓法不責眾,他們這些不曾管束的朝臣卻會掉了腦袋。
梁德逑不著痕跡的朝著隔斷那邊看了一眼,一敲手中驚堂木,“砰”的一聲重響傳出之后,周圍站著的衙差也紛紛圍攏上前。
“肅靜!”
那些原本議論紛紛的百姓和圍觀之人都是到了堂肅穆氣氛,口中議論聲都是小了下來,漸漸變得安靜,所有人都是朝著堂上看去。
“本奉皇命嚴審豫國公方瑋庸勾結漕司,私通北狄,為謀私利命人謀害前都轉運司芮攀,以及漕司提舉溫志虎一案。”
梁德逑握著驚堂木時,神肅然,
“因事關外界流言,且涉及陛下清譽,為表公正,今日之案于堂前公審,允百姓旁觀,只審案期間管人等不得干預,堂外之人不得嘈雜,否則休怪本無!”
“來人,帶相關人等上堂。”
周圍寂靜無聲,衙差那邊很快便將芮麟、溫家一行人全數帶堂前,與此同時,豫國公也被人押著送堂前。
蘇錦沅抬眼看著豫國公,跟上一次在宮宴上見到的那個大權在握,容睿明淡定言笑的老人比起來,此時的豫國公卻要狼狽許多。
他上穿著囚服,雖然未帶鐐銬,卻也見在外的皮上生了很多瘡斑,腕間、面上更是消瘦很多。
數月牢獄生活,哪怕看管再好,他整個氣神也萎靡了下來。
顴骨突出,下顎消瘦,頭發整理過了,卻依舊難掩鬢間突生的蒼白,那麻麻的白發掩藏在束起的發之中,讓得他看上去比之數月之前,像是老了十來歲。
Advertisement
豫國公頂著周圍目進大堂時,看似依舊跟之前一樣鎮定,行走間背脊直毫無半懼意,可蘇錦沅卻依舊從他上看到了那掩藏在鎮靜之下的惶惶不安,也看到了遲暮之下早已不復的意氣。
豫國公,終究還是怕了。
芮麟等人上堂之后,便直接跪下。
豫國公卻立于堂前,有衙差上前押著他下跪時,他卻是直接掙開來,抬頭說道:“老夫乃是當朝國公,先帝親封輔政大臣。”
“陛下未曾褫奪位之前,你等無權讓老夫下跪。”
黎儉二人聞言都是看向梁德逑。
梁德逑神微冷,他自己算不得好人,也重權好利,可比起豫國公所做之事他卻已經算得上是絕世好人。
要是放在往日他自然不愿意招惹豫國公,可之前因為黃頡之事已經結仇,豫國公沒暗中害他,如今他更是知道豫國公沒了將來,又何必給他留臉面。
梁德逑半點不懼豫國公,只冷聲說道:“笑話,這里是刑部,不是你豫國公府。”
“天子犯法尚且與庶民同罪,更何況是你,本今日是代陛下審你,你如今不過是通敵叛國勾結北狄的罪人,又何來不跪之權。”
“來人,讓他跪下!”
站在后的衙差瞬間上前,一人按住豫國公的肩膀,一人朝著他腕上就是一腳,原本立于堂前的豫國公吃痛之下,被生生按著跪了下去。
“梁德逑!”
豫國公抬眼怒視,“你敢折辱老夫?!”
“本不過是按律行事。”
梁德逑只冷漠說了一句,就一敲驚堂木,扭頭看向芮麟:“芮麟,月余之前你敲登聞鼓,狀告豫國公方瑋庸謀害你父之事,陛下已經移刑部今日堂審。”
“你將所告之事當堂重述一次,不得有所瞞。”
Advertisement
“是,大人。”
芮麟跪于堂前,那好看至極的臉上滿是肅,當著眾人之面說道:
“我芮麟,乃是前都轉運使芮攀之子,我父親芮攀得陛下看重,得管督察漕運和各地鹽鐵之轉運之事。”
“我父親為清廉,也深皇恩一日不敢怠慢,于府衙之事從不懈怠,卻不想那漕司上下勾結,里早已腐爛至極。”
“有人想拉我父親與他們同流合污,我父親不愿,便為他們眼中釘中刺。”
他眸微紅,聲音也泛啞起來,
“一年多以前,我在亭山書院進學之時,突然收到我父親傳來書信,信中父親言辭驚懼,提及他查到漕司上下與朝中重臣勾結,走私漕運貪污賄的證據。”
“他說他側已現殺機,唯恐被人所害,父親將他收集的證據連帶書信一并送來書院。”
“我接信之后不過數日,我父親便突然自縊于府中,更留下所謂告罪書,言及他貪贓枉法之事,不待我趕回家中,我父親便已被朝中定罪,芮家上下更是被遣流放。”
芮麟像是想起其父之死,眼中通紅:
“我父親是被人所害,貪污之名更是被人冤枉,而害他之人便是當朝豫國公方瑋庸,我父留下書信之皆可為證。”
“豫國公早前數次想要收買我父親都被他拒絕,更數次暗示我父親于漕運之事上放寬界度,也被我父親視而不見。”
“他拉攏我父親不,便狠下殺手,更想將我芮家趕盡殺絕。”
梁德逑聽著芮麟說完之后,方才開口:“你既有證據在手,為何這麼長時間不曾京上告?”
“我怎能不想上告?若是能替我父親平反,我就是拼了命也在所不辭。”
Advertisement
芮麟面苦笑,紅著眼睛可憐說道,
“可他是當朝國公,權傾朝野,且我父親被害之后,他便一直派人追殺芮家之人,就連亭山書院也未曾放過。”
“我這一年多間幾次險死還生,若非芮家家仆拼死相救,我又早早察覺不對逃離書院,恐怕早就死在豫國公府的人手上。”
“我曾幾次試圖上京,可每次還沒靠近京城就被人發現,這次若非得知漕司之事暴,豫國公下獄,京中已無阻攔,我怕是也沒命能夠踏足京城,去敲那登聞鼓。”
“梁大人,我一平頭百姓,怎能與權貴抗衡?”
芮麟本就長得極好,杏眼鈍圓,容貌無辜,看著比之年歲還要稚氣一些。
他笑起來時極為討人喜歡,而想要取信于人時,也很容易便能讓人心生好,更遑論他此時微垂著眼,臉蒼白輕抿著,紅著眼睛像極了惶惶不安的小兔子。
那滿是苦地說著被人追殺逃命的艱辛,讓得堂前圍觀之人都是心生同。
平民和權貴,向來都是矛盾所在,芮麟將自己劃到了平頭百姓這一邊,頓時便讓得所有人都對仗勢欺人的豫國公心生惡。
“這豫國公實在可惡!”
“就是,人家不與他同流合污,就殺人滅口,還想將人孩子也趕盡殺絕,這種人當真該死。”
堂外罵聲陣陣。
豫國公則是目眥裂:“你這小兒,老夫何時命人殺你!”
他是讓人解決了芮攀,也讓人定了芮家的罪將其滿門發配,可卻不知道芮攀還有義子在亭山書院。
他要是早知道芮家還有這麼一個人,當初就會斬草除將人弄死,又怎會讓他活到現在,還讓他拿著芮攀留下的所謂證據,將他到如此地步?
芮麟聞言看著他:“你當然不認,就像是你害死我父親,偽造書冤害于他一樣,像你這種心狠歹毒之人,又怎會承認自己所做惡事。”
“我這麼長時間險死還生,就是要將你這惡人繩之于法,否則對不起我枉死的父親,對不起被你所害之人!”
“你……”
明明是信口雌黃,可所有人都信了眼前小兒之話。
向來巧舌如簧的豫國公這一刻竟會到百口莫辯之。
“砰!”
梁德逑重重一敲驚堂木,厲聲道:“本審案,未曾詢問你之前誰允你開口?”
命人按住豫國公后,他便冷道,
“若再有下次,休怪本命人掌。”
豫國公被重重按在地上,怒聲道:“梁德逑,此人分明是被人收買故意誣陷老夫,芮家本就無此人,你不明黑白,任其大放厥詞污蔑老夫,你就不怕陛下摘了你頂上烏紗!”
“本的烏紗用不著你來心,不過你既沒謀害芮攀,未曾命人滅口,又怎知芮家上下都有誰人?”梁德逑一針見。
豫國公瞳孔猛:“老夫與芮攀有舊……”
梁德逑冷然:“當初芮攀獲罪之時,可是國公爺一意力定了芮家上下之罪,更是你親自下令將芮家流放漠北,那時怎不見國公爺說你與芮家有舊?”
豫國公被堵得臉灰白,還沒開口反駁,就被梁德逑命人拿下,
“當堂喧嘩,辱及本,擾審案,來人,掌!”
“你敢……”
“本代陛下審案,有何不敢。”
梁德逑早厭惡豫國公至極,冷聲道,
“掌!”
衙中之人都是愣了一下,面對豫國公時,卻無人敢于上前,就在這時,原本站于一旁的衙差突然走到豫國公前,抬手就朝著他臉上就是幾掌。
隨即豫國公被直接按在了地上,那張臉都被得變了形。
“你……”
豫國公滿是狠地抬頭看著梁德逑,卻見上方那老狐貍不為所,而周圍之人看到豫國公慘狀時,都是不由臉微變,這梁大人是打算得罪死了豫國公。
豫國公今日若不定罪,怕會跟梁家不死不休。
霍見到豫國公慘狀,冷哼一聲道:“該!”
蕭云鑫也是目微暗,他蕭家上下的命,那數萬將士的枉死,如今只不過是討點利息而已,若非是知道接下來還有好戲。
他只恨不得能將豫國公拆骨去,一刀一刀地活剮了他。
蘇錦沅卻是微帶詫異的看了眼堂上的梁德逑,這位中書令向來老巨猾,為人也是圓至極,哪怕這段時間他跟豫國公生了嫌隙,如今也豫國公落魄。
照他以前,也不該這般不留面,當堂掌。
蘇錦沅微瞇著眼覺得有些不對勁,卻也沒開口說話,只是默默觀察著梁德逑和堂上眾人。
梁德逑命人掌之后,敲了驚堂木下了堂前嘩然,這才扭頭朝著溫思晴等人問話。
溫思晴恨極了豫國公,毫不猶豫就將豫國公和父親溫志虎多年勾結,貪污漕運巨利,威利江南員與其合謀之事通通都說了出來。
臉上消瘦很多,跪在原地泣道:
“我父親當年被他設計,一腳踩進貪腐漩渦難以,這些年他早已后悔,可卻被豫國公住把柄不得不為虎作倀。”
“漕運之上,這十數年間貪得銀錢便數之不盡。”
“其中六用于打點漕司上下,由漕司員和運軍分得,剩下之中兩疏通各地關系,收買江南員,另外兩則是了豫國公之手,為他立足朝堂,排除異己,替他自己鋪平朝中之路的踏腳石。”
“是豫國公經手之數,就足有千萬。”
“嘩——”
人群之中瞬間嘩然,滿是震驚的看著堂上豫國公,而旁觀薄膺等人,聽到溫思晴的話后也都是忍不住變。
哪怕早知道漕運貪腐嚴重,這些年落于豫國公之手錢財不,可他們也沒想到居然會有這麼多,要知道去歲臨川和西北賑災之時,攏共也不到兩百萬兩。
“千萬啊,那是多,我們一家四口二兩銀子就能富足一月。”
“我整年辛苦,也不過落得十余兩銀錢,夠糊口而已……”
普通百姓之家,二兩銀錢便能富足一月,尋常人家一整年下來也未必能落下幾兩碎銀子。
千萬之數……
在場這些人幾乎不敢去想,怕是壘銀山都沒這麼多銀子。
梁德逑也是驚住,敲著驚堂木下外間沸騰,沉聲道:“繼續說!”
溫思晴眼睛通紅,恨恨看著豫國公:
“我父親被豫國公鉗制,多年替他走私漕運謀取錢財,對他忠心耿耿,這次更是冒險替他走運宿鐵。”
“豫國公跟狄人勾結,販賣朝中,我父親不愿做此通敵叛國之事,他便拿著府中之人威脅。”
“父親無奈之下只能答應,可誰料宿鐵途徑仙卻出了問題,豫國公貪心不足,想要私吞所有宿鐵所得利益,不愿將這批東西得來的錢財分于旁人,竟是命府中暗衛冒充賊人。”
“他強奪宿鐵,害死我父親,又將此事嫁禍給剛好在南地的謝大人。”
“那一夜若非謝大人相救,我和妹妹恐怕也死在了豫國公派去仙的那些暗衛手中,我父親恨極豫國公過河拆橋,卸磨殺驢,臨死之前將他與豫國公這麼多年走私漕運,謀害朝臣,勾結朝中之人貪腐的證據全數給了我。”
“豫國公他該死!!”
豫國公聽著溫思晴滿是恨意的說著與他有關之事,聽著周圍那些喧鬧之言,只覺得心頭泣。
他赤紅著眼想罵溫思晴是蠢貨,想說他從未曾下令殺過溫志虎……
猜你喜歡
-
完結296 章

寵後之路
上輩子傅容是肅王小妾,專房獨寵,可惜肅王短命,她也在另覓新歡時重生了.傅容樂壞了,重生好啊,這回定要挑最好的男人嫁掉.誰料肅王突然纏了上來,動手動腳就算了,還想娶她當王妃?傅容真心不想嫁,她不怕他白日高冷晚上…,可她不想當寡婦啊
89.5萬字8.18 88574 -
完結106 章
被太子搶婚之后
明珠是家中不受寵愛的庶女。 一朝入了太子殿下的眼。 便被送到了他的別院,成了他的外室。 四五年被鎖在小院里不見天日。 直到有一天。 太子殿下要娶親,毫不猶豫賜她一杯毒酒。 明珠才知道太子殿下并沒有那麼喜歡她。 重生之后。 明珠一心只想逃離冷酷無情的太子殿下。 男人嫌她身份低不能娶她,她說好。 男人見她乖巧懂事,對她多了幾分憐愛,說:“我會照顧你一輩子。” 明珠表面上假裝很感動,結果等到時機一成熟 ,肚子里揣著崽立馬跑了。 人跑了之后,太子殿下才深刻體會到后悔這兩個字是怎麼寫的。
32.4萬字8 93744 -
完結319 章

妃常彪悍:腹黑邪王寵入骨
她是二十一世紀最頂尖的金牌特工。 一朝穿越,她竟穿越成了東嶽國貌醜無鹽又癡傻懦弱的五公主。 他是異國翻手覆手便可逆轉乾坤的攝政王。 絕色傾城,嗜血殘忍。 初見,她被渣男未婚夫算計,意外撞見了重傷不能動彈的他,對他上下其手。 看著她那副無恥又囂張至極的模樣,某妖孽惡狠狠地磨了磨後槽牙,暗暗發誓,有生之年,定要將她找出來,挫骨揚灰,碎屍萬段! …
52萬字8.18 80368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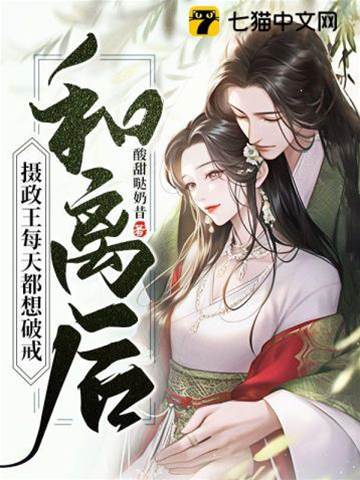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345 -
完結242 章

教不乖,佞臣替人養妹被逼瘋
【傳統古言 廢殺帝王權極一時假太監 寄人籬下小可憐 倆人八百個心眼子】少年將軍是廝殺在外的狼,窩裏藏著隻白白軟軟的小兔妹妹,引人垂涎。將軍一朝戰死沙場,輕躁薄行的權貴們掀了兔子窩,不等嚐一口,半路被內廠總督謝龕劫了人。謝龕其人,陰鬱嗜殺,誰在他跟前都要沐浴一番他看狗一樣的眼神。小兔落入他的口,這輩子算是完……完……嗯?等等,這兔子怎麽越養越圓潤了?反倒是權貴們的小團體漸漸死的死,瘋的瘋,當初圍獵小兔的鬣狗,如今成了被捕獵的對象。祁桑伏枕而臥,摸了摸尚未顯孕的小腹。為了給兄長複仇,她忍辱負重,被謝龕這狗太監占盡了便宜,如今事得圓滿,是時候給他甩掉了。跑路一半,被謝龕騎馬不緊不慢地追上,如鬼如魅如毒蛇,纏著、絞著。“跑。”他說:“本督看著你跑,日落之前跑不過這座山頭,本督打斷你的腿!”
42.7萬字8.18 153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