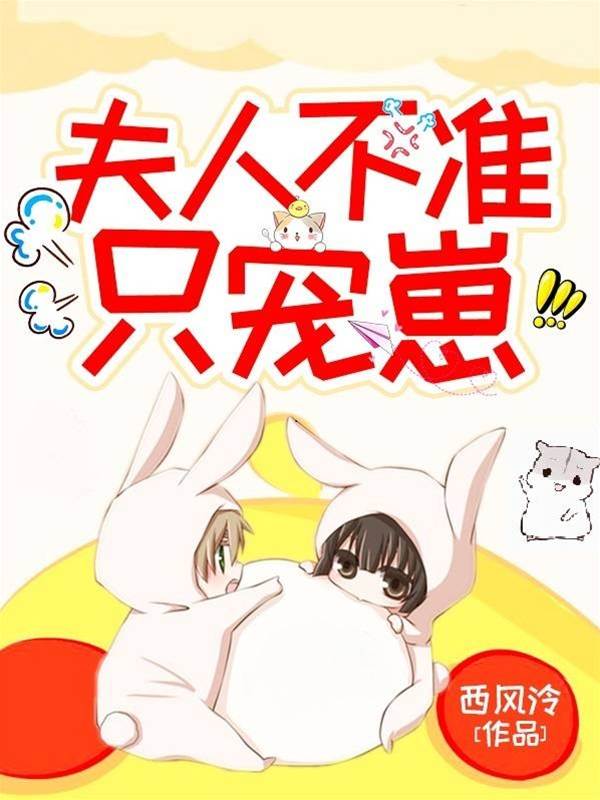《你看起來很好親》 第 1 章
初秋,荊市。
列車即將進站,顧桉倚著車窗打瞌睡,冷不丁被手機鈴聲吵醒,廣播同時響起。
“各位旅客,列車即將到達荊市車站,請在荊市車站下車的旅客準備好自己的行李下車。”
顧桉坐直眼睛。眼角偏圓,瞳仁黑亮剔,像隻誤闖人間的小鹿,迷迷瞪瞪,純良無害。
接起電話,眼睛往窗外看過去:“哥哥,我到車站啦!”
明明幾個小時前還在江南水鄉,幾個小時後就到這座北方城市,聽說四季分明,冬天有雪,氣候幹燥,沒有連綿雨季。
幾個月前,親哥顧楨工作調,從西南邊境調到荊市刑偵支隊,在這座城市安了家。
父母離異,兄妹倆一個跟著父親一個跟著母親,而現在顧楨一切穩定下來,第一件事就是把接到邊讀高中。
“我這邊有個案子暫時不開,地址發給你,自己打車,不要心疼錢。”
顧桉從行李架上取行李,隨著人往外走,忍不住笑出小虎牙,“你放心吧,我自己也可以的!”
-
荊市公安局,一樓,走廊盡頭。
電話那邊老人語氣和,“之前,你一消失就是好幾年,家裏整天提心吊膽,現在工作穩定了,是不是應該考慮一下終大事了?”
“你爺爺給你定過婚約,之前你在外地工作,就沒跟你提過,現在跟你說說,有個心理準備……”
“過幾年等人小姑娘再大點兒,咱就把婚訂了怎麽樣?”
“,請您取消婚約。”接電話的男人長鶴立,一警服冷淡肅穆,聲音很好聽,隻是眼睫半垂,神態不馴。
電話那邊頓了頓,繼續循循善:“聽說小姑娘跟個小瓷娃娃似的,特別可,說不定你一見到人家就喜歡了呢?”
Advertisement
江硯一臉總結案的波瀾不驚,“沒有這種可能。”
“你看看你呀,現在也老大不小了,老李上個月都抱第二個重孫子了……”
過了十多分鍾,電話那邊才掛斷。
手機屏幕暗下去,江硯解鎖,點開同事顧楨對話框。
兩人警校同學,過命的。
【江硯:你家還有客房嗎】
【江硯:最近不想住家裏】
【顧楨:閣樓留出來,其他房間任選!】
就在這時,帶著濃重哭腔的聲音從後傳來:“警,我要、要報案!”
孩哭得上氣不接下氣,說話斷斷續續沒有邏輯,在警安下緒才慢慢平靜。抬頭,坐在對麵的男警察看過來。
他頭發很短,五深刻,線平直,過分英俊又冷又酷的一張臉。隻是睫長且,當他抿,角竟然浮現一點很淺的梨渦。
看得呆了,直到他劍眉微揚,才紅著臉開口:“我今天在荊市火車站,遇到了人販子……”
大學開學,報案人今天從家裏坐高鐵來。出站時被老太太搭訕,在意識到不對勁兒的時候,老太太同夥中年男子圍上來,說報案人是他媳婦兒,怎麽跑出來這麽多天不回家。
路過行人圍過來,聽到他們這樣說,分分鍾腦補狗八點檔家庭倫理大戲,誰也不想摻和別人家事。
“就在他們要把我拖到麵包車上的時候,我砸了路邊攤主的手機,這才,這才引起大家注意……”
報案人做完筆錄,徘徊大廳門口一直沒有離開,轉就見剛才的冷麵警換了便裝,簡單黑外套黑長,雙手抄在兜下樓。
瘦高白皙,肩背直,不穿警服簡直像個二十出頭的警校生,一年氣毫不違和。
Advertisement
“江警,能加個微信嗎?”
孩臉頰微微紅,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報案還能遇到這麽極品一帥哥,幹的是刑偵長得卻像個白麵書生,這麽被他看一眼,不知道要回去牽腸掛肚多久……
江硯垂眸,盯著他睫出神,呆呆舉著二維碼臉頰泛紅,“就、就是有線索的話,可以聯係您……”
“有事可以給我打電話。”
生眼中滿是驚喜。
“110。”江硯頷首,錯而過。
黑SUV開出公安局大院,刑偵支隊的小夥子們百忙之中湊堆,八卦之魂熊熊燃燒。
“江硯,還有那個一起來的顧楨,到底是什麽背景?”
“空降刑偵支隊不說,當時還是省廳特意打的招呼……”
“據說這哥們兒前幾年在西南邊境毒一線,前幾年部裏督辦的711驚天大案聽說過沒?我猜是上頭的保護政策,把大功臣塞到咱這兒。”
“就像有些人藍襯穿到老一輩子都混不到白襯,也有些人,警校剛畢業的前三年,就刷出了別人一輩子刷不出來的履曆……”
-
火車站南街,顧桉察覺自己走錯方向,行李箱立在邊,重新加載地圖查看路線。
從側麵看過去,臉頰的滿是膠原蛋白,加上背帶和卡通T,完全就是個萌可欺的中學生。
“小姑娘,自己一個人呀?”老婦人笑瞇瞇湊過來,一副拉家常的樣子,“是要打算去哪兒?”
顧桉手機信號不好,看著屏幕皺眉,“洲際佳苑。”
“聽口音不是本地人吧?也去那兒,”顧桉轉,直接被握住手腕,“一起呀,拚車還便宜呢……”
地圖緩衝出來,車站街的公車可以直達,顧桉彎起角,“不用啦,我去前麵坐公車就好。”
Advertisement
聽這樣說,剛才還笑瞇瞇一臉慈祥的老婦人瞬間變臉,皺紋恐怖堆積在滿是橫的臉頰,想要掙開手,老婦人卻攥得更,手背被指甲劃出一道紅痕。
幾道悶雷之後,天瞬間暗下來。
車站南街路人稀,行匆匆,就怕下個瞬間落下大雨。
“請你放開我……”冷意順著孔擴散,顧桉脊背發涼,掙開婦人的手要走,罵罵咧咧的男聲在頭頂響起:
“小小年紀不學好,從家裏了錢出來玩?你還有沒有良心?”
胖的禿頂男人攔在麵前,劣質煙草味道猛然近,“有什麽事兒回家說,媽,別在這兒跟廢話。”
“我不認識你們,請你們鬆手……”
行李箱倒地發出悶響,顧桉被人拖拽拉扯,極度恐懼讓腳發,心髒快要撞破腔,原本糯的聲音帶了哭腔,引得路人頻頻回頭。
老婦人立刻換了一副抹眼淚的可憐相,“我家孩子了錢出來玩,被我們遇到還不服管教,這養孩子真是罪過啊!罪過!”
馬路對麵停著黑麵包車,車門大開,如同惡魔張開盆大口,下個瞬間就要將吞食腹。
華燈初上,綿雨滴落下,周遭霧蒙蒙。
路上行人稀,黃燈幾秒之後變了紅燈,像是電影裏的畫麵。而這時抬眼,看見路對麵的年輕男人。
他沒打傘,瘦高,很白,眉眼濃重如水墨,黑衝鋒領口抵著下顎。
視線驀地對上,綠燈亮,他長一邁,往這邊走來。心跳和他腳步聲重疊一起,每一幀畫麵都像是死裏逃生的慢作。
而過的瞬間,剛才死死鉗製著手腕的手驀地鬆開。
人販子麵容扭曲手腕被反手擰在後,狗急跳牆從夾克兜拿出什麽,男人直接在他膝窩狠踹一腳直接將人摁在地上。
Advertisement
他側臉清俊,鼻梁秀如劍刃。
漆黑眉眼充滿冰冷迫,額前碎發已經被雨打。
顧桉手止不住發抖,強定心神撥出的110報警電話剛剛接聽,對麵的聲音親切:“您好,荊州市報警中心為您服務……”
人販子的臉因為痛苦扭曲,惡狠狠看向時更顯猙獰,大腦經曆過強烈恐懼徹底宕機,顧桉裏字詞毫無邏輯連不句子:“我、我這兒,人販子……車站南街……”
看見什麽,顧桉眼睛睜大,徹底失語。
泛著冷調金屬澤的手銬,幹脆利落鎖在人販子手腕,與此同時,聽見他的聲音,低沉好聽的聲線,帶著清晰冷意。
“警察。”
-
荊市公安局,顧桉做完筆錄,對麵警察遞過紙筆:“如果確認無誤,請簽字。”
顧桉接過來,乖得像個一年級小朋友,一筆一畫寫下自己名字,手指關節因為用力泛白,對麵警還說了些什麽,大腦卻空白一片。
“小姑娘,你可以走了,以後可得長個心眼兒。”
顧桉站起,如果不是正好遇見路過的警察,現在又會是怎樣的境?
冷意從骨頭兒裏滲出,聲音小小的、還有些抖:“請問剛才那位警呢?”
“哦,你說江硯啊?忙去了吧。”
還沒有和他說聲謝謝呢……
“那您方便給我個聯係方式嗎?”
又是一個被衝昏頭腦的?
當初江硯職,荊市公安係統就跟著了三,這哥們兒過往清白履曆神、省廳特意打過招呼不說,偏偏人家還生了一張能吊打娛樂圈小生的冰山臉。
調來荊市這短短幾個月,追過他的包括但不限於家裏有礦的富二代、係統部公認警花、省廳領導大舅子家的外甥,以及人民群眾熱心介紹的幾十個適齡青年……
然而時至今日無一近的了,行走的製冷機一個,傳言冷淡。
“這種暴躁小哥哥,就隻有臉好看而已。”警察小哥有些於心不忍地看一眼,“你知道今天有小姑娘問他要電話,他怎麽說的嗎。”
顧桉懵懂,乖巧搖頭。
“他說,可以打妖妖靈。”
顧桉笑得眼睛彎彎,小虎牙冒出可的尖兒:“那麻煩您替我說聲謝謝呀!”
走出大廳路過宣傳欄,看到什麽,驀然停住腳步。
宣傳欄裏那張冷淡的寸照,和親哥顧楨的照片並列。
照片中的人一警察常服,英俊拔,五線條冷,偏偏抿起的角一側有一點淺淺的梨渦,而眉宇幹淨,直直看過來,讓人無端想起暴雨洗過的湛湛青空。
右下角黑宋備注:刑偵支隊,江硯。
猜你喜歡
-
完結143 章

重生之大佬的復仇嬌妻
前世,她受人蠱惑,為了所謂的愛情,拋棄自己的金主,最后身敗名裂,慘死在家里。 重生后,她只想抱著金主大大的大腿,哪里也不想去。可后來發現,金主抱著抱著,好像不一樣,她有點慌,現在放手還來得及嗎? 某天,金主把人圈在懷里,眸光微暗,咬牙切齒說“叫我叔叔?嗯?” 她從善如流,搖頭解釋,但他不聽,把人狠狠折騰一番。第二天,氣急敗壞的她收拾東西,帶著球,離家出走。
34.1萬字5 41505 -
完結968 章

總裁我不要辦公室戀情
一場奇葩的面試,她獲得了雙重身份,工作日她是朝五晚九忙到腳打後腦勺的房產部女售樓,休息日她是披荊斬棘幫上司的生活女特助。 他們說好只談交易不談感情,可突然有一天,他卻對她做了出格的事……「商總,你越線了」 「這是公平交易,你用了我的東西,我也用了你的」
255萬字8 19705 -
完結10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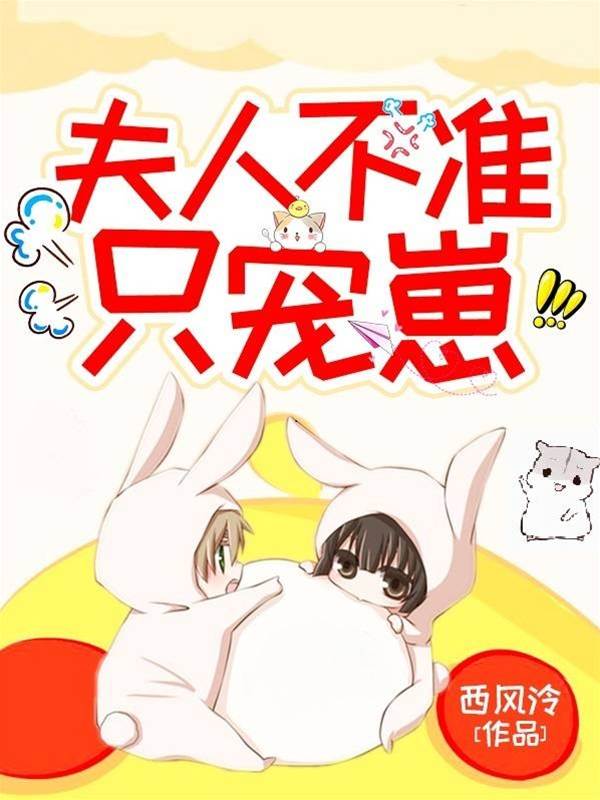
夫人不準只寵崽
南悠悠為了給母親治病為楚氏集團總裁楚寒高價產子,期間始終被蒙住眼睛,未見楚寒模樣,而楚寒卻記得她的臉,南悠悠順利產下一對龍鳳胎,還未見面就被楚家接走。
24.6萬字8 7222 -
完結389 章

炙吻
今年18歲的許芳菲,父親早逝,家中只一個母親一個外公,一家三口住喜旺街9號。 喜旺街徒有其名,是凌城出了名的貧民窟。 許母開了個紙錢鋪養活一家,許芳菲白天上學,晚上回家幫母親的忙。 日子清貧安穩,無波無瀾。 後來,樓下搬來了一個年輕人,高大英俊,眉目間有一種凌厲的冷漠不羈和刺骨荒寒。男人經常早出晚歸,一身傷。 故事在這天開始。 * 又一次相見,是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原,雄鷹掠過碧藍蒼穹,掠過皚皚白雪。 許芳菲軍校畢業,受命進入無人區,爲正執行絕密行動的狼牙特種部隊提供技術支援。 來接她的是此次行動的最高指揮官。 對方一身筆挺如畫的軍裝,冷峻面容在漫山大雪的映襯下,顯出幾分凜冽的散漫。 看他僅一眼,許芳菲便耳根泛紅,悶悶地別過頭去。 同行同事見狀好奇:“你和鄭隊以前認識?” 許芳菲心慌意亂,腦袋搖成撥浪鼓,支吾:“不。不太熟。” 當晚,她抱着牙刷臉盆去洗漱。 走出營房沒兩步,讓人一把拽過來給摁牆上。 四周黑乎乎一片,許芳菲心跳如雷。 “不熟?”低沉嗓音在耳畔響起,輕描淡寫兩個字,聽不出喜怒。 “……” “你十八歲那會兒我執行任務,拼死拼活拿命護着你,你上軍校之後我當你教導員,手把手教你拼組槍支,肉貼肉教你打靶格鬥,上個月我走之前吊我脖子上撒嬌賣萌不肯撒手。不太熟?“ “……” 鄭西野涼薄又自嘲地勾起脣,盯着她緋紅嬌俏的小臉,咬着牙擠出最後一句:“小崽子,可以啊。長大了,翅膀硬了。吵個架連老公都不認了。” 許芳菲:“……”
62.8萬字8.18 159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