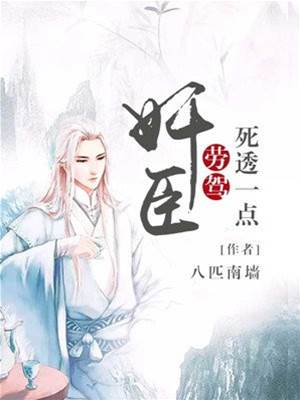《我同夫君琴瑟和鳴》 第145章 紅綾渡江(中)
五、
那次的戰況非常慘烈,傅玨帶著人遭了敵人埋伏,被圍困在蒼茫的亞娜若山谷中。而江遠波守在山谷的另一頭,遲遲未等到匯合的信號。
山谷地形錯綜復雜,有終年不散的瘴氣云霧,毒蟲猛日夜徘徊,營地氣氛沉重,所有人都猜測這次兇多吉。
然而第七日,有隆隆的馬蹄從巨谷傳出,由遠及近,兵士們奔走呼號:“都督回來了!都督回來了!”
傅玨真的回來了,坐在馬上,脊背得筆直,披風上沾了點,笑容有些疲憊。
江遠波從人群中走出,他毫不意外傅玨能從那樣的重圍中殺出,面對致命困境,他們擁有如出一轍的漠然從容。
他上前迎接攙扶,傅玨卻擺手說不必,趁著主帥歸來,軍心激的時刻,站在高臺上,沉聲宣告了此次戰役結果。
我軍傷亡五——敵軍全軍覆沒。
眾人嘩然,本就是敵暗我明、敵眾我寡的艱難爭斗,竟能力挽狂瀾到這等地步!一時間呼喝聲、吶喊聲震天地,在群山之中久久回。
討鄭賊,興煃室,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口號響徹云霄,過了很久才平息。江遠波凝著日下那個傲然而立的影,心中微微一嗤。
果然,人散后的軍帳,鮮打布巾,熱水送走一盆又一盆。
撕拉一聲,是江遠波在用燒灼到滾燙的金刀割下陳舊潰爛的傷口,他作準而快,指尖起落毫不猶豫,像在割一塊無生命的樹皮。
傷口的主人面很白,但眉頭半點也沒皺,側過頭看著被扔到盤中的腐,面上沒有半之前的慷慨激昂。
只淡淡說了聲:“弄干凈些。”
好像刀尖此時沒有劃在自己上。
Advertisement
江遠波面無表道:“大人晚來半刻鐘,這條手臂便保不住了。”
傅玨神平靜:“我計劃乘勝追擊,最遲半個月就又有仗要打,一條手換得振軍心,不虧。”
江遠波不意外,他早料到這般想法,當下作更快,只聽一聲,一烏黑的霧噴灑而出,他一翻紗布將其裹住,道了聲:“好了。”
傅玨方才閉上的眼緩緩睜開,額頭浸了汗,忽然說:“這次的確兇險。”
江遠波站起,開始清洗皿,聞言輕輕頷首:“剛剛的創口帶了毒,是某種霧瘴之地生的蜈蚣——您深巨谷腹地了?”
“是的,差點回不來,但多虧了一個人。”
“那個這次被您帶回來的人?”
“你已經見過了?”
“鬧出的靜可不小。”
傅玨難得地笑了一下,這是一個下意識的,不因為任何目的笑。
“住在山里,日子并不好過,你知道西南大山中的人怎麼對待奴隸——”說,“總之,救了我們,所以我決定帶走。”
江遠波將最后一柄刮刀收皮袋里:“但據鄙人了解,知恩圖報不是您的作風。”
傅玨翻看著手中堪輿,頭也不抬:“自然。”
既然如此,一個孤,能給帶來多大好?
這很快便能知道。
江遠波傾告退,路過兵帳的時候,聽到里面傳來吵嚷。
有人揮舞著木大:“抓住那個瘋子!搶了我的東西!”
又是噼里啪啦一頓響,江遠波略微駐足,接著掀帳往走,眾人一看見他,皆恭敬俯,口稱先生。
也有人置若罔聞,還在地上翻滾著,扭打撕扯旁人的頭發。
那是一個黑黃干瘦的,衫襤褸,上沾了黃泥,顯得更加污濁不堪。氣吁吁,枯瘦的手臂竟力大無窮,把七尺高的漢子在下,一下一下地往對方臉上砸拳頭。
Advertisement
一時間無人敢上前拉架,大家都在看軍師的臉,等待他發號施令。
江遠波卻一不,他靜靜地看著那拳頭高舉又下落,男人的表從咬牙切齒到苦不堪言。
他招來一人,淡聲問:“發生了何事?”
士兵囁喏道:“回先生,這的說的饅頭被了,不依不饒地到追打,搶別人的吃食說是的……”
江遠波頷首,他看見視線中心的終于劈手奪下男人懷中的馕餅,宛若保護著什麼珍寶,抱著餅起,跌跌撞撞地進角落里。
雜擋了視線,讓江遠波看不真切,肩膀在微微地,他以為那是在發抖,走近了幾步,才看清在大口吞咽。
江遠波等吃完才問:“你憑什麼說這餅是你的?”
聽懂了這一句,抬起頭惡狠狠地說:“那上面有我咬過的缺口!”
的眼睛在蓬發的間隙,亮而利地映過來,像凍雪淬洗過的天空。
江遠波看了一眼,就轉走了,他走之前搖了搖手,示意此事作罷。
軍師有令,眾人不得不從,皆作鳥散。唯有慢吞吞爬起來,抓住邊最近的一個兵士,問:“那個人呢?”
兵士避之不及:“那個人?”
“那個姓傅的,長得很高的人。”
“你竟敢——算了,你找做什麼?”
“我要見,答應了我一件事。”
“傅大人豈是你想見就能見!給我撒手——”
六、
江遠波第二次見到那個,覺得上有了點變化。
戾氣和兇狠,好像收斂了很多,頭發和軍中其他兵一樣,都扎起來束在腦后,出黑白分明的一雙眼。衫也穿得齊整,至袖口沒沾著泥。
規規矩矩地立在傅玨后,像個侍從,抑或是守衛。
Advertisement
傅玨對說:“這位是軍師,軍營中最有學問的人,今天請他來為你取個漢名,你可愿意?”
的表竟可以用乖巧形容:“可以。”
傅玨溫和地笑了下:“要說愿意。”
力點頭:“愿意!”
江遠波默默看著這一幕,過了會兒才開口:“你原本什麼?”
吐出一串低沉鼻音:“晃泉阿骨朵。”
“漢人中沒有姓晃的,給你改做姓黃,”頓了頓,江遠波又說,“至于名——”
手起筆落,剛勁有力的一個正楷字,落在宣紙之上。
長脖子來看,艱難念出:“白——完?黃白完?”
傅玨淡笑道:“這是一個字,念作皖,寓意為潔白,完,是一個寓意很好的字。”
突然懂得了禮數,沖著江遠波深鞠一躬,繼而咧開,出滿口雪白的牙齒:“多謝先生賜名!”
捧著紙張高高興興地去了,江遠波收回視線,落在上首的傅玨上:“大人眼很好。”
“哦?”
“的確很不錯。”
“說來聽聽。”
“其一,底子不錯。屬下之前在軍營里見過一次,當時骨角度有異,分明有折損,卻能忍痛和對手扭打許久,這份忍耐力算是有。更別說,今日見,已經是恢復如初了。”
“接著講。”
“其二,手絕佳。屬下早聽聞亞娜惹山中有民族世代聚集在峭壁之上,靠采藥和捕捉毒蟲為生,族人個個矯健凌厲,能踏云追霧,看來,是此族出。”
“你說對了,祖上是這一民族,不過被大寨捉去當了奴隸。”
“其三……便是這份心。”
江遠波的話戛然而止,沒有后文,但傅玨已經聽懂了未盡之意。
Advertisement
執起一枚棋子,淡漠道:“我救下的時候,幾乎被主人折磨而死,帶走的時候,許諾要給吃不完的食,不盡的自由,再也不會被人無故毆打辱罵。”
“然后——我把帶回來,晾了十天。”
“這十天,不聞不問,來請見都拒絕,也不向旁人吩咐如何善待,把徹底忘在兵帳里。最后我再見的時候,已經等了我很久。”
江遠波落下一子,他能夠想通這是出于什麼原因。
若僅僅只是威利,傅玨最多得到一個良將,若將其好生招待,傅玨會得到一個忠將。
若在許諾無數后漠然之,在其沮喪懷疑之時再出現,加之更甚萬倍的關懷。那傅玨會擁有一個足夠為肝腦涂地的死士。
雖然現在遠遠不到出生死的地步,但江遠波知道,這事一定會。
在他跟隨傅玨的這些時日里,還沒見沒做過什麼事。
傅玨需要一個背景干凈,心單純,可以死心塌地的人。在需要的人面前,這個年輕的野心家可以裝任何一副模樣。
說的每一句話,臉上每一個表,都是經過了千萬次思量才呈現出來的,恰到好的真誠。
為了這份真誠,花上的工夫不能不算不真誠。
恐怕只有在同類江遠波面前,這位前途無量的都督才會懶得偽裝。
江遠波深深俯:“恭賀大人,又添良才。”
傅玨一拂棋盤,忽然問:“你可否會制毒?”
“會,但并不算妙。”
“若給你兩年時間,潛心研究一種毒,這一種能否做到妙?”
“能。”
“那便從今天開始罷,記住,你會醫的事,除了我,不要向任何人。”
“屬下明白。”
七、
潔白,完。
這個字的寓意的確很好,無論如何說明都無可指摘,但江遠波不能否認,他在書寫下那些比劃的時候,心中只有嘲諷。
和一點淡淡的可憐。
面黃瘦,蓬頭垢面,哪里來的潔白,哪里來的完。
他看步傅玨的圈套,以為自己得到了從來沒得到過的溫暖庇護。屋及烏,敬傅玨,也激軍師初見那日在帳中給解圍(即使本意不是如此)。稚懵懂,看他獨來獨往,以為他也被人排,不收歡迎。
黃皖在軍中學槍,一一刺,很快就從僵笨拙到流暢自如。每學一個新招,就在傅玨門口徘徊,想有機會耍給對方看。
這樣的機會屈指可數,畢竟戰事吃,作為一個地區的大都督,傅玨非常忙。于是那些新招,就被江遠波看了去。
猜你喜歡
-
完結273 章
惡女世子妃
她江寧音本來是二十一世紀的職業女性,事業纔剛剛起步就穿到了大夏國的同名同姓的瑜安郡主身上.他足智多謀,驚才絕豔,用兵如神,名動天下,更是天下衆女子傾慕的的肅北王世子.她無才無德,殺人放火,無惡不做.人人避之不及,更是無人敢娶的第一惡女.第一才女清高作死,那就讓你不作死就不會死.第一美女僞善,那就剝了你的美人皮.她是誰,她可是第一惡女.宗旨是把惡女本質發揚光大.無人敢娶正和她意.三國盛會,惡女驚豔天下,風華冠三國,人人上門求娶,更有聖旨逼婚.她爲拒婚,發帖肅北王府世子.貼上寫道:無通房,未納妾,不擡姨娘,終身一妻,君能應否?回帖:一生一世一雙人!
85.2萬字8 31846 -
完結147 章

朕的悍妃誰敢欺
穿越了?還是個沒親娘的灰姑娘。被賜婚?太子心有所屬,要一刀把她咔嚓掉?此時不逃更待何時。據說那個攝政王,睿智果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這樣的大腿不抱,除非是被驢踢腦子,所以:爺,您就收了我吧!不做王妃,做個妾,實在不行做丫頭,我也沒意見啊!(本文純屬虛構,請勿模仿。)
33.9萬字8 25282 -
完結3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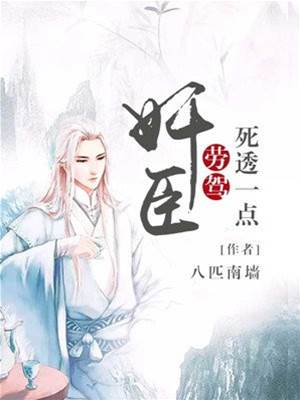
奸臣,勞駕死透一點
蘇問春五歲時撿回來一個臟兮兮的小乞丐,十年后小乞丐踩著蘇家步步高升。春風得意之際,蘇問春伏在他腳邊求他為蘇家討個公道,只得他兩個字:活該!后來蘇問春受盡酷刑著牙闖出一條血路終得平反。兩人尊卑顛倒,他一身囚衣坐在死牢,卻是一臉繾綣:“不是一直…
70.1萬字8 6083 -
完結505 章

織繡滿京華
繡娘穿越農家,一來就挨打,必須打回去; 帶領爹娘發家致富奔小康; 還有個青梅竹馬追求,同甘共苦,互相扶持,沒想到卻成了一匹黑馬; 一手抓事業一手抓愛情,夫妻雙雙譽滿京華。
93萬字8 478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