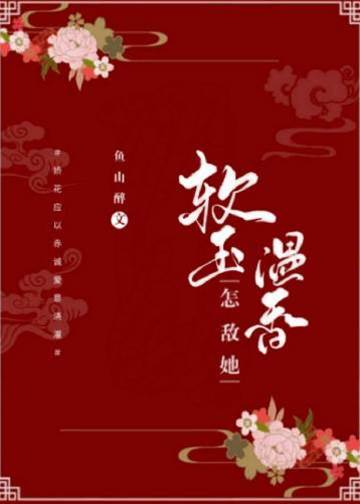《掌上嬌卿》 第105章 番外一
對于鎮北王府的下人來說, 王妃好像還是他們的夫人,但又好像不是。
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從歸燕堂的世子夫人直接變離北堂的王妃, 丫鬟小廝們一時還有些不適應。
畢竟從前府中沒有王妃, 世子夫人就是他們的主母,管事的都同打過道,丫鬟們也見慣了世子和夫人里調油,如今夫人換了個份, 雖然還是他們的主母, 卻了王爺的王妃。
不過在大部分人眼里, 王妃就是他們王爺娶回來照顧的姑娘,是故之。
沈老夫人年紀大了,孫和離,再嫁也未必能嫁得良人, 到如今還沒有歸宿, 而太皇太妃又催著王爺家,加之鎮北王府又因錯認世子對武定侯府有所虧欠,這不就一拍即合!
直到離北堂新婚夜一晚上了三回水,第三回的時候天都快亮了,接下來的幾晚, 最也是三回四回, 比從前世子爺搖鈴的次數還多, 相隔時間也更長, 底下人才都傻了眼。
“照顧故之,用得著水來照顧嗎?”
“你傻呀, 真若只是將王妃當做故之, 用得著娶進門嗎, 認作義豈不更為合適?”
“難道說……王爺其實是喜歡王妃?”
“當然,否則又豈會連外頭的風言風語都不顧,偏偏將從前的世子夫人娶回家。”
“王爺這三十幾年來,你見過他邊有一個子嗎?”
……
眾人說著說著,表到最后總會從面面相覷的震驚轉變為心照不宣的竊喜。
而離北堂的丫鬟比旁人又多了些墻角可以聽,倒也不是們想聽,只是這主屋里頭靜實在不小,就如昨夜,鈴鐺聲急而,-哀憐的嚶嚀聲在里面,人聽了都忍不住臉紅。
Advertisement
只有離北堂的管事季平知曉王爺如此蠻狠的緣由。
新婚那夜,王爺會完賓客回到院,對他吩咐了幾句招待事項,又似無意問了一句世子從前房的搖鈴次數,他謹慎地答了,王爺面上雖看不出什麼緒,但眸卻比黑夜還沉。
結合接下來的幾晚,季平就心領神會了。
王爺這是與世子爺暗暗較勁呢。
不過就說世子爺那板,和陵侯世子、國公府李二公子比比還算綽綽有余,在王爺面前本不夠看的,而且據季平觀察,世子爺頭兩年還行,后來放縱太過不知收斂,近兩年來已有力不從心之勢了。
可王爺年輕時深敵營可以幾天幾夜不眠不休,還不是像世子爺那般游戲花叢,那可是真刀實槍地上戰場,力遠非常人能及,如今也算是老當益壯了,三十多的人比之弱冠年郎有過之而無不及。
日上三竿,沈嫣塌塌地躺在床上,纖長的眼睫漉漉的,掛著兩顆秋般的淚珠,兩頰還像昨晚那般著一層薄薄的。
謝危樓已經起來了,到書房理了幾樁要務,出來時管家郭嘯手里拿著賬本來稟:“王爺,從前府上中饋也是王妃掌管,如今回來,您看是否將……”
謝危樓”嗯“了聲,沉片刻道:“過段時間吧,王妃子虛,讓養幾日再說。”
郭嘯立刻心領神會。
養幾日大概就是養到王爺復原職,至不會在白天折騰,到時候他再將府中事務轉夫人掌管。
謝危樓就讓他下去了。
回到寢屋外,兩個陪嫁丫鬟站在廊下提防地著他。
謝危樓走過去,“夫人還沒起?”
對外王妃,離北堂院的丫鬟都是習慣了夫人,云苓和松音對視一眼,躬道:“夫人昨夜眠,今晨才睡下,這會還未起。”
Advertisement
謝危樓想了想道:“讓膳房準備些清粥送來,不要太甜。”
云苓微微一頓,拱手下去了。
門口就剩下松音一人,膽子還不如云苓,面前這位氣勢又格外迫,威嚴之氣幾乎撲面而來,松音都不敢抬頭與他對視,無奈暗暗咬牙,讓到一邊。
謝危樓進了屋,小姑娘還睡著呢,乖的一團蜷著,如瀑的長發傾瀉下來,一截纖細白皙的后脖在外面。
他坐到床邊,出手,想要將埋在錦被里的小臉掰出來,可指尖才一耳垂,小姑娘就條件反般的一,立刻驚醒了,以為他還要來,耳尖登時紅了一片,雪頸上都起了一層栗。
“不你了,還不起?”
沈嫣渾還酸著,一點力氣都沒有,才不相信他的鬼話,自己往里挪窩,不想看他。
“你自己做的好事,還怪我起不來?”
綿綿的嗓音悶在被子里,聽得人指尖發。
謝危樓嗤笑了聲,撥開鬢邊的頭發:“我做什麼好事了,前日不是還放過你了?”
還說呢,新婚夜鬧得太厲害,第二日進宮都是抖的,被太皇太妃瞧了笑話,還囑咐他收斂些,臉面盡失,在太皇太妃面前頭都抬不起來。
若不是昨日回門要見祖母,他又豈會只區區兩回便放去睡,如今過了回門,這人又開始放肆起來。
謝危樓手過來,手掌在肩頭挲,“有沒有哪里不舒服,夫君給?”
沈嫣還閉著眼睛,抿了抿,頭埋得更低,不打算搭理他,“不要你。”
謝危樓笑了笑:“不喜歡?我還不夠疼你嗎?”
手指了后頸,姑娘家的雪太過細,和他掌心的糲對比鮮明,讓人不忍心用力。
Advertisement
“方才管家來稟事,我讓他退下了,這幾日都不會來煩你,待你適應好了,府上中饋還是由你打理,門路,不用現學。”
沈嫣反應了半天,才知他口中的“適應”,并非是適應府上的生活環境或是王妃的份,而是適應他的……頓時又又怒,想到他連著幾夜干的混賬事,沈嫣就想繞開他自己的那只手,無奈又沒什麼力氣。
腹中空空,小腹被他按的地方還發痛。
謝危樓說著話,手上作也沒停,卻也放得格外輕緩,目落在那微微凸-起的頸椎骨,立刻就讓他想起昨夜,從后頸到腰窩,沿著脊柱一節節吻下去的那種覺,眸暗下了幾分,低聲線,在耳畔道:“讓我親一親,好不好?”
哄般商量的語氣,指尖落在后脖的讓渾一僵,“你還要?我還得見人的。”
“不要,就抱抱你。”
聽著帶哭腔的聲音,終究還是沒舍得,畢竟比自己小這麼多,又這麼瘦,細腰在他掌中盈盈不堪一握。
其實他已經算收斂了,否則不會只是這樣。
謝危樓嘆口氣,大手探進錦被,將人攬到自己懷中來,聞著上淡淡的甜香,也是一種藉。
“這段時間,還有沒有夢到前世?”
帶著溫熱氣息的嗓音落在耳中,的覺,悶悶地說了句“沒有”。
過去不愉快的記憶在大婚之前好似戛然而止了一般,也許老天爺心疼,想讓往后的日子沒有苦,只剩甜。
“那就好。”謝危樓角微微上揚,親了親的小耳朵,懷中的人不安分地了,居然又挑起他一的火。
掌下的腰肢手細膩,得不可思議,謝危樓現在的呼吸幾乎要靠克制才能保持平靜。
Advertisement
沈嫣背靠著他實的口,雙臂亦被錮在他懷中,瞬間就掙扎不得了,彼此的心跳聲重疊,背后的軀越來越燙,“你別……”
話未落,屋門敲響。
云苓在外面道:“王爺,粥到了。”
謝危樓沉默地看著微敞的,轉頭看向門外,語調往下一沉,“進來。”
云苓戰戰兢兢端著托盤進來,一抬眼就看到自家姑娘面紅,可憐地窩在鎮北王懷里,除了心疼還是心疼。
謝危樓指了指床邊的案幾:“放下吧。”
云苓應了聲是,目瞥到那白皙鎖骨下的藹藹紅痕,趕忙移開視線,放下托盤后就退下了。
謝危樓拍了拍小姑娘后背:“吃點東西再休息。”
沈嫣聞到香味兒,肚子就了,無奈上使不上力,一手指頭都不想,懨懨地說:“不想吃。”
說完肚子不爭氣地“咕咕”一聲,沈嫣頓時紅了臉頰。
謝危樓垂眸笑了笑,手去腦袋:“不想吃還是想讓夫君喂你?”
他喂的次數可不,這幾次都是湯羹端到邊喂的,小姑娘沒良心,還同他發脾氣。
謝危樓逗:“說想要夫君喂,夫君就喂你吃,好不好?”
沈嫣說不出口,這個人太壞了!欺負不說,到這會還在戲弄。
謝危樓將碗端過來,銀匙一下下攪著,紅棗山藥的清香緩緩散發出來。
“真不吃?不吃的話,晚上可就連抓我的力氣都沒有了。”
“咕咕。”
回應他的又是一聲肚子。
被他鬧了一整夜,沈嫣這會早就得前后背了。
咬咬下,心不甘不愿地說了一句:“想要夫君喂。”
謝危樓靜靜看著笑,居然沒有靜,沈嫣又又惱,一轉,銀匙到,一枚甜甜的紅棗喂了進來,甜津津的味道溢滿了齒間。
沈嫣嚅著吃東西,圓圓的眼睛還瞪著他,每次都抿著,讓他手懸在空中舉一會才肯賞臉。
“乖一點,寶貝。”謝危樓輕笑著吹了吹銀匙里的粥,吹溫了再送到邊,真就像服侍兒似的哄著喝。
吃了半碗,沈嫣就躺下了。
謝危樓便放下碗,取來干凈的棉巾給拭。
“離我復原職還有十來日,趁這個時候帶你出去走走?”
沈嫣眼前一亮,“去哪?”
有好幾年沒有正經出門玩過了,一直都很羨慕江年的快活瀟灑。
謝危樓提議道:“去天水行宮可好?”
天水行宮在北直隸管轄范圍之,是太宗皇帝當年出行寓居之,山水秀麗,樹木蔥蘢,是騎狩、避暑、休憩、觀景的好地方,后來賞賜給了謝危樓,不似延芳淀、南海子那種世家子弟皆可進出的園囿,為謝危樓私有,多人想進進不去。
盡管這些年謝危樓不在京中,行宮也有專人打理,秋日風景甚佳。
沈嫣自然很高興,忙不迭地點點頭。
既是出去玩,他總該克制些了吧,否則像今日這樣,是連路都走不的,還能怎麼玩呢?
又眨了眨眼睛,扯扯他的角:“那我能不能……帶年年一起去?早就想去天水行宮看看了。”
謝危樓似笑非笑地看著:“你覺得能嗎?”
猜你喜歡
-
完結2366 章
隨身醫典:醫妃權傾天下
”伴隨著這聲清冷的帶著一絲不確定的聲音,蘇年有些艱難的睜開眼睛。
217.8萬字8.38 214424 -
連載1529 章

神醫狂妃乖乖受寵
醫學界頂級天才顧初暖穿越了,還悲催的中了隻有男人才能解的毒。為了保住狗命,她半路拉了一個重傷的美男解毒。“睡一覺而已,你又不虧。”她說得理直氣壯,卻把他氣得差點昏死。混蛋,他堂堂戰神,竟讓一個來曆不明的女人給染指了,最惱人的是,她還搖頭晃腦的點評,“技術太差,有待進步。”很好,這樁梁子他們結大了。一紙婚書,她跟他成了親。麵對戰神的步步緊逼,顧初暖暴怒,從此走上出牆之路,“滾你犢子的不近女色,我也是信了你的鬼,和離,必須和離。”“和離無效,你出牆一寸,我便挪牆一尺。”“……”男強女強,強強聯手,甜文寵文,歡
166.9萬字8 59945 -
完結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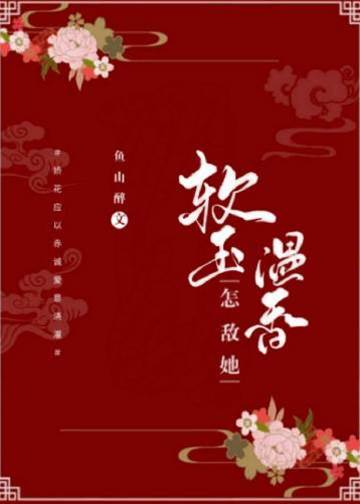
怎敵她軟玉溫香
提起喬沅,上京諸人無不羨慕她的好命。出生鐘鳴鼎食之家,才貌都是拔尖兒,嫁的男人是大霽最有權勢的侯爺,眼見一輩子都要在錦繡窩里打滾。喬沅也是這麼認為的,直到她做了個夢。夢里她被下降頭似的愛上了一個野男人,拋夫棄子,為他洗手作羹湯,結果還被拋棄…
21.9萬字8 11492 -
完結216 章

不夜墜玉
師蘿衣與錦鯉小師妹爭斗。 不甘心比了一輩子,敗了一輩子。青梅終究比不過天降,最后連她的竹馬未婚夫也不可救藥地愛上了小師妹。 破廟瀕死,無人殮骨。 就很氣啊! 她驟然想起,很久之前,自己也曾贏過一次:她不可描述了小師妹看得和眼珠子一樣的凡人兄長
33.5萬字8.33 90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