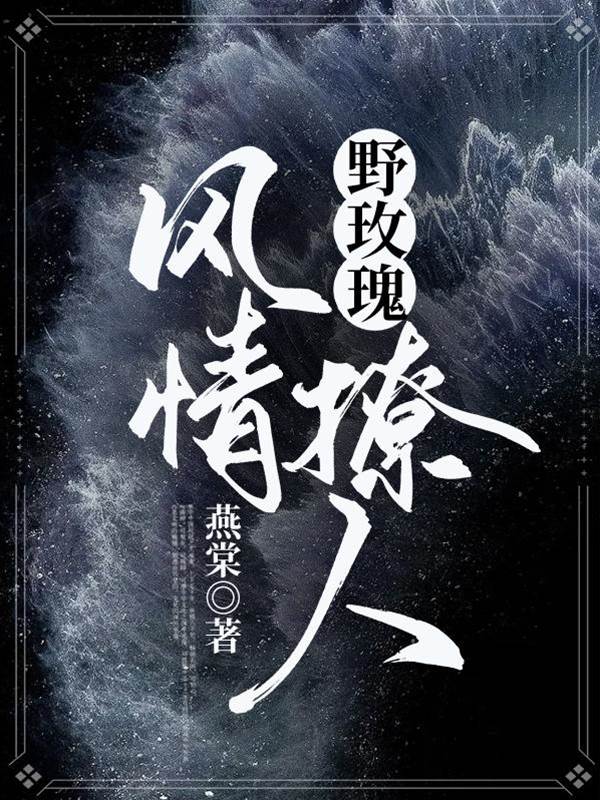《從群演開始(重生)》 第7章 季衛言
蘇向揚家洗了服,都在二樓連著蘇向揚臥室的臺晾,那里足還不用擔心下雨淋服。
蘇向揚讓季衛言去樓上晾服,自己則進了廚房。
大鐵鍋里的粥早就好了,這估計是他們回來前,他媽就已經煮好的,旁邊還有幾個熱騰騰的蛋餅,是面加水加蛋蔥花攪面糊之后在鍋里攤的,應該是他媽看到季衛言來了之后做的。
蘇向揚很小就會做飯,他媽要上班,他不搭理他,他就自己學著做飯,做多了就會了,只是廚藝不怎麼樣。
周英英買藥去了,蘇向揚見案板上有榨菜,就洗了切裝碗里,加一點味拌一拌,這是他們家夏天每天都吃的下粥菜。
拌好榨菜,他又用燃氣灶炒了五個蛋和一盤青菜,菜是從門前地里摘的,正鮮著。
蘇向揚有心做幾個好菜,但他們家今天沒買,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只能這麼著了。
剛將飯菜端上桌,蘇向揚就看到周英英回來了,帶回來一瓶從赤腳醫生那里買的紅藥水,還有用塑料袋裝的油炸花生和油炸蠶豆,這兩樣在他們村里的小賣部有散裝的賣,價格便宜,村里人常常買來加菜。
“小季,我們家也沒什麼吃的,你隨便吃點。”周英英不好意思地開口。
“已經很好了,謝謝阿姨。”季衛言道謝,一口蛋餅一口粥地吃,吃飯的樣子讓人看著賞心悅目的。
周英英從昨晚上一直忙到今天中午,雖然下午睡了四小時,卻還是不夠,跟蘇向揚說了一聲,讓蘇向揚給季衛言藥,就去休息了。
季衛言上的傷已經好些天了,當初雖然破了皮,但現在已經結痂。
不過大概是季衛言不太重視,有些地方化了膿,一點紅藥水也好。
Advertisement
蘇向揚就拿了藥給季衛言。
刺頭似的季衛言也不炸了,低聲道:“晚飯還有這藥的錢,你從我給的錢里扣,要是不夠了,我再給。”
“行。”蘇向揚一口答應,把紅藥水往季衛言背上抹。
他其實很想知道季衛言的爺爺為什麼要打季衛言,但他跟季衛言不,最終什麼都沒有問。
過藥,蘇向揚就去收拾樓上的房間。
他家樓上空房間很多,還有一張他爺爺生前睡的舊床。
床有點舊了,但并沒有壞,他大姨和表妹偶爾來家他住,睡的就是這張床。
蘇向揚的大姨結婚后好幾年沒孩子,后來好不容易有了個孩子,生孩子的時候還差點送了命,以后也不能繼續生了。
現在計劃生育,按理他大姨就生一個沒什麼問題,偏他那個大姨夫是個重男輕的,一心想要兒子。
因著這個緣故,他那個姨夫對他大姨很不好,偶爾喝了酒還會手,他大姨了委屈,就會回娘家。
又因為他舅媽脾氣不好,他大姨大部分時候,都會來他家住。
房間還算干凈,蘇向揚簡單打掃了一下,又在天井里洗了竹席給季衛言鋪上,還道:“我家的房子很一般,但到了冬天我可以借你被子蓋,在這里住下你絕對不虧。”
“嗯。”季衛言哼了一聲,現在是六月底,離天冷還有三個月,到時候,誰知道會怎麼樣?
蘇向揚心很好,他又拿了一床他媽廠里發的巾被給季衛言蓋,然后對季衛言道:“你要不要跟我去樓下坐坐?我跟你說說影視城的事。”
說影視城的事為什麼要去樓下?季衛言雖然不解,但沒有反對,跟著蘇向揚去了樓下堂屋。
然后他就見蘇向揚在點燃了一圈蚊香之后,開始踩紉機,用周英英做服裁下的邊角料自行車墊子。
Advertisement
季衛言震驚地看著蘇向揚。
蘇向揚笑著看季衛言:“你要學嗎?很簡單的。”踩紉機真的簡單的。
有些家長怕小孩子弄壞東西不讓孩子紉機,但他媽不這樣,他小時候對紉機好奇,他媽就教他踩,他自然也就學會了。
不過他只會用紉機來合布片,做服需要裁剪什麼的,那些他是不會的。
季衛言默默搖頭,一邊聽蘇向揚說影視城的事,一邊看蘇向揚坐墊。
蘇向揚沒花多久就好了墊子,又找來一些化纖棉花填充進去。化纖棉花是他們這里方言的法,蘇向揚覺得這東西應該就是聚酯纖維的填充棉,因為很蓬松的緣故,本地人一般用它來做枕頭,他媽在化纖廠工作,他家也有一些。
做完之后固定在自行車后座上,蘇向揚又問季衛言:“你還有什麼要問我的嗎?沒有的話就早點睡?”
一番折騰下來現在已經八點多了,十六歲的小孩還在長個子,應該早點睡。
他也應該早點睡。
上輩子他猝死,就是因為熬夜太多。
“沒有了。”季衛言道。蘇向揚剛才事無巨細跟他說了很多,他有種大開眼界的覺,暫時沒有別的想知道的事。
蘇向揚又看了看季衛言的頭,笑起來:“你明天可以跟我一起去王老板那里找活兒干,你這頭好的,有些古裝劇劇組,就喜歡頭群演……你之前那一頭黃發就不行了,基本上沒有劇組會要。”
季衛言:“……”
季衛言昨晚上聽到那些村民說已經報了警,怕警察來盤問自己,才會匆匆離開。
擔心家里人來抓他,覺得黃發有點顯眼,他今天早上還花三塊錢,去鎮上菜場附近專門給老頭老太理發的理發店刮了個頭。
Advertisement
沒想到歪打正著了好事兒。
兩人上樓睡覺的時候,季衛言突然問:“你就這麼把我帶到你家住,不怕我是個壞人?”蘇向揚都沒跟他要份證看看!
蘇向揚道:“你是個好人,我相信你。”
季衛言微愣。
蘇向揚跟著又道:“而I且我家這麼窮,你想在我家東西都不著什麼。”
季衛言不跟他說話,一腳四級臺階,大步走了。
蘇向揚見狀低聲道:“你小心點,我家這臺階沒有護欄……”他家這房子蓋到后面實在沒錢,樓梯就沒有刷沒有裝護欄。
他話沒說完,季衛言就已經沒影了。
最近天已經很熱了,不過客房那邊有個電扇,應該夠季衛言用的了。
至于空調……反正他家是沒有的。
蘇向揚跟季衛言說可以包水電,主要就是因為他們家沒有什麼電。洗機冰箱他家一概沒有,他媽早年買的黑白電視機也已經壞掉不能看了,平常用的電除了電燈電扇就只有一個電飯鍋。
他家的電費一直很,以前他住校他媽一個人在家,電費一個月五塊錢都不到。
現在已經零五年了,這幾年因為影視城的緣故,他們村的人多多掙了點錢,村里大部分人家,都是有彩電冰箱的,還會安上一個空調,夏天全家人一起用。
至于鎮上市里……蘇向揚記得他去市里同學家,人家家里什麼電都有,電腦都有兩個,跟十幾年后已經沒有太大區別。
當然生活條件比他家還差的也不,村里就有,影視城那些外地來打工的農民工,家里的日子就大多不好過。
蘇向揚想著上輩子的事,慢慢睡著了。
另一邊,季衛言躺在床上,有些恍惚。
Advertisement
他從小到大,除了前幾天住的破廟以外,從未住過這麼破的房子,睡過這麼舊的床。
但他前所未有地安心。
雖然蘇向揚一副錢的樣子,但他能覺到蘇向揚在照顧他。
這人估計是覺得他可憐。
可實際上他家很有錢,特別特別有錢,家里保姆司機一樣不缺,住著大別墅。
但那對他來說是個牢籠。
季家祖上是大豪商,是本地首富,但因為他爺爺的父親是個敗家子,以及時代原因,什麼都沒留下來。
甚至他爺爺他父親在某些年份,還過得很不好。
他父親聽多了他爺爺說的以前的種種,一心想要振興季家,也就在八十年代的時候下海經商,還大手筆地借錢盤下了一個食品廠。
可惜他爸就不是做生意的料,食品廠險些倒閉,最后是他媽看不下去,接手食品廠,才力挽狂瀾轉虧為盈。
他爸見狀,改行去做別的生意,然而又虧了。
如此虧了幾次,家里就不讓他爸去做生意了,他爸也放棄了做生意,轉而把注意力放到才兩歲的他上。
他爸覺得自己沒辦法恢復祖上榮,就想著靠他去恢復。
他當時還小,什麼也不懂,就只知道從早到晚,自己沒有一刻空閑。
五點就被起來背書,還要學鋼琴,學書法,學畫畫,學英語……一直到晚上九點,他才能睡覺。
甚至于他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什麼時候上廁所,都被嚴格規定,但凡他不吃的東西,他爸就天天做頓頓做,著他吃。
這也就算了,他發燒了不舒服了,都不能休息,哪怕嚎啕大哭都沒有任何作用,他父親只會在旁邊冷漠地看著他,覺得他太氣不能吃苦。
他父親甚至刻意讓他大冬天去游泳,大夏天去曬太,其名曰鍛煉他的意志力。
對了,為了避免他變敗家子,他父親還要求他自己洗服,讓他學做飯,全包家里的家務。
他總覺得不過氣來。
他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都已經認識大部分常用字,會一口流利的英語了。
也是因為上了小學,他意識到了不對。
別人的生活,不是這樣的!
他的同學可以看電視,可以跟小伙伴玩,可以吃自己想吃的東西,而他什麼都沒有。
他開始不服管教,反抗他的父親,然后就被斥責“不聽話”,就會挨打。
如果一般人,被打幾次,可能就被打服了,不敢反抗了,但他不是這樣的人。
他爸越是打他,他越是不服氣,越是想要反抗。
不過他那時候太小了,能力有限。他不聽話他爸就不給飯吃,他的一舉一還全在他爸的監視下,所以他最后不得不聽話。
當時他除了去學校以外,依然要接各種補課各種興趣班,在他父親的高下,他為了一個品學兼優的小學生,還跳了兩級。
但他每一天都過得很痛苦。
在他六年級的時候,他終于不了了,有一次他爸打他,他跟他爸對打。
那時候他才十歲,自然打不過他爸,他的反抗還讓他爸然大怒,找了子揍他。
他被打斷胳膊,進了醫院。
他躺在病床上,策劃著要離家出走,然后得知他爸在來醫院給他送飯的時候,出車禍死了。
他當時就懵了,放棄了離家出走的計劃。
他媽很忙很忙,基本不管他,兩人一個月見不上幾次,見上了也說不了幾句話。
現在他爸沒了,他理所當然的,被給爺爺照顧。
他爺爺恨他,覺得是因為他不服管教,他爸才會死。
不管他爸在別人眼里是怎麼樣的,在他爺爺眼里,那是一等一的好。他爸一直說他不聽話,他爺爺自然也這麼覺得,再加上覺得他害死了他爸,他爺爺很不喜歡他。
此外……他爺爺跟他爸一樣將他管得不風,季衛言覺得他爸會那樣,應該就是學的他爺爺。
他爸死了,他也不好,頭兩年是聽話的,但就算他聽話,他爺爺也從不滿足,只會讓他學更多,還時不時教訓他,想總辦法找他的茬。
他都考了年級第一了,他爺爺還能以他語文扣分多為理由讓他反省認錯寫檢討。
而他要是不認錯不寫檢討,就沒飯吃。
他不覺得自己有錯,自然不肯認,就常常挨。
他爺爺找茬當然不止在學習上找,生活中也一樣,他哪怕為自己辯解一句,都是不敬長輩,要去祖宗面前跪著,他要是不跪,那必然是挨打挨一條龍。
說來也好笑,他在頂尖的私立初中上學,有花了大價錢請的家庭教師給他補課,有豪車接送有保姆照顧,結果連飯都吃不飽,上也沒有毫零花錢。
怕他變敗家子,他爺爺一分錢都不給他。
要不是中午那頓是在學校吃的,他指不定要死。
這日子他實在過不下去,他又開始反抗。
有本事就打死他死他,反正他就是要跟他們對著干!
從初三開始,他上課睡覺考試一個字不寫。
他爺爺再打他的時候,他還會還手,會跑。
他已經長大了,想打他沒那麼容易。
不過當時他心里還是存著期的,他覺得等他上了高中,就可以擺家里。
要知道他的那些初中同學,有不高中會出國,再不濟高中也要住校。
他要是能離開那個讓他窒息的家,那真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但他失敗了。
他跳過級,十四歲那年參加中考。
雖然之前他考試的時候一個字不寫,但其實還是學了的,中考考得很好,考上了不錯的高中。
他以為他會開始新生活,結果他的績了他之前故意不考試,叛逆期不聽話的鐵證,又被打了一頓。他媽也覺得他太過分,專門跟家長對著干。
他高中想住校,但他爺爺不讓,理由是怕他在外面學壞,以后變本加厲。
他媽覺得有道理。
高中了,他依然過著完全沒有自由的生活,他試圖向他媽求救,但他媽覺得他是不聽話,才會被打。
如果他上課不睡覺考試好好考,犯了錯乖乖認錯,他爺爺又怎麼會打他?又怎麼會不給他飯吃?
他媽訓了他一頓,就又去忙工作了。
他怎麼想的,他想要什麼,從來沒人管。
他高中的時候,干脆不去學校了,他打架鬧事,他離家出走,他染頭發,他徹底不服管了。
可惜他家庭不普通,他總會被抓回去。
當時的他也已經明白,他沒有份證,就算離家出走了,也不好找工作養活自己。
一星期前,他拿到了年滿十六歲之后,去警察局辦的份證。
同時,他媽生日,家里請了一些親戚朋友吃飯。
他一開始不想跟人吵架,但他們一群人聊著聊著,又開始說他不聽話不肯上學的事。
他爺爺歷數他的罪狀討伐他,他媽也覺得他不知足,覺得已經給了他這麼好的條件,他卻不聽話跑去當混混,簡直沒救了。
他到底還是沒克制住。
他說他不想要這樣的“好條件”,是倒了八輩子霉才生在這個家庭。
他說他寧愿沒有被生出來,在這個家待著他還不如死了算了。
他說他媽有本事,就殺了他,不然再這麼對他,他就從樓上跳下去。
他說了很多很多,還掀翻了桌子。
他媽氣得不行,說他在福中不知福,但這福氣可不是他想要的。
不管是他爸,他爺爺還是他媽,都不了別人忤逆他們,不聽他們的話,更不要說在場的還有很多親戚,他媽當場就說他要是嫌棄這個家,就滾出去,以后別回來了。
當時一群人勸他們冷靜,他被推搡進了臥室。
那天半夜,他拿著賣了自己的手表換來的五百塊錢,還有自己剛到手的份證跑了。
他一直都是沒有零花錢的,他之前染發什麼的,都靠賣自己的服鞋子什麼的換錢,當然因為這個,他被打過好幾次。
大晚上的,他從那棟金碧輝煌的別墅里出來,走了兩個多小時到汽車站,上了一輛充斥著難聞氣味的大,就這麼奔向自由。
住破廟又怎麼樣?他自由了!
前幾天被蚊子咬得滿的包,但他依然是快樂的,就是總擔心他媽說話不算話,又找人來抓他。
不過他無論如何,都不會再回去。
猜你喜歡
-
完結336 章

愛你蓄謀已久
丈夫那方麵有問題,卻和情人半夜車震出了車禍,她四年的婚姻一夜之間兵荒馬亂。婆婆逼她給懷孕的小三出錢保胎,丈夫逼她去酒店陪睡擺平巨額賠償。在崩潰的邊緣,欠下的一百萬債務讓她忍下恥辱。為了幫丈夫善後,她屈辱地走進酒店。然而,昏暗的房間裏,將她狠狠壓在身下的男人眼眸深沉陰鶩,強迫她親手解開扣子,“程太太,知道該怎麼求我了?”對霍景洺來說,宋曉是他心頭拔不掉的刺,與其爛在心底,不如奪走她、占有她,哪怕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對宋曉而言,霍景洺是劫,愛上了就永遠逃不開躲不過。兜兜轉轉,愛你這條路,我從萬劫不複走到歲月深處。
65.8萬字8 58333 -
完結403 章

重生八零:獨寵小媳婦
九十年代的霍小文被家里重男輕女的思想逼上絕路, 一睜眼來到了八十年代。 賣給瘸子做童養媳?!丟到南山墳圈子?! 臥槽,霍小文生氣笑了, 這特麼都是什麼鬼! 極品爸爸帶著死老太太上門搗亂? 哈哈,來吧來吧,女子報仇,十年不晚吶,就等著你們上門呢!!!
72萬字8 9632 -
完結1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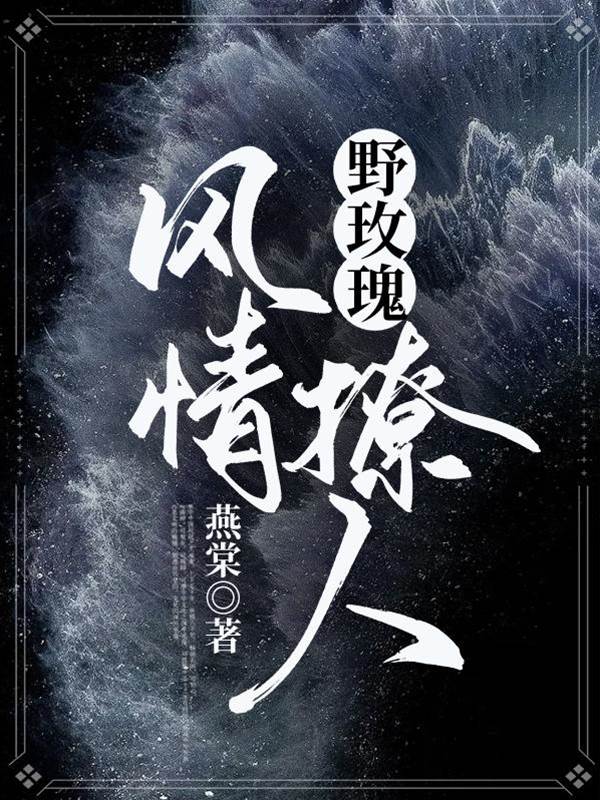
野玫瑰風情撩人
(已完結)【成人愛情、頂級曖昧、雙向勾引、極致拉扯、1v1】 眾人皆說明燭是江城第一惡女。 她瑰麗風情,出身又矜貴無比,撩男人隻需要勾勾手指,他們就跪在她紅裙之下。 眾人很嫉妒。 明燭喜歡被人嫉妒,惡女這個稱號也不錯。 於是她一開心,就去勾引了那個剛回國的衛家掌權人,衛陸饒。 聽說他又狠又絕。 - 明燭對衛陸饒撩撥蠱惑,而他肆意遊走於她的圈套中, 與她親吻、糾纏。 予她救贖、心動。 卻不更進一步。 當她意識到,他才是獵人,而她是獵物時。 她的心,已經被他攥在手裏。 成年人的感情遊戲,動心者即為輸家。 明燭選擇斬斷關係的那一晚,男人瘋狂而放縱,聲音嘶啞著說, “明燭,贏的人,是你……” “九年前,我就輸了。” - 明燭以為,和衛陸饒的開始,是她的引誘。 而實際上,是他的蓄謀已久! 他奉上真心、使用計謀、淪陷自己。 隻為了,讓她在人間被愛一場。 她永遠是他,可憐的小姑娘。
28.2萬字8 13931 -
完結1016 章

限量的你
潼市人人都說,聶相思是商界傳奇戰廷深最不可冒犯的禁區,碰之,死。 -- 五歲,一場車禍,聶相思失去了雙親。 “要不要跟我走?” 警察局,男人身形秀頎,背光而立,聲線玄寒。 聶相思沒有猶豫,握住男人微涼的手指。 -- 十八歲以前,聶相思是戰廷深的寶,在戰家橫行霸道,耀武揚威。 十八歲生日,聶相思鼓起勇氣將心儀的男生帶到戰廷深面前,羞澀的介紹,“三叔,他是陸兆年,我男朋友。” 戰廷深對聶相思笑,那笑卻不達眼底。 當晚,戰廷深將她擁在懷裏! 事後,聶相思白着臉道,“戰廷深,我要告你!” 戰廷深將兩本結婚證扔到聶相思面前,眯眼冷哼,“我跟我自己的妻子在一起,誰敢有異議?” 聶相思瞪大眼看着牀上那兩隻紅本本,徹底懵了! “還不快叫老公?” “……”
260萬字8.18 15482 -
連載496 章

拿到絕癥通知后,陸總說我還在裝
上京人人知道,陸宴景最恨的人是季淺。 季淺的解釋,陸宴景說她在狡辯。 季淺得絕症,陸宴景說她是裝的。 季淺被構陷,陸宴景眼瞎心盲拉偏架。 只有在牀上被他變着法折騰時,他纔會誇她哭的真情實感。 陸宴景以爲自己能把季淺困在身邊虐一輩子。 可當季淺真的逆來順受,對他的愛恨都不再給予迴應時,他突然就慌了。 陸宴景卑微乞求:“季淺,我不恨你了,你能不能再愛我一次?”
93.6萬字8 215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