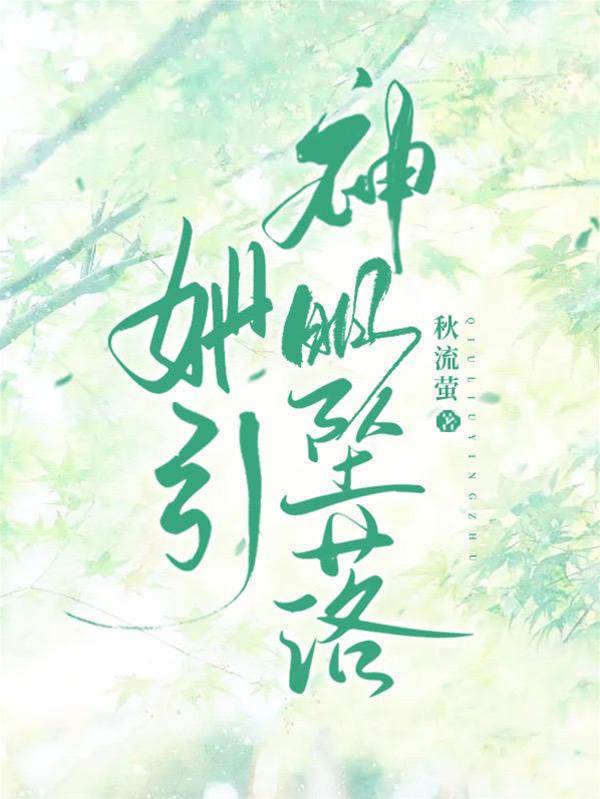《小情竇》 第83章 第八十三章
有時候宋枝蒽自己也納悶, 臉皮怎麼就那麼薄。
明明該發生的都發生了,可面對祁岸溫聲語的逗弄,還是無法自然地應對。
也虧得祁岸這話是, 才不至于面紅耳赤。
化完妝后, 宋枝蒽乖乖把祁岸帶上來的早午餐吃掉, 隨后又被祁岸投喂了兩片消炎藥,說消腫能快一點。
他這人一直都這樣,做什麼事都坦坦, 壞也壞得坦, 所以格外惹人心。
大概是關系突破后, 廉恥心也越來越不重要, 兩人出發前, 祁岸又著在沙發上親了會兒。
宋枝蒽無奈之下,只能上車后又補了一遍膏。
雖說昨晚已經經歷過張忐忑的一路,但這次還是不大一樣, 這次畢竟是見祁岸的父親,也就是他本質上最親的人。
知道心忐忑,祁岸一直牽著的手, 語調輕松地安,“別擔心,又不需要你做什麼。”
宋枝蒽看他, “真不需要?”
祁岸慵懶靠坐在座位上, 勾著角里氣的, “不然呢?帶你去看他已經很給他面子了。”
“更何況,”他好整以暇道, “我帶你過去又不是孝敬他, 而是告訴他, 我祁岸從今往后有主了。”
宋枝蒽沉默一秒,朝上翹了下角。
這話倒不是什麼哄開心的甜言語,而是實話。
祁岸從本上就沒指祁家接宋枝蒽。
甚至一開始他就盤算好,如果祁家有任何人讓宋枝蒽不開心,他就直接帶宋枝蒽離開,反正他幾個關系好的叔叔,酒店開得風生水起。
不過事實證明,他在過多擔心,最起碼以現在祁家兩位老人的態度來看,他們沒有不接納宋枝蒽的意思。
Advertisement
祁仲卿就算態度再怎麼強,也始終不過兩位老人。
有他這番話,宋枝蒽心漸漸松懈下來,臉上的笑容也變開心。
祁岸了的手,“笑什麼呢。”
宋枝蒽偏頭看他,“就是覺得,咱倆還配。”
祁岸煞有介事地揚起眉,“哪里配,展開說說。”
宋枝蒽輕抿,“就……咱們倆跟父母的關系都不太好。”
與其說不好,還不如說是生分。
宋枝蒽年遲鈍,如今想到自己的父親,更多都是后知后覺的恨意,恨他為什麼要對自己那麼不好,也恨他為什麼即便走,都走不干凈,反倒讓這個不疼不的兒替他苦。
而對于李秋,宋枝蒽更多的是無話可說。
即便李秋在辭職后,一直試圖聯系,可宋枝蒽一次都沒有搭理過。
也正因為這,才覺得自己并不“孝順”。
宋枝蒽幾分失笑,“如果你的家庭關系好,我可能還會擔心,你會不會覺得我不孝順——”
話沒說完,宋枝蒽就被祁岸拉著摟進懷中。
祁岸下頦兒抵著順的發頂,嗓音沉磁溫,“別整天胡思想,就算我家庭關系好,我也不會覺得你不孝順。”
為了杜絕宋枝蒽這個“不健康”的想法,祁岸語氣難得鄭重,“我喜歡你,跟你漂不漂亮,孝不孝順,全都無關,我喜歡你,就只因為你是你,明白嗎?”
宋枝蒽怎麼會不明白。
比誰都明白。
角浮起清甜的笑,宋枝蒽微微仰頭,眨著眼看他,“我也是。”
“……”
“不管別人怎麼看你,我都一樣喜歡你。”
路上兩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沒多久就到了祁仲卿養病的私立醫院。
Advertisement
這家醫院專門為有錢人服務,醫療設施和環境眼可見得高端和素凈,得知祁岸和宋枝蒽今天過來,祁仲卿的助理早早來迎接。
前往病房的路上,他還大致把況告訴了兩人,跟老太太電話里說的一樣,祁仲卿是惡腫瘤,已經做完了手,但是以后還有復發的可能,能撐多年,誰也說不清楚。
也正因如此,今天老爺子和老太太才親自去廟里給他祈福。
助理說的時候,宋枝蒽一直看著祁岸的臉,原以為祁岸會毫無容,但祁岸鋒冷的眉眼還是出賣了他的心。
沒有人會真的不在意自己的親。
祁岸只是看著疏冷淡漠,但他的心比任何人都要有有。
或許是因為心疼他,宋枝蒽在這刻莫名鼓足勇氣,在病房門打開的時候,沒有任何遲疑地跟隨祁岸一同進去。
如想象中一樣,祁仲卿的病房確實足夠奢華頂級,只是該養病的地方,卻依舊難以擺繁忙的公務,三個人進去的時候,祁仲卿還在跟書理合同。
直到聽到助理的說話聲,才抬起頭朝祁岸的方向。
這是宋枝蒽第一次見到祁仲卿。
很神奇的是,這個年過五十的中年男人,居然真的和想象中差不多。
和祁岸一樣冷厲俊朗的眉目,但看起來遠比祁岸正經威嚴,又有種飽經滄桑的干練,只是因病原因,他看起來比同齡人要蒼老一些。
可即便如此,也能讓人從中看出他年輕時的風姿。
在宋枝蒽默默打量他的時候,祁仲卿也在打量宋枝蒽,或許沒到當年那張合照里,資質平平臉上還有胎記的小姑娘,能出落到現在這副模樣,他稍稍有些驚訝。
但這瞬的驚訝,很快就轉變對祁岸的關注,“怎麼就只有你們過來。”
Advertisement
到底是生分了好幾年的父子,祁仲卿已經盡力寬厚,但說出來的話還是不怎麼中聽。
就好像在說,我可不想單獨見你。
偏偏祁岸也和他對著來,冷冷一笑,“你以為誰都有時間來看你麼。”
宋枝蒽了祁岸的手,示意他注意語氣。
哪曾想,向來脾氣火的祁仲卿非但沒生氣,還讓助理帶兩人坐下,“吃飯了麼。”
即便坐下,祁岸也牽著宋枝蒽的手沒松開,他沒接下話茬,而是問他,“病房怎麼就只有你自己,你那小老婆和兒子呢。”
話里明顯的輕蔑。
宋枝蒽也是在昨晚事后,兩人抱在一起促膝長談的時候,才知道祁岸還有個弟弟,這個小孩兒現在差不多四歲,他連面都沒見過。
他父親的這個小老婆,當初更是跟祁仲卿好了好多年扶正的。
祁仲卿在商界有頭有臉,是出名的企業家,也是有名的慈善家,他的人生履歷無疑是功的,但這并不意味他的私生活也多麼清正。
他這種階層的有錢人自始至終都擺不了那套活法,祁岸也接不了這樣的父親。
在外人面前,他多麼偉..正,可回到家,他卻和易茹各玩各的。
對祁岸來說,他并沒有一個好父親的模樣。
可祁仲卿卻熱衷于扮演一個好父親的角,為他籌劃這籌劃那,甚至為了讓他聽自己的擺布,不惜攪他的人生。
曾經的祁仲卿永遠都意識不到,他是怎麼將祁岸親手推開的,直到病來如山倒。
他才恍然發現,自己這輩子最失敗的是什麼。
他最的那個兒子,了最恨他的人。
而這種覺,在祁岸坐在他面前的一刻,的更為深刻。
祁仲卿知道他在諷刺自己,但還是語調平和,“我嫌他們吵,就不讓他們來了,自己一個人待著也很清凈。”
Advertisement
宋枝蒽莫名從這話聽出一種遲暮老人的意味。
祁岸結微滾,也顯然有同樣。
祁仲卿難得笑笑,“就是趕得時候不巧,你們要是晚來幾天,我還能出去招待一下你們。”
即便知道這會兒自己不應該說話,但宋枝蒽還是鼓起勇氣,擅自接了祁仲卿的話,“我們已經吃過了,謝謝叔叔關心,當下的況,還是叔叔您的病要。”
說這話的瞬間,祁岸跟祁仲卿一同朝看來。
祁仲卿是意外,祁岸則是意外中帶著些許另眼相看。
再然后,祁仲卿親眼看到祁岸寵溺地笑了下。
與他看自己時不同,這刻的祁岸,眼里是有的。
祁仲卿從沒見過這樣的他。
也許被這一瞬深深撼,祁仲卿在那天,和宋枝蒽說了不話。
而原本應該擔當主角的祁岸,卻始終在旁邊沉默著。
祁仲卿問了宋枝蒽許多,比如關于的家庭,學業,和現在的生活,語氣并沒有摻雜任何緒,而是平鋪直述地了解。
宋枝蒽也回答得不卑不,完全不再是幾年前,那個電話里茫然無措的小姑娘模樣。
對話就這麼進行了沒多久,宋枝蒽手機響了。
是個不認識的來電話號碼。
宋枝蒽表略有些為難,是祁仲卿開口,“沒事,你出去接,我也正好和祁岸單獨聊聊。”
宋枝蒽也不傻,乖乖笑了下,起要離開。
祁岸倒也沒攔著,只是在出門后多看了眼。
還是祁仲卿把他拉回神,“這姑娘,比我想象中優秀很多。”
兩父子之間的話題,似乎就只有關乎到宋枝蒽,才能對上話頭,祁岸沒有剛進來的敵意,沉聲一笑,“一直都很優秀,只是你一直用有眼看待。”
一個窮人家的小姑娘,姿平平,企圖通過祁岸攀龍附,是聽著就讓人生厭。
然而當他親眼見到宋枝蒽的時候,才明白,那些描述都與無關,也明白,為什麼祁岸非不可。
有一種知世故而不世故的聰慧伶俐,又有一種而不自知的純粹和謙卑。
跟祁岸,一個張揚一個斂。
沒有比誰能更像一樣,治愈和溫暖祁岸。
什麼家室,什麼門當戶對,遇對了人,其他一切都變得無足輕重。
大概是人走到生離死別這步,總會放下諸多執念,祁仲卿點頭,“好。”
祁岸沒想到這種話會從他父親的里說出來,神思一瞬凝滯,祁仲卿又說,“這三年,我應該早點過去見你一面。”
……
宋枝蒽從病房離開后,并沒有去太遠的地方。
電話一遍遍打得急,只能在就近選個安靜的地方接通。
其實一開始,想過不接的,因為這幾天,李秋一直有找,可當時那種況,也只能給祁岸父子留下空間。
只是沒想到,宋枝蒽著頭皮一接通,聽到的卻不是李秋的聲音,而是一個陌生的,年輕的聲。
生聲音禮貌又欣然,“您好,請問是宋枝蒽嗎?”
宋枝蒽愣了愣,“是,請問您是?”
生聽到是,立馬自報家門,說自己是北川大馬隊的副主席,之所以聯系,是希能幫忙勸勸祁岸,參加九月份的馬比賽。
宋枝蒽聽著的說話方式莫名耳,想起什麼,問,“你是在學校門口和祁岸加過微信的生嗎?”
生很驚訝,“你怎麼知道的?”
宋枝蒽心下了然,“那次我就在附近,無意識聽到你們說話。”
生沒什麼心機,心里想的都是怎麼勸祁岸隊,順著話茬就把來龍去脈代清楚,說找宋枝蒽也是不得已,因為祁岸在通過微信申請后沒多久,就把刪了。
理由是,怕朋友不高興。
于是該生就覺得是不是宋枝蒽誤會了什麼,也借著聯系不到祁岸的機會,想通過這邊來說服祁岸。
宋枝蒽倒沒想過那會兒隨口的質問,還真讓祁岸有所行,一時有些哭笑不得。
兩人通了下,宋枝蒽做了個大膽的決定,“我試試看吧,至于他答不答應,我也不好跟你保證。”
生大為驚喜,“真的啊,那太謝謝你了!!!”
電話掛斷,宋枝蒽心稍稍平復。
又莫名有些雀躍。
這種雀躍,一方面是因為,“祁仲卿”這塊重擔,好像已經在無形中被和祁岸化解,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真的很希祁岸可以放下心結,重新回到賽場。
宋枝蒽莫名覺得,祁岸也許會聽的話。
事實證明,的想法確實是沒錯的。
當天祁岸從病房出來后,這場見面就結束了,祁岸狀態看起來比來時要輕松一些,卻又有些無法言說的沉重。
回去的路上,變宋枝蒽牽著他,等著他對自己敞開心扉。
似是在想著怎麼跟說,祁岸好一會兒才開口,“他跟我道歉了。”
宋枝蒽默默看著他,“然后呢?”
“然后,”祁岸垂下長睫,驀地一笑,“我發現我早就不恨他了,我只是埋怨他,為什麼從來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思考。”
宋枝蒽與他十指相扣,“可能,他只想給你最好的,只是找錯了方向。”
祁岸勾勾,“我以后一定不要做這樣的父親,我只要我的孩子健康快樂。”
說話間,他眸玩味地看著宋枝蒽,“你覺得可以麼?”
宋枝蒽沒有讓他的調戲得逞,而是正兒八經道,“你想孩子之前,是不是先想一想自己的事。”
祁岸挑眉,把扯過來抱著。
宋枝蒽香香,抱起來手格外好,祁岸埋在頸間深吸了一口氣,仿佛被治愈。
宋枝蒽卻拿出說正經事的態度,“那個馬隊的副主席,給我打電話了。”
祁岸微微抬眸,有些好笑,“倒是會找門路。”
宋枝蒽像那麼回事地嗯了聲,“因為聽說祁岸是金融系出了名的妻管嚴。”
似乎也覺得麻,宋枝蒽往下抑著角,別開視線。
祁岸聽樂了。
頭一次見到說著說著自己還不好意思的。
祁岸問,“那你怎麼說的。”
宋枝蒽沒吭聲。
祁岸起宋枝蒽的下,讓扭頭看向自己,調子吊兒郎當又放浪,“你老公問你話呢。”
雖然這個稱呼,昨晚被他到嗓子都喊啞了,可在車上被他這麼一嚷,宋枝蒽還是有些尷尬。
趕忙回頭瞪他一眼,那眼神好像在說車上有司機。
祁岸笑得壞,毫不在意地把摟得更近了些,“你怎麼說的。”
話里完全沒有在意司機的意思。
宋枝蒽也算是服了,只能投降,干道,“就說……你確實聽我話的。”
祁岸湊到耳畔若有似無地親著,咬字低黯,“還有呢?”
宋枝蒽心猿意馬,小聲咕噥,“還,特別粘人……”
因為這句,祁岸當晚又給宋枝蒽展現了一遍他的“粘人”功力,也虧得房間隔音效果好,宋枝蒽第二天面對長輩們才不至于太丟人。
只是膝蓋紅得有些明顯,被涂了底遮蓋,脖子也了一個創可。
但這并沒有影響祁沫看煞有介事的調笑目。
后來還是祁岸告訴,那東西兒就是祁沫準備的,小丫頭欠了吧唧的,回頭一看里面空了,自然知道怎麼回事。
不過這一晚上的春風得意,也確實搞定了祁岸,祁岸答應參加馬隊。
猜你喜歡
-
完結315 章

月亮在懷里
退出國家隊後,祁月投身農學專業。某次聚會上,有人起哄,誰射擊遊戲輸了就要被祁月親一下。看著試驗田裡扛著鋤頭不修邊幅一臉泥巴正在種土豆的祁月,大傢伙的臉都綠了。所有人爭先恐後瞄準靶心生怕被罰。最後的結果是,A大男神顧淮抬起手,脫靶射了一個0環。第二次見面的時候,顧淮在擊劍館被惡意挑釁步步碾壓。祁月看不下去被迫出手。第三次見面的時候,顧淮在路邊無家可歸。祁月為了幫他,花光了三個月的生活費。多年之後。祁月看著從家裡翻出來的寫著顧淮名字的世界射擊記錄證書、擊劍冠軍獎杯以及十幾套房產證,陷入了沉思:“……”
28萬字8 25647 -
完結607 章

分手后,被前任小叔纏吻肆意寵
【妖冶絕艷人間美色VS禁欲悶騷高嶺之花,1V1,雙潔】 一個人負責撩,一個負責寵,雙向奔赴,互為救贖,甜到爆炸~~~ 作者簡介無能,一個字,就是甜。 全程高能,甜到你打滾,甜到你捶墻,甜到你上天入地大聲囔囔瘋狂喊娘。 入股不虧,寶子們趕緊上車,我們出發啦——
87.3萬字8.18 180316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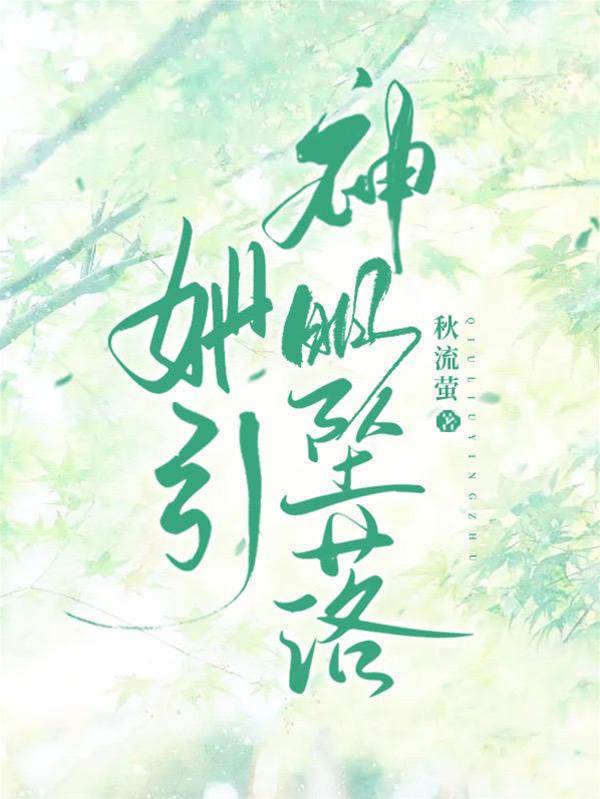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4572 -
完結322 章

賀總為白月光取消訂婚,我不嫁了
賀寒聲有一個如珠如寶的白月光。戀愛紀念日,他跟白月光在燭光晚餐。她的生日,他陪白月光散步。答應她的演唱會,他也推了去陪白月光。直到訂婚宴當天,賀寒聲因為一個白月光的一個電話取消了訂婚。姜星染愛了七年的心終於死了。她給賀寒聲發了一條分手簡訊,就離開了。賀寒聲覺得她就是鬧脾氣了,冷一冷她就好。直到……她跟別人領了結婚證。那位高高在上,永遠運籌帷幄的賀總瘋了!!!
56萬字8.33 282580 -
完結487 章

婚然天成:景少的秘製愛妻
從景仲言的秘書,到成為她的妻子,整個過程中,喬蕊都扮演著被動者的角色。景仲言說他需要一個妻子,她最合適,喬蕊覺得自己需要保住這份工作,就忍辱負重的同意了。可說好的,婚後分房,各安其身呢?為什麼這男人卻不守信用,不但步步緊逼,弄得她丟盔棄甲,還各式花樣的將她翻過來,轉過去,折騰個沒完沒了。不過還好,當那個曾在他生命中留下最最濃豔色彩的女人迴歸時,喬蕊覺得自己終於可以全身而退了。只是……
92.3萬字8 683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