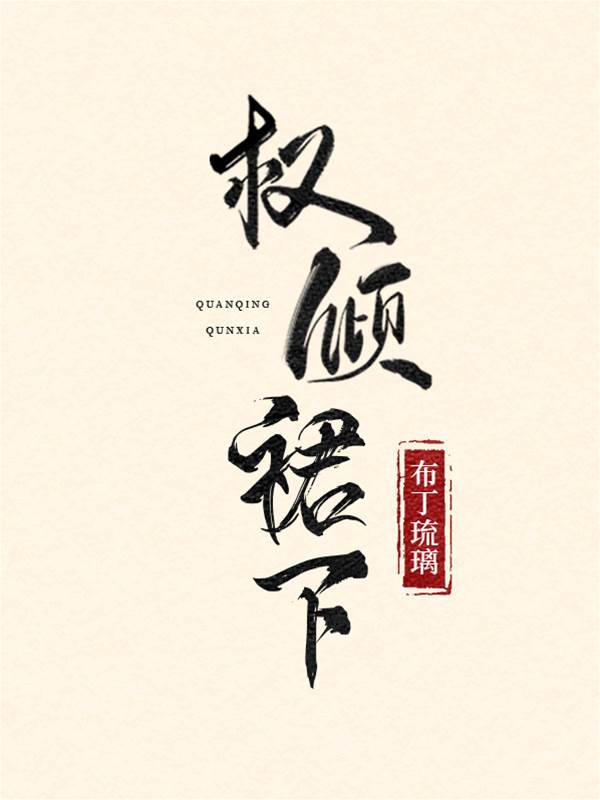《貴妃裙下臣》 夜宴(三合一)
李令月著裴濟難得化了幾分的堅毅面龐,眼神閃了閃,竟是浮上一層細細水霧。
垂眸瞥過已被飲空的酒杯,忍著哽咽道了句「多謝表哥」,便低著頭起,快步離開這一片歡宴之地,往麟德殿中一早已尋好的偏僻偏殿去了。
邊的宮人悄悄向太后與李景燁低語數句,道公主有些不適,先下去歇息。
太后與皇帝二人本都有些心不愉,方才也瞥見了李令月往裴濟那裏去,只當又被裴濟冷落,心下不快才離開,便也不多管,只命那宮人好生照看。
便在這時,人群之中忽然傳來一陣驚呼。
原來方才去更的麗質,此刻已隨一眾樂師們緩緩步上臺去了。
比之方才,又稍做了一番裝扮。
烏髮盤作雲髻,斜一支鳥雀銜珠金步搖,隨著行走的步伐慢搖輕,別韻致。眉間了抹金相間的海棠花鈿,在燈火映下熠熠生輝,更襯得眉目如畫,顧盼生姿。
緻艷的面與修長纖細的脖頸間,除了雙塗脂外,不施黛,可饒是如此,卻通無暇,瑩白勝雪,再配一火紅榴花舞,更襯得艷嫵,令人萬黯然失。
殿中千人,皆移不開眼,先是不約而同地靜了一靜,隨即驚艷讚歎之聲不絕於耳,不娘子更興地討論起貴妃這一裝扮,料不到半月後的長安,子敷鉛之風便會過去大半。
而最高,皇帝與邊眾人則心思各異,一時都將目放在臺上之人上,再沒人注意李令月的離開。
不多時,但見麗質沖眾人微彎腰肢,隨後示意樂師們奏樂。
一曲《春鶯囀》隨即奏出。
樂聲如春日晨起時的鶯啼,由空靈婉轉,漸至歡快活潑,麗質的舞姿也隨之由靈漸漸變得輕盈熱烈。
Advertisement
腰肢,寬擺如柳枝,偶爾彎折,顯出驚人的纖細,時不時引座下眾人驚艷高呼。
大約是因生得比舞姬們都更上幾分,這分明是常見的舞,卻偏偏被跳得極富染力。不多時,座下飲了酒的男竟有不已開始隨樂聲與共舞。
夜宴氣氛一時被推至高|。
裴濟著臺上的麗質怔怔出神。
自方才登臺時,他心底的鬱結便好似掃去大半,漸漸化作幾分抑不住的燥意。
那一抹火紅的影漸漸與那日太池邊涼亭里的影子重疊在一起。
他腦中有片刻混沌,莫名想起那一日,在紫宸殿外,曾說會再為他跳一支舞。
可今日的舞卻是獻給陛下的壽誕之禮。
他眼神黯了黯,努力剋制著心底再度漫溢而出的鬱與燥意。
然而不知為何,那一團糾結在一的複雜緒卻沒有半點熄滅下去的趨勢,反而慢慢漲開,繼續侵蝕著他心底的角落。
他暗暗蹙眉,擱在案下膝上的雙手悄然拳。
臺上樂師們奏出的樂曲漸漸止息,麗質的舞也趨近收攏之勢。最後那一刻,放腰肢,輕點腳步,雙臂舒展時帶起帶與廣袖翻飛,如倦鳥歸林一般,收攏軀,慢慢伏跪在地。
一時眾人屏息凝視,呆怔一瞬,方回過神來,紛紛擊掌讚歎。
麗質緩緩起,沖不遠的李景燁微微躬行禮,聲道:「妾向陛下獻醜了。」
李景燁此刻也沉浸在驚艷震撼之中,平淡溫和了一整日的面容終於出真心而喜悅的笑容。
他知道麗質貌異常,也見過無數技藝湛的舞姬跳過《春鶯囀》,甚至如今宮裏的幾位才人中,也有曾給他跳過此舞的。
可他卻沒料到,由貌異常的麗質跳出的一曲《春鶯囀》卻比他見過的任何一次都更令人驚艷難忘。
Advertisement
他親自步下座去,行至臺上麗質邊,眾目睽睽之下彎腰托著的雙肘將扶起,揚聲道:「貴妃一舞,足令萬失,朕今日得見,實是大幸。」
皇帝讚譽至此,旁人自然紛紛附和。
麗質莞爾:「蒙陛下不棄,妾慚愧。」
李景燁牽著的手將重新帶到自己邊坐下,示意臺上演出繼續,隨即也不顧太后厭惡的神與嬪妃們羨慕又嫉妒的模樣,轉頭了的手,輕聲道:「麗娘的心意,朕看到了,今日千上萬的賀禮,都不及麗娘的這一個。」
「陛下喜歡就好。」微笑,拿了帕子拭額角的汗珠,起道,「妾還需往偏殿沐浴更,請陛下恕罪。」
李景燁鬆開握著的手,滿是憐,點頭應了,目直著的影消失,才慢慢收回。
太后始終冷眼旁觀,此刻見他如此模樣,不由到一陣無力。
面疲憊,沖李景燁擺擺手,道:「我年歲大了,有些撐不住了,這便要回長安殿去歇下了。」
李景燁見狀,知道母親心中不快,面上的笑意也跟著淡了些。
他親自從座上起,沖太后躬拱手,恭敬道:「朕的壽誕本也是母親難的日子,朕在此與眾人同樂,卻又讓母親勞累了,是朕的不是。」
到底是自己上掉下的,又親手養到這樣大,太后聽罷,心中也生出幾分慨與不忍,最終輕嘆一聲:「罷了,陛下不必擔心我,且與群臣同樂吧。」
說著,又與大長公主招呼了一句,也不必何元士送,由邊的宮人攙扶著回長安殿去了。
太后一走,原本力求端莊溫婉的嬪妃們便稍稍放鬆了些,趁麗質不在,也同皇帝說著話。
殿中歡笑作一片的人們漸漸又歡笑作一片。
Advertisement
裴濟卻默默垂眼,沉默不語,只覺心底裝著一團火,還未燃起來,卻讓他有些莫名的難耐,連心神也止不住地渙散。
見天差不多,他便起往宮中各去巡查。
自為大將軍后,每逢宮中大宴,他都會中途離開,四巡查,以防意外。這幾乎已了慣例。
然而就在他站起,目不經意自周遭瞥過時,卻發現旁原本正坐著沉默飲酒的睿王竟已不知所蹤。
他作微頓,飛快地掃一眼其桌案上飲得剩下半杯酒,不由蹙眉。
只是心中那一團火令他有些煩躁,並未深究,只衝陛下和母親拱了拱手,便轉往外退去。
待退出人群,離開主殿,他只覺燥意仍未消退,反而有緩慢地加重的趨勢,不由更加快腳步。
主殿附近還有往來的侍與優伶,他未如往常慣例一般先去麟德殿各偏殿巡查,而是徑直步出,順著龍首原緩坡下行。
殿外空闊,秋日涼風吹來,終於令他神思暫且清明了些。
方才那人在臺上艷麗的舞姿再度自腦中閃過,他微微晃了晃腦袋,隨即卻回想起睿王空空如也的座位。
雲來樓里的對話漸漸在耳邊迴響。
他猛地一激靈,倏然收住腳步。
那人離開主殿去更,睿王恰也消失……而且,似乎不止他一人發現,方才離開時,他恍惚間看到陛下的目,也正落向那張空著的座位!
他暗道一聲不好,腦中的混沌與難耐登時去了大半,轉便重新回麟德殿去。
……
麟德殿西側的一偏殿裏,麗質才沐浴過,烏髮仍高高盤著,拿起一旁搭在屏風上的淺羅換上。
是貴妃,不能與今日數以千計的伶人在一更梳洗,教坊史便特意替尋了這間離正殿稍遠的偏殿作更休息之。
Advertisement
此刻正殿中笑鬧歌舞聲不斷,此卻是鬧中取靜,格外適意。
方才那一舞后,有些四肢酸,眼看正是宴酣之時,不願回殿上,便在此小憩片刻。
只是才在榻上不久,春月便急急奔來,輕聲道:「小娘子,睿王果然過來了!」
麗質一下睜眼,目也即刻清明起來。
先前在殿上時,便總有些惴惴不安,覺得有什麼事要發生,於是方才更沐浴,就多留了個心眼,讓春月將外間的窗開著,觀遠長廊,果然便見睿王來了。
毫不猶豫自榻上起裹了件披帛,拉著春月便從門邊閃而出,躲到廊下拐角暗,噤聲不語。
李景輝是睿王,犯再大的錯也是皇家子弟,有太后護著,卻不能掉以輕心。
千秋節皇帝的逆鱗,不死也得層皮。
不出片刻,李景輝果然步履沉重地靠近殿門,還不猶豫地抬手輕叩門板:「麗娘,你可在裏面?」
屋裏自然無人應答。
遠遠的,麗質從暗看見李景輝剝落頹唐的面上有幾分焦躁與迫切,似有滿腹的話要說。
等不到回應,他只猶豫一瞬,便深吸一口氣,手便直接將門推開,眼前的形卻令他一愣。
屋裏樹支燈燭都靜靜燃著,將相連的外兩室照得格外敞亮,香爐中的香煙也正裊裊升起,空氣里除了幽香,還帶著曾沐浴過後淡淡的水潤霧氣。
獨獨不見人影。
他呆立在門邊,似乎滿腹愁緒找不到宣洩的地方,一時回不過神來。
拐角,麗質屏息凝神觀著,正想悄悄離開,卻忽然見不遠的廊邊,又有人正快步行來。
那人一明黃常服,步履極快,後的兩個侍躬著腰追趕不及,隨著漸漸靠近,已能看清他面上的鬱與怒意,正是李景燁。
隔著數丈距離,他忽然停住腳步,著敞開的門邊怔怔發愣的弟弟,忍許久,終於冷冷開口:「六郎。」
立在門邊的李景輝渾一僵,緩緩轉過去。
兩個侍悄悄退開。
二人對視片刻,李景輝喚了聲「陛下」。
李景燁一步一步走近,先往空無一人的屋裏看了一眼,隨即面無表問:「你在這裏做什麼?」
自數月前的婚儀之後,兄弟二人幾乎沒再私下獨過,此刻正面相迎,再沒了從前的親近。
李景輝咬了咬牙,直言道:「我來找麗娘。」
「放肆!」李景燁幾乎是立即厲喝出聲,著弟弟的眼神里俱是冷厲的迫與威勢,「麗娘的名諱,是你能直呼的嗎!」
李景輝冷笑一聲:「我怎麼不能,陛下別忘了,可是我的王妃,是與我行過婚儀的,我既未與和離,也未寫過休書,自然還是我的妻子。」
「不是你的王妃。」李景燁面沉,話語里已經沒了半點為兄長的溫度,「你大可去宗正寺的譜牒上看看,看看到底是你的王妃,還是朕的貴妃。」
「你!」李景輝震怒不已,年輕意氣的脾氣被徹底激發,開始口不擇言起來,「你不過仗著自己是天子罷了,若非如此,你以為麗娘會願意宮嗎?你將我與麗娘強行分開,朝中上下,乃至天下百姓,無數雙眼睛都看著呢,你若不是天子,只怕早已被人唾罵鄙夷,再抬不起頭來!這天下,哪有搶親弟弟人的兄長!」
他一番話說得激不已,字字誅心,卻反而讓李景燁原本要噴薄而出的怒火漸漸平息下來。
他面無表地著弟弟,目冷淡得彷彿在看腳下的螻蟻。
「是,朕就是仗著天子的份。你呢?你又仗著什麼?仗著母親的偏寵嗎?可惜,朕是萬民之主,天下的的一毫一厘都是朕的,朕不但可以要你的人,朕也可以將你廢為庶人,更可以要你的命。這便是權勢。」
說著,他輕嘆一聲,似乎不過一瞬,又恢復個關心弟弟的好兄長。
「六郎,你已及冠,卻為何還是這樣天真?果然是母親從前太縱著你了。明年開春,朕會替令月在新科進士中擇才俊,屆時也會替你再在貴中擇一位配得上你的王妃。如今大魏雖是太平盛世,可你為皇室子弟,不該沉溺於一己私慾,也該將心思多放在大事上了。」
李景輝錯愕地著他,彷彿頭一次看清眼前這位從小尊敬的長兄。
為皇子,他雖從小養尊優,得父母寵,卻也知道自古以來,皇室之中父子反目、手足相殘的事並不鮮見。
只是他一直就明白,長兄是太子,將來會繼承父親的皇位,而他只做個閑散宗親,便能安樂一生。
他看來行事張揚,放浪不羈,可心裏卻始終明白什麼是自己的,什麼不是自己的。他也一直認為自己與長兄多年默契,只要他不覬覦那個位置,長兄定不會虧待於他。
他哪裏是天真不經事?不過是表明自己的態度罷了。
不論如何,到底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脈相連,兄友弟恭在皇家雖,卻也不是沒有。
可直到今日,他才意識到,長兄似乎並不是這麼想的。
他這個弟弟在長兄眼裏,也不過是草芥。
「是我天真了。」他忽然冷靜下來,默默垂下頭去,本就瘦了些的影顯出幾分慘淡,「陛下心懷天下大事,區區婚事,不勞陛下心。今日陛下千秋,願陛下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說罷,他轉快步離開。
李景燁仍立在原地,著空無一人的屋中一不,片刻后,方雙手背後,轉離開。
長廊中復又空無一人,只隔著的高牆外有恢弘的樂聲與眾人的笑語聲傳來。
麗質在暗,面有些冷,直等到被春月扯了扯袖才回過神來。
那一對兄弟,看似是因而起的爭執,可他們哪個人問過的心意?分明都是為了私慾。
秋夜裏的空氣有些涼意,攏了攏肩上披帛,也不願再回殿中,轉道:「走吧,咱們回承歡殿——」
話音未落,雙眼便對上一道悉的,帶著怒意的凜冽視線。
的腳步頓住,隔著數丈距離與他對片刻,忽而微微一笑:「將軍怎會在此?」
想起來了,中秋之夜,正是李令月給裴濟下藥,他不得不與自己婚的時候。
裴濟盯著雲淡風輕的微笑,垂在側的手暗暗攥。
方才他半道折返,一路上行得極快,可還沒走近,便看見何元士正守在廊下。
看來陛下已來了,他心下警醒,忙避開這一,從偏殿後側繞過來,先窺一窺況。
可還未待他走近,卻見眼前這人正帶著婢在暗,平靜地看著不遠的皇帝與睿王爭執不休!
一時間,他也說不清心底到底是何種滋味,憤怒有之,不解有之,鄙夷有之,甚至還夾雜著的慶幸與失落。
而此時,竟還能像置事外一般,對著他出笑容。
他深吸一口氣,閉了閉眼,沉聲質問:「你——到底有沒有心?竟還能這麼無於衷!」
麗質沒應聲,只轉頭對春月道:「去同陛下說,我乏了,先回承歡殿歇下了。」
春月小心又戒備地看一眼裴濟,似乎在提醒謹慎些,隨即轉離去。
麗質笑著裴濟,緩步靠近,在一步之遙的地方停下,仰頭迎上他的目,輕聲道:「妾有沒有心,將軍不知曉嗎?早已放在將軍這裏了,何必明知故問。」
猜你喜歡
-
完結2267 章
神醫狂妻:國師大人,夫人又跑了
風如傾,流雲國第一紈絝,她貌似無鹽,霸男欺女,卻仗著有皇帝老子疼愛,不但棒打鴛鴦,強嫁給丞相府公子為妻,更是氣暈婆母,最後因一旨休書而傷痛欲絕,就此了結了一生。 再睜眼,鋒芒畢露,她不在是胸大無腦,橫行霸道的紈絝公主。 …… 聽說,公主府的奴仆都是靈獸,而那廢柴公主每日喝的都是萬金難求的靈藥膳。 聽說,丞相府的公子前去找公主複合,被公主橫著踢了出去。 聽說,昨日又有美男心甘情願的上門,要為公主的奴仆,結果差點冇被國師給打死。 聽說,公主把天下第一美貌的國師給睡了,現在國師正到處找她要讓她負責……
200.2萬字8 199224 -
連載3264 章

醫妃逆天:廢柴大小姐
“廢物!背著本宮,你究竟和多少個男人鬼混過!?”一個耳光,她被打的口鼻出血,渣姐趁機加害,讓她一命嗚呼亂葬崗!再睜眼,鋒芒乍現,浴火歸來!渣男前任帶著丹藥新歡欺上門,她嗤笑:“這種垃圾,也好意思拿出來丟人現眼?”一紙休書,甩在他臉上,讓他有…
590.9萬字8 65066 -
完結260 章

絕世丑妃(完)
她,臉有胎記奇丑無比,卻遇上他獨獨鐘愛那張容顏。不顧世人的眼光,他將身為他弟媳的她納為己有。他無比溫柔,她步步淪陷。最終發現她也不過是另一個女子的替代品而已。失子之痛令她傷心離去,再次相遇,他對她說,“賤人,你連給朕暖床的資格都沒有!”他的…
28.9萬字8 29637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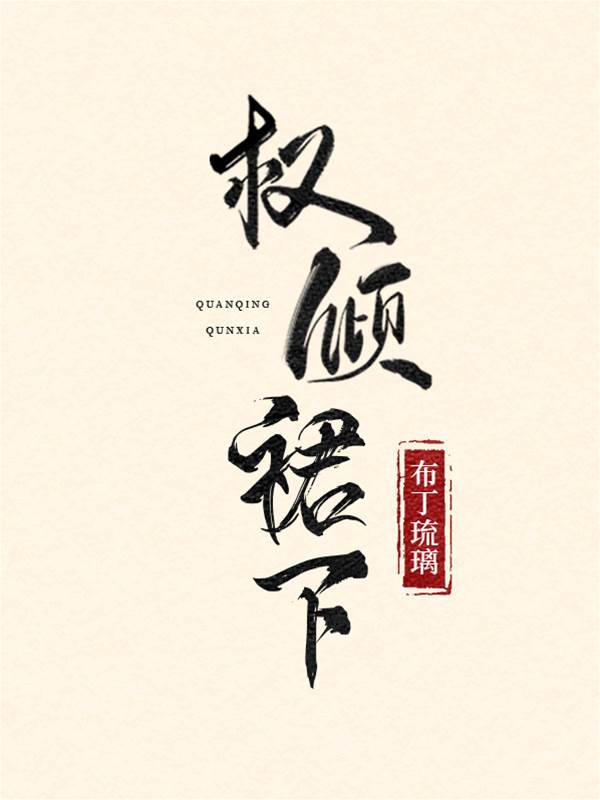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2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