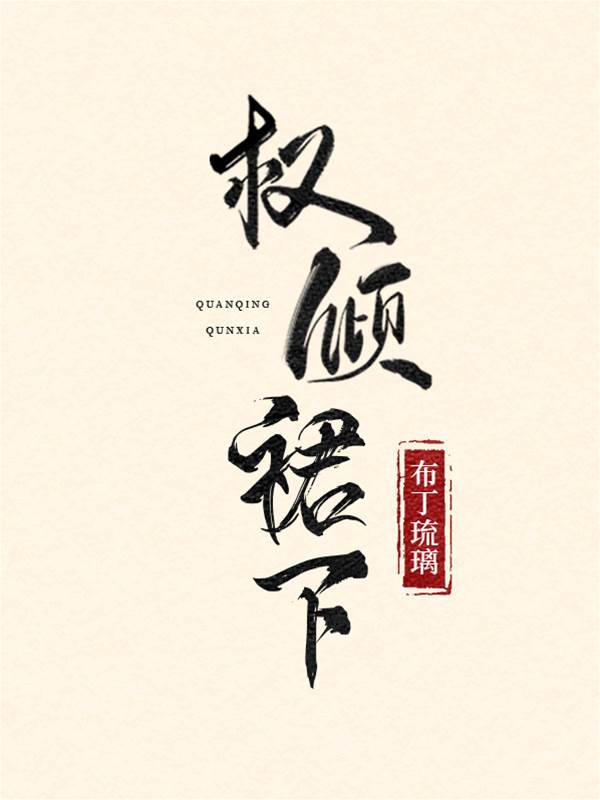《我力能扛鼎》 第311章 第311章
被這麼多人喊住,席春也沒出異,跟車上的爺通稟一聲,往車尾找了個面。
“別人都當我是天生的半啞,小神醫果真慧眼如炬,能看出是舌頭的病。只我這是陳年舊傷了,看過大夫,都說沒法治。”
席春張給他們看。
他并沒有斷舌,可舌面、舌系帶底下是大片的瘢痕,任誰看了心里都怵一下。
舌系帶說的是舌頭底下的那舌筋,正常人的這條筋該是能夠牽拉舌頭自如的,而席春舌上瘢痕重得舌面、舌底都是糊爛一團,他沒法像正常人那樣吐出舌來,更別提發聲咬字。
有唐荼荼的揣測在先,幾個影衛眼神都鋒利起來:“這是什麼傷?”
他們說話沒有低聲音。馬車上的席四爺聞言,目陡然鶩,擱在墊上的五指似要出,他側過臉,在窗上,在一片雜音中細細聆聽著席春的每個字。
車窗上投著一小片灰影,席春眼珠了,緩緩開口。
“那是時的事了。文和三年,十二月初九,大寒節令,我在河面上嬉冰,不慎墜了冰窟中……諸位興許不知,凍僵了的人不能到火邊烤,驟冷驟熱,連皮帶都要掉下來,需得裹上毯子、服食熱粥熱水,從里到外慢慢復溫。”
“當時,公子為救我命,來不及燒水了,倉促中,命人從火爐子里揀了幾塊熱炭,融雪水給我灌下去,留住了我的命,只是炭心滾燙,燙傷了舌頭——那之后一年,我口不能言,舌頭屈都難。公子教我含著石子說話,勉強才算是能出聲。”
“公子是好人。”席春低聲道:“奴才一條賤命,公子尚且如此待我,微姑娘比我更得寵慣百倍。諸位這樣多疑,未免寒人心。”
Advertisement
席春很慢地說完,一不的,任由他們打量。
誰也沒看到,他垂著的眼簾底下是一片茫然的冰寒。
一群差衙役這頭,又看看那頭。晏昰怕唐荼荼有顧慮,拍拍肩膀:“還有什麼疑點,一并問了。”
唐荼荼搖搖頭:“沒有了。”
再回想自己這一宿,鬧來了差,鬧來了這麼多人,實在是糊涂。從沒救下巧鈴鐺開始,就陷了魔怔一般,腦子渾了,眼睛也花了,連席爺是哭是笑都沒看清,無憑無據,妄加揣測。喪服?什麼喪服,原來是茶白……
唐荼荼只萬幸沒張揚出聲,不然,怕是要給爹爹惹大麻煩。
“席春,敘完話了麼?”
車門上鑿壁刻梅,席四爺的影在這幅梅花圖上頭,恬靜得像幅水墨畫。
唐荼荼沖馬車的方向屈膝行了個禮,心里冒出歉疚,又實在不知該說什麼,只好閉口不言。
“春先生這確實是舊疾啊。”杜仲打著燈照了照,裝模作樣診了兩句,暫時想不著如何治,目送席春回了席家的隊伍。
蓬萊閣大門一開,才知道外邊圍了多人。
閣里出了命案,留下等著質詢的又都是沒經過事的爺小姐,家中長輩哪里能放得下心?都派了大管事在門外等著。
唐老爺比別家的長輩更急,荼荼今兒出門只帶著個馬夫,連丫鬟也無,唐老爺急得自己過來等消息了,在門柱下兩腳不停地踱著步,急得站不住。
門一開,他直直往里走,抻著脖子四找。
“荼荼,荼荼!爹在這兒呢。”
看見閨裹著不知道誰的披風,披風底下淋淋半水,唐老爺差點嚇出心梗來,一疊聲問:“你也落水了?”
Advertisement
對完幾句話,才把心收回肚子:“沒事就好,沒事就好,爹聽說墜海的是個姑娘,可嚇死我了——你娘們在侯館等著,非要過來,那不是添麼,我好說歹說才勸住。”
街上東西兩向都車馬堵了路,老爹急得要命,兩條跑進來的,馬車還在老外邊。他攥著荼荼的手往街口走,手里熱汗涔涔的,卻也暖得出奇。
唐荼荼埋臉往袖子上蹭了蹭。
“怎麼哭了?啊?丫頭是不是嗆水啦?”唐老爺急得拿手指抹臉,越抹水越多。
唐荼荼其實沒想哭,就是沮喪,難過,眼睛本來是干的,唐老爺越是追著問,那一點點委屈越是發酵,變了一大團。
“我想救人的,沒救回來……”
唐老爺放下手,替那素昧平生的人嘆了聲:“生死都是命,沒法的事兒。爹過來的路上聽說,這閣年年摔死人,醉了酒的、失了足的、懷才不遇的、做生意沒做好家敗人亡的,盼著一跳能登天,盼著閉眼見圣賢。和尚道士作法驅障都沒用。”
“今年也怪爹爹,答應得痛快,沒想這許多。荼荼沒事,啊,就今年看看熱鬧,咱家以后再也不來了。”
蓬萊閣其實不高,主樓三層堂,景樓七層塔,可在這每高一尺都代表高一層權勢的時代,這閣就是有的高樓,站在樓頂憑欄風,手摘星。千百年來文人墨客揮毫潑墨,也不枉仙人上天選在這兒。
唐荼荼回頭,這座金碧輝煌的樓在眼里一下子黯淡了,澤盡失,丑得出奇。
等回了候館,又是一通紛。
家里的眷對“淹死”沒什麼概念,京城河湖,沒聽過有誰死得這樣不面,又聽家丁把小姐對著死尸吹氣的事說得有鼻子有眼,丫鬟們都嚇白了臉。
Advertisement
“姐……”
珠珠的臉,眼淚汪汪的,憋出一句:“你是不是想學話本子里的仙人,吹一口氣,死的就變活了?”
“珠珠別鬧你姐姐,回你屋去。”唐夫人的心正著,不能聽什麼死死死的,把小丫頭攆回房,催廚房燒了三壺熱水,盯著荼荼泡了個熱水澡,干頭發,又盯著灌了半碗姜湯。
今兒穿出去的裳鞋都讓奴仆拿去燒了,怕不吉利,首飾沒舍得扔,放匣子里鎖住了,回頭找個佛寺開開。
裳被拾掇出去的時候,唐荼荼支起眼皮了一眼,沒力氣吭聲,權當讓母親做個心安。
家里沒人知道溺水急救是什麼,但關于死人、關于除晦氣的講究,誰都能說出一兜籮。除了珠珠,沒人在意為什麼要往那尸里吹氣。二姑娘發癔癥的回數那麼多,再多一件,也沒什麼分別了。
待人都走盡,已是子時了。
唐荼荼蜷在床上,面朝墻,牙齒咬著指關節一點點地磨,在這微弱的疼痛里冥想,靜心、放空、緩解焦慮。
只是作用不大,無論腦補大海還是藍天,怎麼也不住腹中的,那子意,像是要從肚腹到口掏出一個大,唐荼荼得甚至記不起自己今夜吃沒吃東西。
窗上忽然響起叩擊聲,篤篤篤,三聲,沒人應,又敲三下。
大概是嫌回應太慢,那扇窗自個兒從外邊開了,一雙手到窗臺上,放下了……一只砂鍋??
砂鍋孔冒著熱氣,想是燙得厲害,兩只手隔著墊布都端不住。晏昰站在窗外,頭頂著滿天月,瞳仁黑亮亮的,只裝下一個,眼里是很人的一點暖意。
“剛離火的砂鍋羊。昨天剛雇的廚子,端過來給你嘗嘗合不合胃口。”
Advertisement
“二哥你神了,怎麼猜著我了的?”唐荼荼遲鈍的緒一齊齊復蘇,看見二哥與看見砂鍋的雙份喜悅,把那些壞的緒全沖了個干凈。
忙把桌子騰出來,了砂鍋耳朵,燙得回手,只能看著二哥墊著布把砂鍋往桌上挪。
“哎呀,您給我端飯,真是折煞我了。怎麼連個端飯的人手都沒了?”
晏昰莫可奈何地看著。他多的是人手可用,只是候館的院這麼小,一個四方院里六間屋子,從主到仆十來口人都在院里頭,但有一點靜驚起人來,家的奴仆大概就要提著扁擔嚷嚷“抓賊”了。
窗外又進來一雙賊爪子,放下兩副碗筷和湯勺,不知是哪個影衛,頭都沒往窗里探,溜得比來得還快。
砂鍋一揭蓋,撲鼻的香,那子羊特有的膻味淡得幾乎聞不著,唐荼荼端起碗,吃了一口又放下,把梳順的頭發扎丸子頭,再埋下頭去吃。
晏昰分明看見了手抖,抖得連碗都端不住。
那外按是很耗力氣的,救人的時候,用的不只是雙臂的力氣,整個上都在用力。一分鐘要上百次的按,還得勻著力,次次下達到五厘米,這樣高的頻率,尋常人撐兩三分鐘都要累個半死。
力竭了,就該大補。晏昰隔著一道墻,聽見唐夫人吩咐小廝“去灶房買點好克化的吃食”,那可真是隔著墻都替不痛快。
羊的脂全化進了菜里,片燉得爛,唐荼荼兩碗下肚,吃舒坦了,鼻頭沁出一層汗。
鍋里的香辛料包早早揀出來了,拿舌尖只能辨出黃醬和辣子的味道,微甜、微辣,鍋底鋪了一層綠珠,就是綠豆條,不配米飯饅頭吃也不覺得咸。
兩人坐在方桌兩側,你舀一碗我舀一碗,頭對頭安靜地吃,把鍋底的碎條都清了個干凈。
晏昰也不大敢說話,好幾次才張,又灰悻悻地合上了。沒法兒,右邊大屋里睡著唐老爺唐夫人,這薄泠泠的墻皮,連那屋的起夜聲都聽得著。
要是只有荼荼一人說話的靜,還能裝作是自言自語,可閨房里傳出男人的聲音,怕是又要“抓賊”了。
下了下飯,又催去睡。
唐荼荼瞄他一眼,喝杯茶潤嗓的工夫,又瞄了好幾眼,也沒見二哥有要走的意思,反倒在桌上攤開了文書,對著看起來。
“這是……漕司家的報?”唐荼荼頭回見這東西,著聲驚奇地問。
每一頁都是手錄的,字跡時有分別,像是不同的探子寫下的。也沒什麼條理,前一頁記吃喝宴飲,后一頁就是政事要聞,那一沓十來頁,不知道得看到什麼時候。
“去睡你的覺。”晏昰推推。
“轉運使司的邸,有你爹縣衙門的十倍大,沿河、沿海的外事堂更有無數,遠不是這麼幾張紙能看出名堂的。我大致看看,等你睡著了就走。”
唐荼荼還想再瞅兩眼,可惜字太小,困得眼皮打架,胳膊疼,手也疼,便不管那許多,合上里屋門躺回床上。
屋子小,里外間隔得局促,書桌又離門窗太近,晏昰為了不讓自個兒的影在窗紙上,只擺了一盞燭臺,手里翻著那沓報細看。
紙張薄脆,翻得再輕,總還是有靜的。
唐荼荼在這窸窸窣窣的響里,慢慢安下心來。
像上學時每一個自習的夜晚,無人說話,也無人吵鬧,窗口的月總是吝嗇的,頂燈暖暖地暈出一片。
唐荼荼支起半個,鬼使神差問。
“二哥,你是不是專門過來給我守夜的?”
睡覺之前,唐夫人也說要留個嬤嬤給守夜,唐荼荼一口回絕了,大概又是那些封建迷信的理由,當著母親的面上沒講,可心里是真的煩。
翻頁的聲音停了停,外間那人嗯了聲。
“噢。”唐荼荼著那簇燭:“我們學唯主義的,不信這個。”
晏昰極輕地笑了聲,目從牘上挪開。
他也不信什麼鬼鬼神神,人死如燈滅,半點不留痕。只是方才叁鷹說起來,說頭七不安穩,像巧鈴鐺這樣客死異鄉的魂沒去,更容易回魂,姑娘在的生死門上阻了一阻,保不準會被纏上。
晏昰聽完,心里一突,腳下便往這頭來了。
曉曉啊,能從后世來到千年前,如果說的到來是一場神跡,那他還是愿意信一信鬼神的。人之運勢,縷縷糾纏在一起,他真怕什麼神啊鬼的擋了的運。
他進過刑牢,也殺過人,山似的往這一坐,魑魅魍魎都不敢進這道門。
晏昰掖著這點話沒說,只說:“怕你夜里發噩夢。睡罷,二哥在這守著。”
唐荼荼安安穩穩躺下了,沒合帳簾,那一點燭從眼進夢里,睡得很香。
今日娘娘廟正祭,街巷間的更鼓比往時更,二更,三更,四更,聲聲敲過去。
天邊一魚肚白的時候,晏昰剪好燭燈的火舌,手剛上房門,回頭看看這屋里兩張凳、兩個茶杯、兩副碗筷,又立刻折回來。
他摞好鍋碗,收拾了筷,了桌,拾掇了廚余垃圾,把茶杯燙洗了,擺回茶盤里,不敢留下一點自己來過的痕跡。就怕清早進來個丫鬟喊姑娘起床,那必得陷。
要開門時,聽到院里有仆役醒了、趿著鞋子行走的聲音,晏昰又沒敢出去,留在房等了一等,端著鍋碗瓢盆,豎著耳聽外頭的靜。
等回過神來,他才留意到自己是個什麼姿勢,出門的時候眉頭都是擰著的。
晏昰怎麼也想不明白,他堂堂人中之龍,怎麼這兩年不是后門就是墻頭,翻墻的章程駕輕就?走唐家大門的回數加起來數不滿三手指頭。
猜你喜歡
-
完結140 章

公府嬌娘(重生)
顏熙去臨縣投靠舅父,被舅父舅母做主嫁給了衛家三郎衛轍。衛三郎生得豐神俊朗、英姿挺拓,猶若一朵長在雪巔的高嶺之花。雖然看著清冷孤傲不易親近,但顏熙卻一眼就相中。只是衛三郎不是真的衛三郎,而是京都長安城魏國公府世子。因失憶流落吉安縣,被衛家誤認…
51.5萬字8 22635 -
連載3516 章

醫毒雙絕:腹黑魔尊賴上門
她,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一朝魂穿!她成了沐家的廢物醜女大小姐,從此,廢物醜女變成了絕色頂級強者,煉丹!煉毒!煉器!陣法!禦獸!隨手拈來!神獸!神器!要多少有多少!可是誰能告訴她,這個人人談之色變,不近女色的魔尊,為什麼天天黏著她,還對她精心嗬護,體貼備至……
282.6萬字8.18 638211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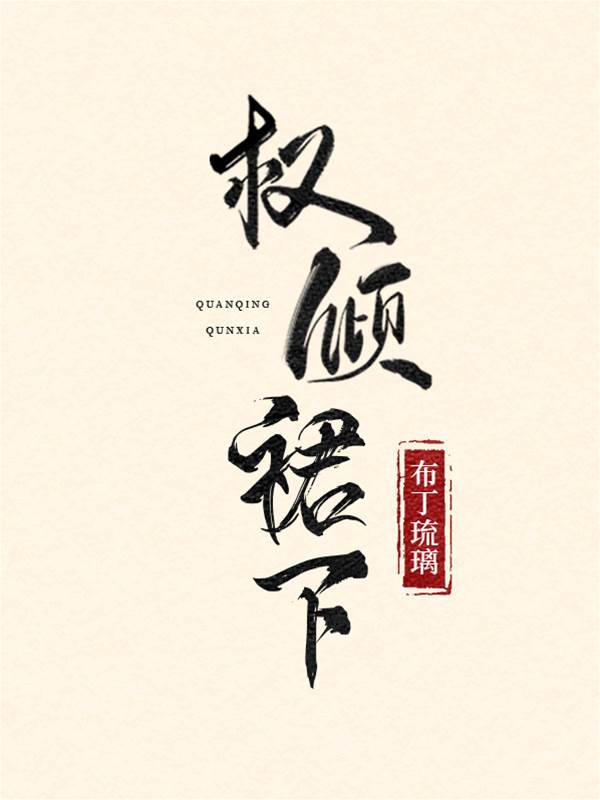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2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