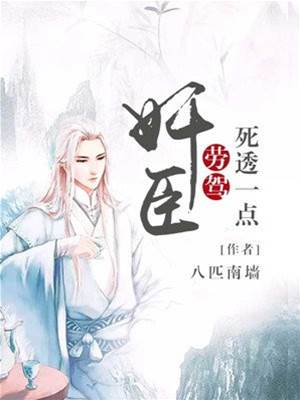《權傾裙下》 第21章 第21章 赴宴
三月初三,上巳節。
辰時,鳥雀的脆鳴先於晨醒來。
東宮寢殿門窗閉,水汽氤氳蒸騰,在樑上凝細晶瑩的水珠。
屏風后映出一道曲線玲瓏的影子,趙嫣一手從頸后攏起半乾的長發,出細白的頸項,一手按住前質地韌的素白綢布,一圈一圈轉著子慢慢纏繞勒。
纏了小半年的綢緞,這都快不是自己的了。然而天氣回暖,春衫日漸單薄,趙嫣毫不敢放鬆警惕。
「再些。」
趙嫣皺眉道,隨即被勒得一窒,好半晌才徐徐找到呼吸的間隙。
「祝酒後便無需太子出場,若流程走得快,則殿下只需忍耐半日。」
流螢伺候主子披上素白的中,遮蓋住那層層繃束縛的白綢,低眉道,「春夏最難熬,殿下苦了。」
是皇后親手教出來的宮婢,行事自然也和皇后一般只問結果,不在乎手段,難得說兩句己話。
「流螢,你真是越來越有人味了。」
趙嫣尚有心思逗弄,穿上緋紅的羅袍,將攏起的長發放下來道,「當初回宮前我便已做好了心理準備,如今都已經走到這一步了,難熬也得著。」
穿戴齊整出門,便見柳姬戴著帷帽立於廊中。
抬手起垂紗一角來,朝趙嫣道:「我要出宮,殿下將我也帶出去吧。」
柳姬雖有東宮令牌,但顧及朝中各派盯得,又有肅王那樣手眼通天的人在,是以行並不方便。若能藏在太子的車中一併出宮,便可省去這些麻煩。
趙嫣其實喜歡柳姬的子。
想什麼、做什麼都會直言說出來,且極有主見。譬如這會兒說的就不是詢問「能否將我也帶出宮」,而是拿定主意的「將我也帶出去」。
趙嫣也沒打探出宮去做什麼,「用人不疑」是太后祖母教的事之道。
Advertisement
簪花宴設在皇城以北的蓬萊苑,從東宮側門出發,拐個彎沿著宮牆外的夾道行兩刻鐘,便可抵達蓬萊門。
「你在何下車?」趙嫣問柳姬
柳姬開車帷看了眼,道:「就在此即可。」
說罷,戴好帷帽下了車。
趙嫣以指撥開車簾一角去,只見柳姬自永昌坊門而,在街邊鋪子隨意轉了轉,便沒了往來不絕的人群中。
趙嫣目送遠去,方吩咐孤星繼續馭車前行。
柳姬穿梭數條街道,漫無目的地閑逛了大半個時辰,直至確定後並無可疑之輩跟隨,這才進了大寧街的一家胭脂鋪子,從後門出,繞到了明德館的後院圍牆。
豪邁地提起邊往腰間一別,也不管出的里袴和小,稔地踩著那棵歪脖子棗樹,翻爬上圍牆。
賣豆花的小販挑著貨架路過,目瞪口呆地著大剌剌坐在牆頭的子。
柳姬腳踝的作一僵,將礙事的擺放下來蓋住,頭髮一甩兇道:「看什麼看!沒見過人幽會郎?」
說罷白眼一翻,跳進了明德館後院中。
牆上鳥雀驚飛,小販道了聲「世風日下」,搖頭走了。
柳姬抱臂躲在院角的假山後,皺眉等那群詩閑逛的酸腐儒生走了后,這才轉出來,徑直朝鏡鑒樓行去。
一路上東躲西藏,倒還真像個見不得人的茍且之輩。
上巳節明德館休假,儒生們要麼歸家探親,要麼結伴出門踏青,風雅點的還會尋個山清水秀之地曲觴流水,詩作對。故而此時閣樓空空,並無人值守。
柳姬踩著盤旋老舊的木樓梯而上,上了五層頂樓。
頂層是一間三面開窗的閣樓,因荒廢已久,未有人及時灑掃,閣中已落了一層厚厚的灰塵,使得案幾與木地板黯淡無,幾乎辨不出原有的。
Advertisement
陳年腐朽的氣息自四面八方包裹而來,柳姬抬手拂去頭頂一個碩大的蛛網,幾度握拳,方有勇氣重新踏這片蕭索的晦暗中。
蓮花燭臺傾倒在地,紙糊的燈罩破損得只剩下竹制骨架,彷彿一架白骨殘骸橫亙於地。
柳姬將燭臺扶起,指腹用力拂去案幾邊角的灰塵,只見筆鋒端正的「拂燈」一字現眼前。
去年此時的記憶如洪流湧現,儒生們圍著病弱溫的太子殿下談經論道的盛況歷歷在目。
他們渾然不知疲倦,累了就橫七豎八相枕而眠,有時睡夢中突然湧出一條極妙的點子,便蓬頭垢面爬起來筆疾書,直至晨熹微,方懷著莫大的滿足倒下。
那時閣樓的燈盞徹夜明亮,一如他們腔中的火種熱烈燃燒。
他們都以為長夜將盡,黎明就在眼前……
柳姬細眉一擰,拔下發間簪子,將案幾角落上的「拂燈」一字一點點劃破,切割,直至完全看不出原貌。
斂袖蹲下,撬開一塊空木板,將封存了近一年的件取出。
那是一卷捲軸,掌大。挑去繩結展開一角,眼先是一朵歪歪扭扭的花狀圖案,繼而是幾個筆各異的落款。
大玄太子趙衍,沈驚鳴,程寄行,王裕,還有柳……
柳姬沒有繼續看下去,將這沉甸甸的捲軸往懷中一塞,轉下了樓。
……
蓬萊苑是皇家花苑,佔地頗廣。
其由東自西開闢了大小十來園子,栽種著片的桃梨杏櫻等各花植,兼有山池林立,殿宇錯落,樓閣掩映於一片雲蒸霞蔚之中,好似人間仙境。
東宮車駕停在正門下,趙嫣踩著腳凳下車,忽的駐足了右眼,那顆細小淚痣被了艷麗的紅。
「殿下眼睛還是不舒服麼?」流螢關切。
Advertisement
「眼皮直跳。」趙嫣皺眉。
流螢去車上捧了個小袖爐出來,替熨在眼尾位道:「恐是殿下這幾日用眼過度,不曾休息好。」
「我還是覺得有哪裏不對。」
趙嫣想了想,吩咐一旁隨行的流螢,「待會兒宴上所有奉上來的酒水吃食,你都要私下驗過再呈上。還有爐中所用的熏香,也要換咱們自己的東西。」
「是。」
流螢回道,「已提前代過李浮了,席后,奴婢會再提醒他一遍。」
蓬萊苑的防備不如宮中嚴,宴上魚龍混雜,多點戒心總沒錯。
主僕正說著,忽聞徐徐的馬蹄聲由遠及近。
趙嫣手中還握著溫燙的袖爐,餘瞥去,只見斜生出宮牆的梨花下,聞人藺單手著韁繩馭馬而來。
大玄以玄紅一為尊,他今日亦穿的一紅底的常服,比袍款式更深,是鮮染就般的暗紅,既勾勒出他肩闊長的矯健形,也襯得他的面容比平日更加霜白清俊。
是了,父皇讓他在宴上挑選合眼緣的貴,自然要穿得打眼些。
趙嫣側避開視線。昨日收到了華來的回信,是時蘭以「長風公主」的名義寫來的,說是謝宮中來使掛念,太後娘娘在華行宮一切安好……
這信寫得委婉,暗指確實有人在暗中打探華的事。
聞人藺近來神出鬼沒,不知在醞釀什麼謀。再聯想他三番五次提及「長風公主」,趙嫣猜想他不會善罷甘休。
難怪從昨日起,這眼皮便跳個不停。
思索間聞人藺已翻下馬,朝這邊走來。梨白如雪,在他靴旁翻飛。
趙嫣不著痕跡地轉了個,迎向剛落轎的周及。
「周侍講來得正好。昨日所學的簪花禮節,孤尚有一不太確定,還請先生不吝賜教。」
Advertisement
說罷,從侍從奉來的托盤中取了一朵層疊綻放的十八學士①。
如此,便自然巧妙地避開了與聞人藺撞上。
聞人藺腳步未停。
小太子素來打扮雅凈,常服以雪、杏白居多,今日卻難得穿了一襲淺緋的羅袍,鮮麗的讓其整個人都明亮起來,連眼尾的淚痣都帶了幾分艷。
而此時,頗為勤勉地捧著一朵層疊綻放的白茶,據周及的提點不斷調整姿勢,眉眼間儘是淺淺笑意。
「十八學士」的花瓣與的指尖相比,竟不知哪樣更為潔白。
聞人藺只掃了一眼,便收回了視線,緩步越過那言笑晏晏的兩人,上了石階。
他這一趟,可不是為太子而來的,沒心逗貓。
帶起的涼風轉瞬即逝。
趙嫣聞到了聞人藺上那極淡的木香,還夾雜著一之前未曾嗅過的氣息,像是……嚴冬時節冰雪的清寒。
「殿下?」周及喚了聲。
趙嫣回神,糊弄道:「多謝周侍講,孤已記住了。」
「利用」完周及就走,似乎也不太夠意思,便將手中的白茶遞了過去:「這個,就當酬謝先生。」
簪花宴,儲君賜花乃是莫大的恩賞,不可拒絕。
周及便手接了,道了聲:「多謝殿下。」
那朵白茶躺在他溫潤的指間,倒也與他的氣質頗為般配。
趙嫣滿意離去。
周及看著輕鬆的背影,腦中浮現出悉的一幕。
華行宮桃花如霞,靈艷的隨手摺了一枝蓓蕾遞過來:「春正好,悶在書房中實在可惜。小周先生不要這般固執嘛,送給你!」
微風青衫,周及對猝然浮出的記憶到疑。
明明聲音截然不同,子也天差地別,他為何會覺得眼前之人仿若舊識?
看來自己這臉盲之癥,是越發嚴重了。
趙嫣沒料到,前來赴宴的眷還多。
除了各家選送上來的未婚貴,閑來無事的後宮娘娘也聚集在東北角的攬芳閣中,登高賞花,遠眺盛景。
趙嫣一經出現,席上眾人的目便紛紛投過來。
在一眾青藍袍服的恩科進士中,東宮太子那緋綉金的羅袍便格外搶眼,更遑論他還生有一張禍水般雌雄莫辨的臉!
如此出的容貌,縱觀全席男子,也就肅王能勝一籌。
但肅王位高權重,喜怒無常,並非容易接近之人。貴們多父母長輩訓導過,自然不會傻到以飼虎。方才郭尚書家那個不自量力的兒鼓起勇氣去「偶遇」肅王,也不知在畫橋上,那肅王淺笑著與說了句什麼,郭家嫡不一會兒就哭著回來了,手腳冰冷抖,宛若失魂……
們看在眼裏,便徹底絕了不該有的心思。
但太子殿下不一樣。
他矜貴漂亮,見之可親,量纖弱而不萎靡,是極能激起子心中母與憐惜的。
年紀小算得了什麼問題?姐姐們可以!
貴們正是懷春的年紀,縱是有帷帽垂紗遮面,也難掩臉紅心跳。
趙元煜站在門的影下,看著遠盡人青睞的太子,刻薄的臉也染上濃重的暗。
「那賤-人怎麼還沒來?趕把東西呈上去!」
他幾乎咬著槽牙催促,迫不及待要將趙衍拉下神壇,連同東宮的尊嚴一起踏爛泥。
小太監不敢違逆,打著飛腳跑去傳話。
另一邊,趙嫣耐著子,含笑同每一個前來跪拜問禮的恩科進士點頭致意。
禮部冗長的開場辭過後,終於捱到了賜簪花的流程。
兩排宮魚貫而,奉上托盤中早已準備妥當的金銀絨花。
按照大玄舊制,狀元、榜眼、探花賜金葉絨花,其餘進士則賜銀葉絨花。太子當親自將花簪於他們的紗帽一側以示聖恩,連用何姿勢拿花,用何角度簪花亦有嚴格的規定。
趙嫣捻起狀元的金葉絨花。
這花極為巧細緻,仔細嗅來,連香味也做得十分真。
趙嫣並未多想,按禮制將花別在了那年紀能當爹的狀元郎帽上。
狀元郎激涕零,三跪九叩方退下。
好不容易賜完了花,還未到開宴的時辰,禮部便呈上清雅的舞樂以供新貴們消遣。趙嫣部悶得慌,便去廊下尋了個涼之氣。
一旁,按捺了許久的貴們你推推我,我瞅瞅你,俱是三五結伴地湊了過來。
有幾個膽子大的,直接大大方方開了口。
「太子殿下,請給我們也賜朵花吧。」
「是呀是呀!殿下哪怕賞草,也是臣們莫大的榮耀啦。」
聞人藺從曲水蜿蜒的廊橋上下來,見到的便是這番熱鬧場面。
小太子被一群鶯鶯燕燕簇擁著,正將新採摘的各花卉贈予們。那副興緻盎然的模樣,全然樂在其中。
聞人藺腳步一轉,朝們行去。
熱鬧的歡笑聲戛然而止,連燥暖的風也停滯下來。
趙嫣抬首,微彎的眼眸在見到信步而來的聞人藺時一滯。
有了郭尚書家嫡的前車之鑒,眾貴見到容貌俊的殺神款款而來,俱是以他為中心飛速撤離。
一名年紀稍小的站在原地,竟是看呆忘了反應。姐姐咬向前,將猛地扯了回來。
聞人藺對們的識趣頗為滿意。
他將視線落在趙嫣上,看了半晌,無甚溫度道:「殿下這花,倒是送得勤快。」
趙嫣可不信他是專程來話家常的。
不過是樂於摧毀的興緻,眾人的慄罷了。
宮人採摘來的玉英已基本贈完,只餘一支早開的榴花孤零零躺在石桌上。
「替父皇賜花恩賞臣民,是孤的職責。」
趙嫣心緒一,順勢捻起那支榴花遞出,仰首乖順道,「這支,是給太傅準備的。」
這話茬接得巧妙。聞人藺的視線從的瓣下移,落在那枝同樣鮮妍的榴花上。
花影扶疏,他們一個負手立,一個筆直端坐;一個殷袍如,一個緋明亮。
賜花是對忠臣良將的恩賞,賜者是君,者是臣。
可惜,他既非忠臣,也非良將。君臣的份之別,約束不了他分毫。
「殿下有心了。」
聞人藺接過了榴花,指腹漫不經心捻了捻。
花枝在指間轉了一圈,聞人藺嗅到了極淺的、屬於榴花之外的一縷清香。
有些違和,他眸微凝。
「王爺。」張滄朝聞人藺一抱拳,似有話稟告。
聞人藺將花枝負於後,朝趙嫣略一頷首,走了。
火紅的榴花在他指間輕輕轉,那霜雪般蒼白修長的指節,便染了花的艷。
浮雲飄散,暖重新傾瀉,趙嫣的視線晃了晃。
忙撐著腦袋,吐出一口熱氣。
「殿下怎麼了?」流螢第一時間扶住。
「有點頭暈。」趙嫣道。
流螢抬頭看了眼燥暖的日頭,低聲道:「許是悶著了,奴婢扶您去拾翠殿歇息片刻。」
拾翠殿並不遠,趙嫣躺在小榻上,頭昏腦漲的覺並未減輕。
以為是束太,不上氣才導致暈眩,便道:「去和禮部打聲招呼,開宴祝酒的事孤許是趕不上了,讓他們自己看著辦。」
流螢見面實在不對,且祝酒也非什麼必不可的流程,便頷首道:「殿下在此稍候片刻,奴婢去安排。」
自明化年間發生親王帶侍衛宮,於宴上行刺皇帝的事以來,宮中便下令:除武將卸甲解刀宮述職,可領一名副將隨行外,其餘人不管王爺世子,皆不可攜侍衛家將宮。
是故連孤星也只能於蓬萊苑宮門外候著。
人手不夠,流螢只能去找侍傳話。
然而四下空無一人,再等下去恐殿下撐不住。略一皺眉,沿著花林掩映的小道朝不遠的宴席行去。
猜你喜歡
-
完結3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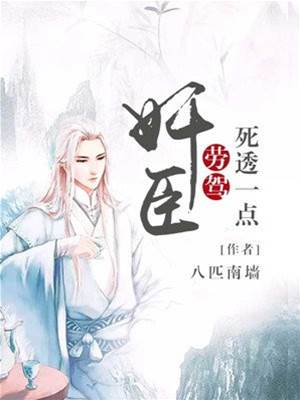
奸臣,勞駕死透一點
蘇問春五歲時撿回來一個臟兮兮的小乞丐,十年后小乞丐踩著蘇家步步高升。春風得意之際,蘇問春伏在他腳邊求他為蘇家討個公道,只得他兩個字:活該!后來蘇問春受盡酷刑著牙闖出一條血路終得平反。兩人尊卑顛倒,他一身囚衣坐在死牢,卻是一臉繾綣:“不是一直…
70.1萬字8 6505 -
完結823 章
棄妃無雙
天道好輪迴! 長平伯府那臭名昭著水性楊花的歹毒小姐,要嫁給困頓落魄到不得不入贅的鄰國質子,滿京城誰人不道一句般配! 質子私逃,伯府獲罪,惡小姐被沒入掖庭宮中為奴,拍手稱快者數不勝數! 可一轉眼,這惡小姐竟搖身一變,改嫁新帝,憑藉不知什麼狐媚手段,當上了一國貴妃,手握鳳印,執掌六宮。 再轉眼,新貴妃清君側有功,母儀天下!
111.8萬字8 7342 -
完結198 章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200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