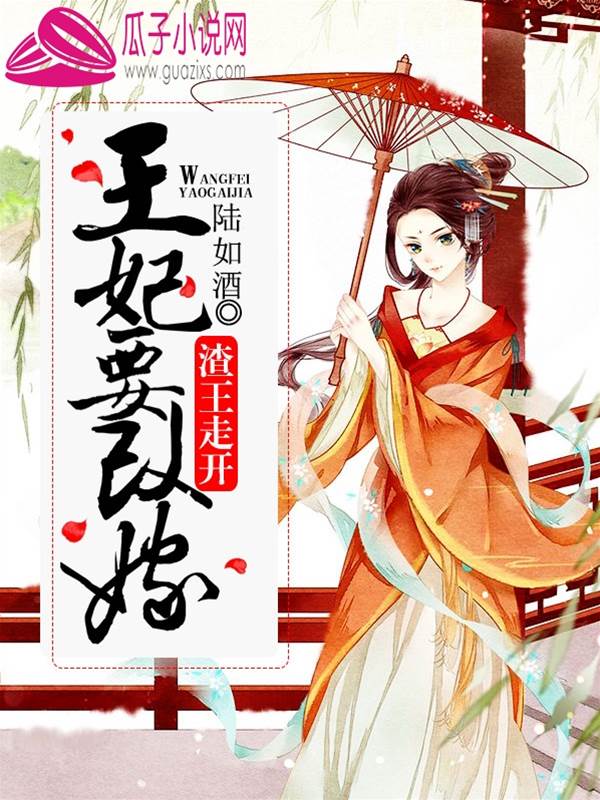《月明千里(嫁給一個和尚)》 第 201 章 海都阿陵番外(作話還有)
“海都阿陵!”
驚怒的質問聲四起,席間眾酋長發出憤怒的咆哮,埋伏在角落裏的親隨同時拔刀暴起,影如鬼魅,一陣寒閃爍,鮮噴灑,剛剛還在怒吼的酋長轉眼首異,一顆顆頭顱在氈毯上滾,大睜著的雙眸猙獰可怖。
“啊——”
帳中服侍眾酋長的奴嚇得大不止。
海都阿陵皺了皺眉,眼神示意托木倫把奴們拖出去,鷹眸抬起,淡淡地掃視一圈。
“你們降還是不降?”
十幾個酋長當場死了六個,親隨手中站滿鮮的長刀就在眼皮底下,其他酋長魂飛魄散,咬了咬牙,怒吼:“海都阿陵,就算你今天殺我們也沒用,我們的部族會為我們報仇雪恨!”
海都阿陵不屑地嗤笑:“就憑你們這幾個小部落,也敢和北戎為敵?今天我可以輕而易舉地殺你們,明天我就能帶兵踏平你們所有人的部落。”
他話音剛落,帳簾掀開,兩個士兵抬著一隻箱子進帳,打開箱蓋,倒出裏麵的東西。
咕咚幾聲,一顆頭顱滾到了剛才怒吼的那個酋長麵前。
酋長認出頭顱正是自己部落最勇猛的勇士,心膽俱裂。
眾人心中暗恨,明白他們中了海都阿陵的計策,他把他們引來營地,趁機派兵襲了他們的部落,他們已經失去和海都阿陵談判的籌碼。
砰的一聲響,一名酋長扔下手中的佩刀,單膝跪地,其他酋長對一眼,無奈地歎口氣,也跟著做出臣服的作。
海都阿陵哈哈大笑,站起,扶起最先跪地的酋長。
瑤英和其他人一起退出大帳。
等眾酋長離開,托木倫勸說海都阿陵:“王子何必要殺那幾個酋長?這些小部落欺怕,隻要以兵力震懾,他們就不敢不聽從王子的號令。殺了人,隻怕他們麵服心不服。”
Advertisement
海都阿陵冷笑:“你沒聽說?這幾個部落已經有人改信佛道了。”
托木倫不解地說:“伊州也有不人改信佛道,連牙帳的幾位大妃也供起了佛。”
海都阿陵聲音發沉:“連你也知道大妃改吃齋念佛了,北戎到底貴族有多人開始念經?別以為這些稀鬆平常,現在不加以遏製,假以時日,北戎士兵中有一半信佛,攻打王庭時,那位傳說中阿難陀再世的佛子親臨戰場,誰還敢衝鋒陷陣?”
托木倫半晌沒吭聲。
海都阿陵接著道:“我勸過大汗,以後誰敢在軍中散播佛子的事跡,立刻以妖言眾為名斬首示眾,以震懾人心,大汗沒有當回事。行軍打仗,不僅要靠排兵布陣,靠良的武備,靠有利的地形,還看士氣軍心,他們把王庭佛子當神,和神對敵,軍心怎麽穩固?”
托木倫睜大眼睛:“大汗當年敗給佛子,軍中就傳出流言,說佛子得神佛庇佑,所以才能奇跡地以勝多。這次大汗集結兵力再次圍攻王庭,還是久攻不下……”
海都阿陵冷笑:“這一次流言會比以前更猖狂,屆時必定軍心,大汗這一次圍攻王庭,勝算不大。”
如果瓦罕可汗早點聽從他的建議,曇羅伽的名聲不會流傳得這麽廣,現在瓦罕可汗自己對那些傳說將信將疑,麵對曇羅伽時瞻前顧後,王庭坐擁地利,士兵百姓信仰虔誠,佛子一聲令下,刀山火海他們也能往前衝,瓦罕可汗必敗。
他沒有可汗的那些顧慮,他的軍隊不允許出現任何一個懼怕佛子威名的士兵,他要訓練出一支強悍的隊伍,打敗王庭,樹立威。
北戎人崇拜強者,鄙視弱者,讓瓦罕可汗束手無策的敵人敗於他手,他才有資格去競爭下一任大汗。
Advertisement
一場風波來得快,平息得也快。
等隊伍出發時,部落酋長們跟在海都阿陵後麵,態度恭敬,已不複前些時日的囂張跋扈。
他們朝伊州行進,海都阿陵忙著收服各個部落,暫時放鬆對瑤英的折磨,終於找到機會暗中和謝青他們聯係,他們還在養傷,叮囑他們別輕舉妄。
期間,海都阿陵親自監督了一場行刑,托木倫從被殺的幾個士兵帳中搜出佛經,將他們斬首示眾。
瑤英被帶到刑場觀刑,鮮濺到上的上,抖了幾下,麵發白。
海都阿陵滿意地看到臉上出懼怕的神。
跟在他後回帳,還在微微發抖,腦海裏卻騰起一道亮。
海都阿陵雖然殘暴,卻很護他手底下的士兵,不會無緣無故重罰士兵,他為什麽要殺私藏佛經的士兵?
想起一個名字。
曇羅伽。
和親兵勢單力薄,不可能越過層層封鎖逃回中原,唯有先找一個海都阿陵的勢力進不了的地方——瓦罕可汗和其他王子是最佳人選,但是他們和海都阿陵並沒有什麽不同,投靠他們不過是從虎坑逃到狼窩。
還有一個選擇:王庭。
海都阿陵絕不敢帶兵去王庭抓捕。
第3章
穿過寸草不生、飛鳥走蹤跡全無的瀚海沙漠後,離伊州越來越近。
這日,他們抵達一北戎部落,修整了兩天,海都阿陵突然下令隊伍讓改道往北,而不是按照原來的行程直接回伊州。
他選出兩支輕騎隊伍押送一部分俘虜去伊州。
托木倫調派人手時遇到一個難題:“王子,該怎麽安置文昭公主?屬下派幾個妥當人先送回伊州?”
海都阿陵著案上的輿圖,推演兩軍對戰,漫不經心地點點頭。
Advertisement
托木倫替瑤英鬆了口氣,轉往帳門走去。
海都阿陵放下羊皮紙輿圖,目落到牛皮帳篷上懸掛的一張毯上。
那是李瑤英親手織的。
跟著奴撿馬糞,織氈,用馬尾做韁繩,鞣製皮革,熬煮牛羊、馬腸,每樣活計都學得很快,而且做得像模像樣,還在織氈時想出了好幾個新花樣,教給其他奴。
北戎人織出來的氈比的紮實,但是沒有的漂亮巧。
親手織的氈毯送到他帳中,心裏肯定很不樂意,早上過來打掃大帳的時候,看到氈毯,臉立刻冷了下來。
想到氣得咬牙又不得不克製怒火的模樣,海都阿陵不嗤笑一聲。
托木倫掀起氈簾,人已經走出大帳,後忽然傳來海都阿陵的聲音。
“留下。”
托木倫暗歎一聲,回頭應是,言又止。
王子強壯勇猛,是北戎第一勇士,征戰從無敗績,想要什麽人都能輕易得到。
他打算像馴服阿布那樣馴服公主,可是公主是個人,還是個人。
人不是雛鷹。
……
瑤英在原野牧羊。
天朗氣清,豔高照。遠巍峨的皚皚雪山如銀冠聳立,天氣轉暖,冰川漸漸融化,草甸峽穀間壑縱橫,河水嘩啦啦流淌,藍寶石般清澈的湖水鑲嵌在峭壁河穀之間,藍天白雲和爛漫山花倒映其中,好似一幅壯瑰麗的畫卷。
山腳下是一片茫茫無際的千裏草場,草木旺盛生長,層層綠浪翻卷,浪頭綿延至天際,和蒼茫的山脊融為一,五六的絢爛野花點綴其間,風過,送來一縷縷潑辣的花香和牧草的腥氣,展眼去,汪洋花海,不勝收。
雪白的羊群悠閑地吃著草。
瑤英騎著馬從織錦繁花的草原飛馳而過,頭梳辮發,一北戎子常穿的翻領窄袖長袍,腰間束帶,勒出纖娜的腰肢線條,馬駒通墨黑,襯得上袍赤紅如火,愈發的明豔照人。
Advertisement
迎麵的風清新何爽,花香沁人心脾。
瑤英夾馬腹,手中長鞭揮出,指揮羊群去河邊飲水。
周圍的北戎人著馬上燦若雲霞的瑤英,忍不住嘖嘖稱歎,拍手好。
瑤英笑著和他們打招呼。
北戎人送上清冽甘甜的泉水,笑著道謝,接過皮囊,坐在馬背上,咕咚咕咚幾口喝完。
送水的年呆呆地看著,周圍的人發出善意的哄笑,年紅著臉跑開。
人們笑得更大聲。
瑤英角輕翹。
自從上次大病一場後,海都阿陵命服侍他的起居,不再讓去伺候其他人,也不會不人把捆起來。
塔麗給出主意:“公主,您不用去做那些活,隻要服侍好王子就夠了,織氈的活計吩咐我們就行。”
瑤英的份依然是奴,但是現在營地沒人敢支使做什麽。
在塔麗和北戎人看來,海都阿陵對已經很容忍了。
瑤英一哂。
海都阿陵確實看似放鬆了對的看守,實則暗暗派了幾個胡日夜盯著。
他知道該怎麽在雛鷹熬不住時適時地給出一點甜頭,讓雛鷹認他為主,對他死心塌地。
瑤英和那些飽折磨的雛鷹一樣,每天都很累,提心吊膽和海都阿陵周旋就幾乎耗費的全部心力,還得幹活,得想辦法吃飽肚子,得在他眼皮底下籌劃逃跑。
有時候,也會詫異海都阿陵的耐心。
揚鞭在草原上縱馬飛馳時,有那麽幾個瞬間,甚至會忘記現在陷囹圄的境,以為自己就像在長安時那樣,正和李仲虔在遼闊的樂遊原上肆意馳騁。
但是心底那道聲音始終清晰響亮:是被海都阿陵抓來的,要回去,不會在被海都阿陵折磨之後因為一點小恩小惠就搖。
塔麗以為每天和其他北戎人一起牧羊、編繩,已經徹底融北戎部落,決定服從海都阿陵,其實在暗中打聽消息,觀察海都阿陵的部下,尋找的機會,順便麻痹海都阿陵。
據說瓦罕可汗正帶兵攻打王庭,海都阿陵會不會奔赴戰場助他義父一臂之力?
瑤英思索著這個可能,任由黑馬啃食地上的青草,忽然覺得周圍安靜得古怪,抬起頭,正好撞進一道凝視的目。
一個高大朗的男人倚在柵欄前,辮發高束,五廓分明,皮獵裝勾勒出健壯形,看去意態閑適,卻帶著兇悍威嚴的殺氣,淡金的眸子冷漠無,沒有一屬於人的溫和,像在暗等待時機的狼,隻有森冷的。
他看著瑤英,示意剛才遞水囊給的年走到他跟前去回話,臉上沒什麽表。
周圍的北戎人大氣不敢出一聲,垂首侍立。
年嚇得臉發白,哆哆嗦嗦著朝他走去。
瑤英韁繩,心跳飛快,張得忘了呼吸。
這個年暗中幫給謝青他們傳遞口信,每次送水不過是掩人耳目而已——海都阿陵是不是看出來了?
海都阿陵和年說話,視線仍然一直停在上,不敢彈,背上沁出冷汗。
過了好一會兒,年把水囊獻給海都阿陵,向他行禮,恭敬地退開。
海都阿陵朝瑤英招招手。
瑤英骨悚然,爬下馬背,一步步朝他走過去。
海都阿陵看著,眼神如刀,拍拍手中水囊:“原來公主喜歡這樣的?”
瑤英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試探還是隨便找個借口來奚落自己,鎮定地道:“他才十一歲!隻是給我送水而已。”
海都阿陵笑笑。
是啊,年才十一歲。
但是他不喜歡這樣。
他隨手把水囊扔到地上,轉:“跟我來。”
看來他沒有懷疑年。
瑤英悄悄地舒口氣,舉步跟上他,以後不能再讓年幫忙傳話,雖然傳的話無關要,被抓住也沒什麽,但不能高估海都阿陵的仁慈。
海都阿陵帶著回到大帳。
托木倫也在帳中,指指地上一堆淩擺放的箱書畫和珠寶瓷,問:“公主認得出這些東西嗎?”
瑤英看了看,指著最底下一隻圓盤道:“這平盤是聖人頒給葉魯部的賞賜。”
托木倫忙把平盤取出來,“公主,這裏哪些是最貴重的寶?哪些適合送人?要又雅致又貴重的。”
瑤英會意,點點頭。
海都阿陵這次從中原和各個部落劫掠了不寶,但是他的部下隻認那些金燦燦的,其他貴重珠寶就辨認不出分別了。現在他回到北戎,肯定要給貴人們送禮,還得把劫掠來的寶進獻給瓦罕可汗,所以把來辨認,好決定哪些送人、哪些私自扣下。
不聲,幫著清點寶,不管是字畫還是珠寶,都能說出由來。
托木倫領著人在旁邊記錄。
海都阿陵斜倚案前,長支起,一手搭在上,一手舉著酒碗,目在滿帳寶間打轉,最後不知不覺落定在瑤英上。
是高貴的公主,是謝家養大的貴,什麽奇珍異寶都見過了,讓幫忙辨認古董本難不倒。
而他和部下隻知道鑲金的珠寶值錢。
他在蠻荒中長大,靠掠奪為生,飽讀詩書,一舉手一投足都像一幅的畫。
李瑤英心裏肯定瞧不起他,覺得他俗野蠻。
海都阿陵不由得想起剛才在草原上奔馳的模樣,笑容燦爛,鮮活明,讓人不敢視。
在他麵前,絕不敢出張揚豔麗的那一麵。提防他,厭惡他,想離他越遠越好,他隻要靠近一點,馬上會嚇得跳起來,或是假裝若無其事,其實在瑟瑟發抖。每次不得不來大帳服侍他時,腳步沉重,恨不能一步三挪,當他揮揮手要離開的時候,就像甩下千鈞重擔一樣,腳步都輕快了。
海都阿陵的恐懼和絕。
高高在上,可不可即,他偏要把扯下來,讓沉淪在泥沼中,徹底臣服於自己。
年時,他偶爾發現鷹巢,冒著碎骨的危險爬上懸崖,和老鷹搏鬥,終於抓來一窩雛鷹。強壯的鷹被其他王子搶走了,阿布奄奄一息,沒人看得上,他救下阿布,悉心把它養大,讓它為北戎最雄壯的神鷹。
訓練以折磨為開端,阿布很倔強,最後還是被他馴服。
時至今日,海都阿陵還記得第一次指揮阿布完狩獵時那種難以言喻的快。
見到李瑤英的第一眼,他覺到了類似的衝和征服,後來也確實從的反抗中到了愉悅。
然而最近,他心裏慢慢生出一種不滿。
他發現自己不再滿足於這種貓抓老鼠似的遊戲。
……
幫海都阿陵辨認珠寶古董後,瑤英注意到陸陸續續有輕騎護送幾口大箱子去了不同方向。
暗暗觀察托木倫,比對箱籠,很快瞧出端倪:最貴重的寶並沒有被送走,而是留在營地。
看來海都阿陵並不打算把所有寶出。
記下這一點。
禮送出後,隊伍繼續往北走。
天氣越來越暖和,幾個膀大腰圓的胡天天守著瑤英,擔心連累其他人,沒再和那個送水的年說過話。
這天,坐在帳中編繩,士兵挑開氈簾:“王子要你去大帳!”
瑤英咬牙站起。
大帳前麻麻站滿了人,看甲都不是海都阿陵的部下,帳中歌舞喧天,時不時傳出一陣哄笑。
瑤英低著頭走進大帳,還沒看清帳中形,長席後的一人指著道:“就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450 章
替嫁棄妃覆天下
問女子的容顏能有多值錢?她是先帝親點的皇后,卻在顏容半毀時被一紙圣旨從后變妃。一旨雙嫁,絕色的妹妹代她入宮為后,而她遠嫁給那少年封王,權傾朝野,冷酷殘暴的雪親王……新婚夜,他說她的容顏只配呆在馬廄里,雖有王妃之名卻只能任人奚落…他中毒命在旦夕,她不顧一切救他,只為讓自己活有尊嚴……以妻子這名,行幕僚之實她伴......類小說,情節引人入勝,非常推薦。
353.4萬字8 121608 -
連載214 章
穿成侯府通房丫鬟后,我擺爛了
秋錦穿越了,穿成被送去當通房,而被拒絕打了回來的小丫鬟。 因長相貌美,算卦老先生說她命中帶福,老夫人將秋錦送給混世魔王嫡長孫小郎君當通房,希望旺旺嫡長孫
37.8萬字8 10786 -
完結301 章

昭鸞
虞昭是聞名于世的東楚第一美人,縱使兩國交戰數年,依舊美名遠播。她本有一樁人人稱羨的美滿姻緣,卻在大婚前被至親出賣,奉旨和親敵國,為宗族換來潑天榮華富貴。初聞消息時,虞昭慘白了面容,她要嫁的人是敵國太子蕭胤。對方龍章鳳姿、戰功赫赫,此前大敗東楚之戰便是由他領兵。新婚當晚,蕭胤以朝務忙碌為由,宿在書房一夜不見人影。虞昭等了許久便倦了,拉過赤錦喜被蓋在了身上。翌日,蕭胤終于見到虞昭的真容。他發覺自己在新婚夜丟下的太子妃,此刻一副睡飽了的模樣,不禁眼底微深。后來,蕭胤將她堵在墻角,試圖履行夫妻“義務”。他望見虞昭哭紅的眼,以及那紅艷的菱唇,既不忍心傷她,唯有放軟姿態,嗓音暗啞道:“孤哪兒不如你那個未婚夫了,你說說。”
46.2萬字8 12326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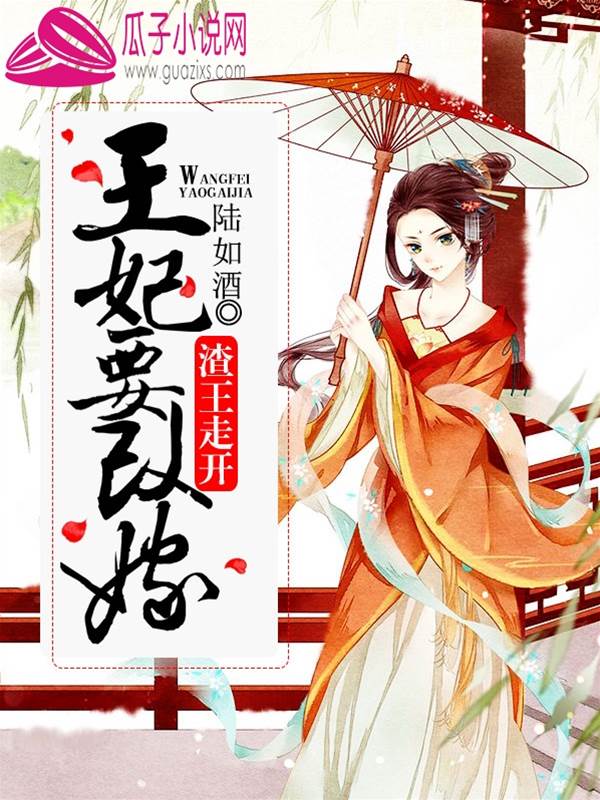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29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