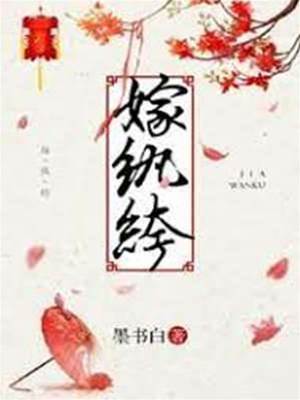《縛春情》 第277章 別院
“尋常人傷了底子不好理,可你是一國之君,東寧最好的醫者俱供你差遣,又怎會醫治不好你上的舊患?”
宋挽走到沈千聿邊,拉著他的手聲道:“往日你子執拗,又不耐配合太醫以針灸藥膳調養。如今年歲上來,倒知這事嚴重了?”
宋挽打趣道:“刀子不落在自己的皮上,終歸是不知疼的。”
“自今日起,我讓許太醫為你日日施針,讓傅太醫為你製定藥膳,如此將養上幾年總能好上大半。”
“會嗎?”
“自然。”
拉著沈千聿的手,宋挽垂眸:“有生必有死,壽數這東西強求不來,你放寬心思,不要日日汲汲於壽數一事。”
早年他在南慶時子虧得厲害,涑河一戰又添不新傷,這幾年他不適的癥狀愈發明顯,看在心裏亦為此焦急。
可宋挽知曉人之生老病死既無可避免,亦不能逃,因此並不執著於讓沈千聿去謀什麽長生之道。
“與其日日擔憂自己的子,不若放開心中憂思,還心自在。”
“人自在了,子也會好上大半。”
幫沈千聿將前了褶皺的衫一點點展開,笑道:“且我知你心疼我,不會舍得丟我一人先行離去,所以我從不擔心這些,你也無需擔心。”
沈千聿膽小又是個粘人的子,這幾年對愈發魔怔了,一時片刻不見便要整個後宮裏去尋。
想著他那模樣,宋挽心生酸,卻是疼惜更甚。
他年時候無人關心無人疼,堅韌自強,哪知人至不反愈發生了孩心。
偶爾甚至覺得對方比沈時晏、沈時驍更似孩。
“我不會的,今生我絕不會丟下挽兒先行撒手。”
這話說完,沈千聿心中好似撐起一子勁來,不再像往日那般懨懨無力。
Advertisement
“我這一生認準了的事便沒有做不到的,挽兒且看著,我定能撐著走在你後頭。”
沈千聿站起,仿似回到年在南慶孤立無援時候。
他就是那等前路越艱難,愈生鬥誌之人。
自這日起,沈千聿日日聽從宋挽安排,早晚讓太醫施針醫治雙膝,吃食也多以溫補藥膳為主。
也不知是太醫的調養起了作用,還是他心中有了可支撐自己的那子氣神,沈千聿的子竟真漸漸朗起來。
沈時晏十歲出頭時,沈千聿便一直將他帶在邊培養。如今沈時晏剛剛及冠,他便急急禪位於子,自己安心做起了太上皇。
新皇登基那日,最為高興的並非沈時晏,而是終得自由的沈千聿。
“吾之一生責任盡矣,自今日起終可安心同挽兒度日,聞人間煙火,品五穀雜糧,做極樂逍遙之人。”
將長樂宮榻之上用慣了的枕丟箱籠中,沈千聿又手去摘床上掛著帷幔。
宋挽瞧著他的作無奈開口:“這件你摘了作何用?那別院位置窄,它同屋中的拔步床尺寸亦不合,便是拿了過去也用不得。”
“無妨,我裁剪裁剪。”
“母後由著父皇去罷,父皇終將肩頭擔子卸下,如今正在興頭上。”
“驍兒說得有理。”
沈時驍麵上帶著淺笑,站在一旁看著他父皇忙碌。
他如今已長翩翩年,單隻站在那便令人之靜心。他雖年輕,但在他上甚能到年人的意氣風發與風流得意。
沈千聿常說沈時驍隨了宋挽,年紀輕輕便被書香氣醃到骨子裏。
“皇兄到如今還未來,想是心中正委屈著。”
“為兄不在,你便在父皇母後麵前編排起為兄來了?”
沈時晏自屋外而進,抱著手臂倚在一旁。
Advertisement
他長玉立,形高挑,竟是比沈千聿還要高出半掌。
商蓉曾說們幾人合力培養出的孩兒,應是個頭角崢嶸朝氣蓬之人,哪想沈時晏越長,越著一子沈千聿年輕時才有的邪佞勁兒。
年時還好,待到登基後,他眸中多幽冷淩厲,同兒時大不相同,甚是駭人。
趙南璋曾言這是天生的帝王相,宋挽卻覺得趙南璋太過疼晏兒,以至於瞧他就沒有不好的地方。
“皇兄難道不曾委屈?”
沈時驍微微一笑,沈時晏見狀輕哼一聲。
他父皇同母後一心要搬出皇宮到別院生活,還是他無論如何都不肯,又在後宮偏僻開了個相對安靜的院子,且勸了許久,二人方決定留在宮中養老。
沈時晏知曉父皇是為徹底讓權。
父皇既已離開權力巔峰便再無手朝政之意,也是想讓他安心做一個帝王。
可對沈時晏來說,他是帝王,也是父皇母後的孩兒,這帝王份如何能敵得住骨親?
思及此,沈時晏道:“自是委屈,可想著委屈也得不到父皇疼惜,便隻能將這份委屈咽下,暗自神傷。”
沈千聿收整箱籠的手一頓,回頭嫌惡地看了一眼沈時晏。
沈時晏同沈時驍見狀,二人頓時笑了起來。
他們向來兄弟深,二人長至這般大從未生過任何嫌隙。
沈時晏不願沈千聿二人搬離皇宮,自也有不舍弟弟同萬宵,以及後宮裏頭的幾個老太妃的意思。
他兄弟二人是這些人一齊看著長大的,若都去了別宮,他便真孤家寡人一個了。
父皇母後留在皇宮,他便有種一家未散的覺。
誰說帝王無?
若讓他來說,皇家同樣也有重之人。
將東西搬往小院,沈千聿牽著宋挽的手悠悠走在後頭。
Advertisement
小院裏頭為商蓉沈時晏、沈時驍等人都留了屋子,可能與他們長住的,怕是隻有萬宵吉榮以及蘅芷了。
“微臣見過……”
剛一進小院,萬宵同吉榮便要下跪行禮,沈時晏快步上前將二人扶了起來。
“您二老這禮我可不起。”
他同沈時驍是在這二人掌心裏寵大的,亦師亦友亦主亦仆,如何能承他二老的禮?
吉榮還想再跪,沈千聿道:“在這院中,這些個繁文縟節便免了罷。”
都一把老骨頭了,真真折騰不起。
“這箱籠給奴才吧,奴才給幾位主子燒了熱水,主子們前去歇歇。”
說話的是跟在吉榮邊的小太監,名喚六垚,乃沈時晏邊近侍,也是吉榮一手帶出的徒兒。
他為人聰敏作也利落,說話間便已將箱籠接了過來安放在屋中。
萬宵幾人進了屋子,沈千聿看了看自己同宋挽的寢房,淡淡一笑。
瞧這屋子便知沈時晏是用了心的。
他的皇兒知曉他子不好,畏寒懼冷。是以這小院地下建了火道,如今燒著地龍,屋中溫暖如春。一路自長樂宮走來沾染的寒氣,進了這屋子也很快消散。
“這屋子好,小且致,冬日亦不會冷。”
宋挽看著沈時晏,慈一笑。
麵容不負年輕時秀,眉眼間也帶了淡淡細紋,可沈千聿瞧著仍覺心。
“你們幾個小的都留下一起吃頓便飯,待過了今日,便莫總來這打擾了。”
指著屋中幾個年輕人,沈千聿淡淡開口。
沈時晏同沈時驍沒什麽反應,倒是六垚同萬宵早些年收的幹兒子崔荇,恭敬應是。
幾人用過膳後一一離開,沈千聿同宋挽回了屋中休息,唯獨崔荇站在萬宵邊,語帶擔憂:“眼下還涼著,義父不若去屋中休息?”
Advertisement
萬宵躺在躺椅上,閉目曬著太。
許久後,他道:“李家二子前段時日去了南慶,如今可安全到了?”
“到了,已在南慶落腳。”
“義父可要孩兒暗中予些幫助?”
“不必。”
“不必了……”
崔荇聞言微微抬頭,不知義父今日為何未再給李家人庇護。
從他被萬宵帶至旁接手東廠後,崔荇便時常可在他口中聽見有關李家人之言。
有的時候是稍加援手為李承祖疏通路,有的時候是為李家長子求一名師,亦或其他瑣碎小事。
他暗中探查過這戶人家,與朝中世家並無關係,同他義父亦沒什麽。
據他所知義父已多年未曾出宮,也沒見過這李姓人家的誰。可他時不時便會接到萬宵的一二指令,去理同這戶人家相關之事。
最令他納罕的是幾年前他剛到萬宵邊,突有一日,義父讓他去理一個京營守備。
那守備份並無異常,他妥善理後回宮稟報,他義父卻微微揮手示意不耐聽。
“那李氏珍娘如何?”
“李氏珍娘……”
崔荇被萬宵問得一愣,一時未能答話。
那是崔荇第一次在萬宵口中聽見李家人之名。
“去查,而後好生安頓。”
萬宵隻留下這一句,便讓他去安頓李氏珍娘了。
他當時不懂義父的意思,待細細查看過後,方知曉那京營守備乃李氏之夫。他在外為人慷慨重義,好似是個至善之人,可實則嗜賭,卑劣不堪。
他暗中將李氏嫁妝盡還了賭債不說,還迫李氏向母族索要銀錢。
李氏的母親心疼兒便給了幾次,甚至還給出了半匣子珍珠。
可那守備不僅不曾恩,胃口還愈發大了,時常對李氏拳打腳踢,很是惡劣。
後來崔荇將李氏夫婿暗中理,不多時李氏便被休棄回家,且還帶著兩個娃兒。
也是自那以後,他每隔一年半載便會聽見義父問起這一家,直到今日。
“去了南慶便不是咱們能管的了,哪怕是東廠的手,也不可得那樣長。”
萬宵站起,崔荇連忙上前攙扶,將人扶進屋中。
沈千聿與萬宵幾人便在這院中安頓了下來,宋挽這些年為照顧沈千聿,同太醫學了不醫。
平日施針推拿便由手,沈千聿原本還有些不忍,可宋挽堅持他也就隨去了。
了這小院中後,時間好似緩緩停滯下來。
二人早起去到花園走走,待累了便回院中歇歇,亦或同萬宵蘅芷幾人一同用午膳。
偶爾商蓉趙南璋等人前來,眾人還會一齊品茗對弈,消磨時間。
在小院中居住的這幾年,沈千聿將子養得不錯,宋挽心中亦放鬆不。
沈時晏愈發有帝王之威,偶爾來到院中陪他二人用膳時,不時會出幾分凝重之。宋挽不知是否前朝出了什麽狀況,但同沈千聿都懶怠詢問。
這江山既予到他手中,夫妻二人便信沈時晏可將之管理好。
宋蕓寧去世時,沈千柏曾回過東寧一次,既是來報喪,亦有想將南慶歸還之意。
宋挽不知千柏同晏兒是如何商議的,隻知驍兒不久後同千柏一起回了南慶。
知曉姑母死訊同沈時驍離京時,宋挽都不曾落淚。倒是一個秋日裏,沈千聿突風寒一病不起,令眼紅了幾日。
本隻是個普通風寒,可沈千聿就是拖了許久都未好。
宋挽心中焦急,麵上卻從不表半分。
“今兒又喝藥?”
“最後一碗。”
沈千聿凝眉:“你昨兒個也是這般說的。”
“是嗎,我怎記不得了?”
宋挽邊說邊將手中藥碗送到沈千聿麵前,又拿了羹匙一口一口喂給他喝。
“苦……”
“你小皇孫喝藥都不曾喊過一個苦字,你喊什麽?”
再次將半溫不涼的藥送沈千聿口中,宋挽再不開口。
知曉氣自己未護好子,故意一口一口喂他吃這苦藥,沈千聿不敢再說什麽,唯有咬著牙一口口咽了下去。
“下次可還敢隻穿著衫在院中飲酒?”
“不敢了。”
“真不敢才好。”
宋挽自瓷罐中夾出一顆糖漬梅子放沈千聿口中,沈千聿臊眉耷眼含著,一句反駁之言都不敢有。
“挽兒,你鬢邊生了白發。”
沈千聿抬起頭,忽見宋挽兩鬢旁邊多出許多銀,他愣愣看著,好似十分驚奇。
“又不是今日方有的,你怎得大驚小怪起來?”
“且我二人都什麽年紀了?沒有白發才更稀奇。”.伍2⓪.С○м҈
沈千聿看著站在下的宋挽,呆呆道:“可於我心中,挽兒一直都是京郊別院裏,站在月下那清冷絕的模樣。”
“以前是,如今也是。”
“那你快些好起來,待子康健,你帶我再回京郊別院一趟,我想去那瞧瞧,再瞧瞧當日的月,想再聽你說一句一帆風順,得遇良人。”
沈千聿仰著頭,眼中展點點笑意:“好,我一定再帶挽兒回一趟京郊別院……”
。您提供大神任歡遊的縛春
猜你喜歡
-
完結516 章

歡喜農家科舉記
一品大員魏銘南征北戰、孤苦病逝,重回十歲饑荒那年,他立志今生要剷除禍國的貪腐奸佞。只是順手救了個女娃,引發畫風突變... ... 他十年寒窗苦讀,歡聲笑語是怎麼回事?他一生清正廉潔,財源廣進是什麼操作?到了最後,魏首輔已經被帶跑偏了,“我夫人是錦鯉本鯉,了解一下?” 首輔夫人崔稚:“轉發這條錦鯉,人生贏家是你!”
93萬字8.18 25989 -
完結525 章
福臨門之農家醫女
絕育女醫生重生成爲秀才的懶饞孕妻.孃親早逝,爹是商人,哥是捕快,把她寵得沒個邊. 公公厚道,繼母刁難,大哥憨厚木訥,大伯母尖酸刻薄,小叔子敗家,小姑子虛榮. 依不了山,傍不了水,打不了野味挖不了寶,捉不了魚逮不了蝦. 沒關係,全能溫柔夫君秀才種小麥收玉米,閒時種菜賣賣瓜,順便養雞養鴨,養兔子. 鄰居家娃病了?沒關係,咱會看. 你家孕婦難產,一屍兩命?這沒啥,咱會幫她剖腹產子! 秀才夫君種田爭功名,她醫人獲名聲. 茅屋變瓦屋,瓦屋變金屋.秀才夫君做了官,她成了誥命夫人,兒女雙全福臨門! 本文1對1.男主吃苦耐勞內向深情絕世好妻奴,女主恩怨分明活潑忠貞相夫教子.
213萬字7.91 57786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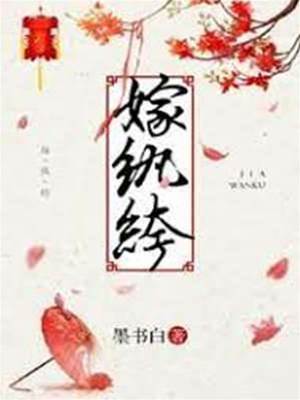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9361 -
完結260 章

絕世丑妃(完)
她,臉有胎記奇丑無比,卻遇上他獨獨鐘愛那張容顏。不顧世人的眼光,他將身為他弟媳的她納為己有。他無比溫柔,她步步淪陷。最終發現她也不過是另一個女子的替代品而已。失子之痛令她傷心離去,再次相遇,他對她說,“賤人,你連給朕暖床的資格都沒有!”他的…
28.9萬字8 29730 -
完結811 章

攝政王的戰神醫妃
末世兵王蘇清顏,醫毒雙絕。一朝穿越,成了被捧殺養廢、臭名遠揚的侯府嫡女,開局就被釘在棺材里……戰神王爺白玉堂,威名赫赫,卻身中劇毒命不久矣……當清冷無雙的戰神攝政王遇到熱情強悍的火爆小醫妃,1V1強寵大戲,開演!
139.4萬字8 113448 -
完結353 章

嫁給白月光的宿敵之后
蘇明嫵本該嫁進東宮,和青梅竹馬的太子舉案齊眉,然而花轎交錯,她被擡進了同日成婚的雍涼王府中。 恨了符欒半輩子,住在王府偏院瓦房,死前才知策劃錯嫁的人是她的心頭硃砂白月光。 一朝重生,蘇明嫵重生在了洞房翌日。好巧不巧,她正以死相逼,要喝避子湯藥... 天子幼弟符欒,十四歲前往涼州封地,十六歲親自出徵北羌,次年得勝被流箭射穿左眼。這樣心狠的大人物,大家心照不宣,蘇明嫵這朵嬌花落入他的手裏,怕是要被磋磨成玩物不止。 尤其是這個美嬌娥,心裏還掛念着她的小情郎,哪有男人能忍得? 雍涼王聞此傳言,似笑非笑點了點頭,好巧,他深以爲然。 婚後滿月歸寧那日,經過樓閣轉角。 “嬌嬌,與母親講,王爺他到底待你如何?可曾欺負你?” 符欒停下腳步,右邊長眸慵懶地掃過去,他的小嬌妻雙頰酡紅,如塊溫香軟玉,正細聲細氣寬慰道:“母親,我是他的人,他幹嘛欺負我呀...” 她是他的人,所以後來,符欒牽着她一起走上至高無上的位置。
53.8萬字8.18 584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