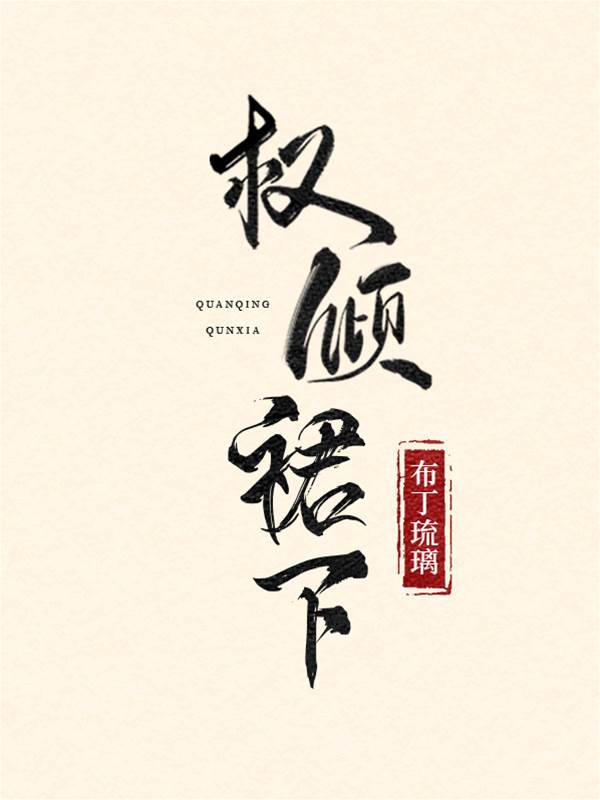《我本閑涼》 12.第012章 我出軌了?
屋安靜得過分。
薛遲還在,隻是已經睡著了,就躺在暖炕上鋪著的錦緞大條褥上,因屋裏燒著炭盆,僅蓋了一條薄被。
青雀就侍立在一旁,神格外整肅。
雕漆小方幾上的藥罐子已經收起,反倒是放了一封拆過的信,左側坐了個有些年紀的人,華服加,滿是威儀。
檀的宮裝未曾換下,上頭用金線刺著的祥雲瑞還很紮眼。頭上挽著的是淩虛髻,墜著金簪玉釵,佩了孔雀銜珠一對耳墜,顯得貴氣人。
即便因上了年紀,眼角有些細紋,可五卻很致,帶著點淡淡的淩厲和雍容。
不管是氣質還是儀態,都是久居上位者才有的。
陸錦惜進來的時候,正拿著一細細的小銀火箸,有一下沒一下地撥著手爐裏的灰,像是等久了。
聽見腳步聲,頭也沒抬一下,像是知道陸錦惜要行禮,隻淡淡道:“坐下吧。”
陸錦惜要行禮的作,一下便頓住了。
這一把嗓音,冷冽裏帶著幾分雍容,語氣似乎也算稔。
可說不上是為什麽,聽了,竟覺得有些不安:總覺得,長公主這一次來,好像不是為了尋常事……
端看這一宮裝,還沒換下,便知一回宮,便來了自己這裏等著。
一個後輩,又份微末,哪裏值得堂堂長公主來等?
懷著疑慮,陸錦惜到底還是應了一聲,坐下了。
隻是便給一百個膽子,也不敢坐到炕上永寧長公主對麵去,隻撿了右手邊一把玫瑰椅,正襟危坐。
這一下,永寧長公主,才了眼皮,看了一眼。
目由上而下,帶著一種毫不掩飾的打量,甚至有些利,像是一把刀,要把給剖開了,研究個仔細。
端莊溫和的眉眼,素淨淡雅的妝容,雙手疊在一起,顯得規規矩矩,從上到下,這上的確不大挑得出錯來。
Advertisement
宮廷,朝堂,什麽事永寧長公主都知道。
看人,也是一把好手。
今日剛回府來,就聽了好一通的熱鬧,甚至聽說那個囂張跋扈的衛仙,也終於在陸錦惜手裏栽了一回。
不僅是自己丟臉,就連丫鬟都被打了豬頭。
要知道,陸錦惜這子,罵了不知多回,都沒起。
現如今,竟一下變了。
該說是世事難料,人心難測,有時候看人也不一定準嗎?
不僅沒料到陸錦惜的改變,也沒料想竟有膽子做出那等事來……
心念及此,便有一火氣往上竄。
還好眼角餘一閃,瞥見了旁邊睡的遲哥兒,隻眉頭一皺,了下來,吩咐了青雀:“先把遲哥兒抱下去睡吧。”
免得一會兒說事,吵著了。
青雀下意識看了陸錦惜一眼。
陸錦惜微不可見地點了點頭,也沒說什麽。
薛遲這會兒睡得很,一點看不出那蠻橫的呆霸王樣。
臉上有傷,可臉紅潤,香甜極了,青雀作也輕,沒把他吵醒,沒什麽靜地抱了出去。
這一下,屋裏便隻有幾個丫鬟。
永寧長公主揮了揮手,也們出去了,隻留下自己邊的幾個丫鬟。
看到這裏,陸錦惜哪裏還不明白,隻怕是真有什麽嚴重的事了。
兩道細眉微皺,放恭敬了態度:“侄媳方才去理英國公府的事,一時回來得晚了,並不知嬸嬸已經到來,還嬸嬸容諒。”
“事本宮已聽說了。”
永寧長公主了那銀火箸,在手裏轉了轉,似乎不大關心,隨口問道:“理得如何?沒出什麽大事吧?”
“都是兩個小孩子間的玩鬧,世子夫人通達理,並未追究。先才侄媳已請了鬼手張大夫為兩個孩子看過,都是些皮外傷,養上幾日,便會痊愈。”
Advertisement
陸錦惜謹慎地回答了,也不敢問更多。
窗外有寒風吹刮而過,搖得窗紙撲簌。
在這人的屋子裏,顯得格外冷寂,又格外人心。
“也算你病了一回,有些長進,找了鬼手張,理得還不差。”
永寧長公主向著窗外看了一眼,聲音有些莫測,隨即又轉頭來看,見眉眼低垂,一副小心模樣,不由笑了一聲。
“說句實在話,當年這掌家的權,是你要薛況給的。本宮也知道你們是什麽況,可你子太,鎮不住他們。沒想到,今日卻本宮另眼相看一回……”
陸錦惜頓時無言。
薛況與原陸氏之間的恩怨,實在難說。
慶安帝一旨賜婚,把兩個人湊了一對。
可薛況回京就帶了個妾室和孩子,對陸氏似乎也沒什麽。
沒了,還不能要個權嗎?
陸錦惜琢磨著,陸氏便是出於這樣的心理,也要維護自己作為薛況妻子的麵,所以才提出了這樣的要求。
太太孫氏喪夫,子骨雖朗,一顆心卻淡了,對府裏的事本就不管。
所以,這條件,據說薛況答應得很容易。
隻是這些年來,陸氏的表現,實在算不得很好。
如今聽永寧長公主提起,陸錦惜便知道,這一位嬸嬸在背後撐著自己,也提點著,多半是因為昔年薛況的承諾。
給不了的,永遠給不了;能給你的,護你周全。
陸錦惜想來,竟覺得有一點點諷刺,隻是不知道該諷刺賜婚的皇帝,還是諷刺這夫妻兩個。
沉下了心思,慢慢回道:“嬸嬸記掛,侄媳病好之後,想通了許多,再不敢跟往日一樣,渾渾噩噩。”
“若真是開悟了,那也算好事一件。”
角一彎,永寧長公主笑得雍容,可話卻讓人難以捉。
Advertisement
“前幾日你人在病中,府裏大小事也沒去打擾你。不過如今卻是等不得了,正巧你病好,我今日便來找你說上個一二。”
下意識地,陸錦惜想到了葉氏說的那些。
斟酌了片刻,大著膽子問道:“嬸嬸要說的,可是顧太師府的事?”
“你竟知道?”
永寧長公主一下有些驚訝起來,不由多看一眼。
陸錦惜微微一笑,回道:“原是不知道的,不過方才去隔壁國公府走一遭,世子夫人正好與我談到此事,還向我打聽顧大公子的事。所以我們聊了三兩句,於是知道了個一二,隻是都不知道昨夜顧太師上山,到底是什麽原委……”
原來是這樣。
還當是自己關心起外麵的事來了,沒想到是巧合。
不過知道一些也好,省得費太多口舌。
永寧長公主捧著手爐,想起了今日在宮裏聽的那一堆閑話,還有出宮門時候,顧家那邊傳來的消息。
“顧太師昨夜上山,是去拜會覺遠方丈了,也就是顧覺非的師兄。”
覺遠方丈是名高僧,隻是他繼承他師尊苦行大和尚的缽,也沒有幾年。
二十多年前,顧覺非才出生不久,虛弱,生了很大一場病。
苦行和尚當時遊方在外,略通歧黃之,無意逢著,使了妙手,給治好了。
那時候,顧覺非還未起名。
顧太師顧念苦行和尚的恩,又覺得這一遭實在是有緣,便請苦行和尚將顧覺非收為了記名弟子,也略作消災解難。
所以,顧覺非名字裏的“覺非”二字,乃是出自苦行和尚,按著佛門的輩分給排的。
如今的覺遠方丈,也是苦行和尚的弟子。
算起來,顧覺非雖是俗家,卻是覺遠的師弟。若真要在大昭寺論資排輩,不小沙彌都要喚他“師叔”或者“師叔祖”。
Advertisement
“覺遠方丈,與顧覺非算是好,又是個有大智慧之人。”
永寧長公主思索著,卻是慢慢地笑了起來,仿佛是看到了不久之後,這風雲湧的京城。
“顧覺非的確是不擇手段,且詭譎,狡詐難測。可對著他爹麽,也不一定就能狠心絕。再說了,京城如今這一盤棋,正正好在點上,他又怎麽舍得不回來?”
話裏,不乏一點辛辣的嘲諷。
陸錦惜卻聽得有些迷糊起來——
從丫鬟們裏聽說的顧覺非,老跟衛儀糾纏在一起,是個癡種;
從葉氏口中聽說的顧覺非,二十三歲拿了探花,是位才華蓋世的如玉公子;
可如今,永寧公主口中的顧覺非,竟是“不擇手段”“詭譎”“狡詐難測”,又了一個人不寒而栗的心機高手?
隻是永寧長公主半分沒有解釋的意思。
“一個時辰前,大昭寺那邊有人傳了消息來,說顧覺非會回,隻是時間還沒定……”
說到這裏,頓了一頓,著陸錦惜,頗帶著點玩味地笑了一聲。
“說是要等,那山上的雪,什麽時候化幹淨,他什麽時候才下山。”
陸錦惜頓時有些咋舌:這架子,也真是夠大的……
永寧長公主卻歎,顧太師這麽頭老狐貍,一生榮華,就沒怎麽摔過跤,結果人老了,想見見自己的兒子,還要看老天爺的臉。
隻對陸錦惜道:“如今京中知道這消息的沒幾個。這十日裏,若不下連綿的雪,總歸還是有雪化的一日的。你如今是將軍府掌事夫人,不得十日後要去太師府走一趟,備的禮不必太厚,最好送到點子上。此事是重中之重,不得馬虎,你看好了。”
“謝嬸嬸提點,侄媳省得了。”
看來,十日後,太師府壽宴,有好戲看了?
得了顧太師上山之事的確切消息,陸錦惜一顆心,慢慢地落了地。
葉氏所言,的確不假。
顧太師府在朝中的勢力,該異常紮實,不然一個大公子要回來的事,也不至於這樣牽人心;
永寧長公主,也的確與顧太師府很近。人人都求不來的消息,到這裏輕飄飄的,半個銅板也不值的模樣。
而且……
對顧覺非的評價,與旁人完全不一樣。
要麽是對此人有偏見,要麽就是知道的,遠遠超過旁人的想象。
陸錦惜心念閃,微有沉思。
隻是很快,便覺到了一道目的注視,抬起頭來,便發現長公主竟又在打量了。
略遲疑了片刻,開口道:“嬸嬸可是有事?”
“本宮今日出宮的時候,在宮門口,見了翰林院侍講學士宋知言大人。”
這是平直的陳述,幾乎不帶有。
連帶著那一雙眼睛,也沒有溫度,有一暗藏風雨的味道。
陸錦惜聽了卻是半點不明白。
宋知言?
是沒聽過,可不知道跟原是有什麽關係?
單從陸錦惜的麵上,實則看不出什麽緒波。
本就不是什麽簡單的人,商場談判桌上混著跟吃飯喝水一樣尋常,即便在麵前的是永寧長公主,沒出什麽破綻。
這樣的不如山,落到永寧長公主的眼底,便多了幾分複雜味道。
是一直小看了麽?
聽了宋知言的名字,都還這樣不聲。
想起今日撞破的這件事,永寧長公主心緒難平,可一看陸錦惜模樣,一下又想起跟薛況那一筆爛賬來。
誰又欠誰呢?
本就是一旨詔書,瞎湊的一對。
雕漆方幾上,那一封拆開的信,已經放了許久。
“你是將軍府的掌事夫人,一品誥命。本宮知道,薛況對你不起,你本也沒有為他守寡的道理。我一直想你改嫁,可你……”永寧長公主隻把那一封信拿起來,起了,冷笑,“可你做的都是什麽?”
陸錦惜聽到半道已經覺出不對,皺了眉頭。
永寧長公主卻直接將信一扔,摔到懷裏,一張雍容的麵目上,已經看不到半點笑意,隻有濃濃的失!
“不過一個從五品的翰林院侍講學士,還是有婦之夫,也配得上我將軍府堂堂的一品誥命?”
“你就不能找個配得上的嗎?”
“便是你與他青梅竹馬,又何苦這樣糟踐自己?!”
陸錦惜傻了。
這個發展完全超出了的預料,跟過山車一樣刺激,讓好半天沒說出話來。
大致聽出出了什麽事,可……
這一位長公主嬸嬸,竟這麽開明?
一時不知道說什麽,隻用一種奇異的目,著永寧長公主。
永寧長公主見了,卻是氣不打一來,怒道:“你就這麽糊塗死了算了!”
說完,竟片刻都不想再待,直接拂袖而去。
猜你喜歡
-
完結140 章

公府嬌娘(重生)
顏熙去臨縣投靠舅父,被舅父舅母做主嫁給了衛家三郎衛轍。衛三郎生得豐神俊朗、英姿挺拓,猶若一朵長在雪巔的高嶺之花。雖然看著清冷孤傲不易親近,但顏熙卻一眼就相中。只是衛三郎不是真的衛三郎,而是京都長安城魏國公府世子。因失憶流落吉安縣,被衛家誤認…
51.5萬字8 22629 -
連載3516 章

醫毒雙絕:腹黑魔尊賴上門
她,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一朝魂穿!她成了沐家的廢物醜女大小姐,從此,廢物醜女變成了絕色頂級強者,煉丹!煉毒!煉器!陣法!禦獸!隨手拈來!神獸!神器!要多少有多少!可是誰能告訴她,這個人人談之色變,不近女色的魔尊,為什麼天天黏著她,還對她精心嗬護,體貼備至……
282.6萬字8.18 638205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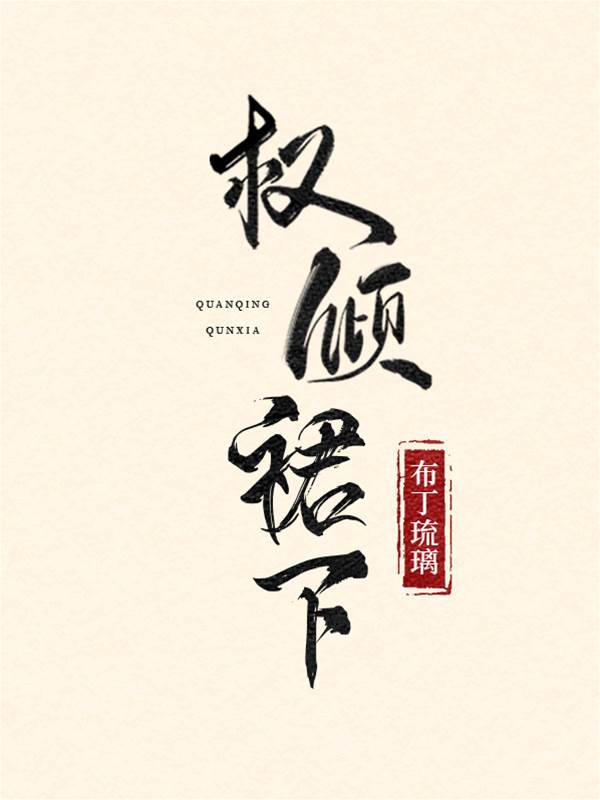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2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