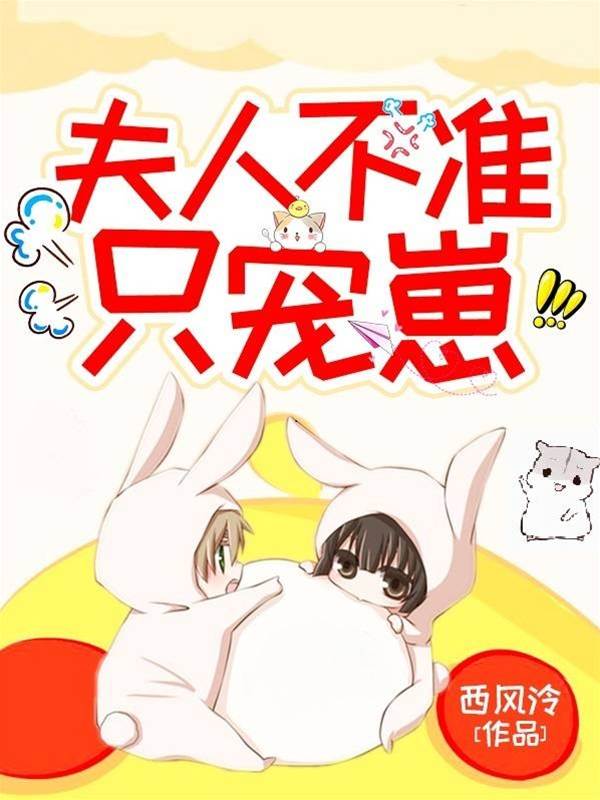《雪意和五點鍾》 番外六
如果有人問梁言, 嫁給陳之和後的生活到底不好,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當然, 要是問全然都是好的麼, 會搖搖頭說當然不是。
生活本來就是悲喜加有起有伏,梁言的生活也不外如是。
蔣教授還是時常對耳提面命,對這個孫還是存有偏見, 楊敏儀時不時會慪一下, 妯娌間偶爾還會有些小……有些煩惱就和慢頑疾一樣,沒辦法藥到病除, 發病的時候梁言還是會覺得不舒服不開心。
日底下雖無新事, 但同一件事即使在這個世界上發生過千千萬萬次, 攤到每個人上仍然是新鮮的, 梁言的生活也有不的新變化, 出版了新的漫畫集, 拿了一個業小有名氣的漫畫獎,開了一家自己的手工小店,養了一隻垂耳兔, 肚子越來越大了。
梁言至今還記得當時在醫院, 得知點上燈籠後陳之和的表, 還是頭一回見他犯懵, 原來再理智聰明的人也會被興沖昏頭腦。
也沒忘記自己當時抱著陳之和哭得稀里嘩啦的, 直說家裡總算要掛上「燈籠」了。
梁言是在冬天懷的寶寶,和陳之和的第二個結婚紀念日是一家三口一起慶祝的, 整個冬季, 基本都宅在家裡養胎, 蔣教授知道懷孕後,隔三差五就燉了湯上門, 梁教授也時不時會來看,倆教授偶爾上,雖難免尷尬,但至不像從前,劍拔弩張勢同水火。
陳之和在懷孕後就推掉了很多工作,他很在公司加班,即使忙不完,他也會把活兒帶回家裡,一方面他覺得自己在梁言邊能放心,另一方面有梁言在邊他安心。
Advertisement
年前,陳之和特地騰出了幾天時間,本想帶梁言去南方比較溫暖的地方散散心,但本人卻想去一趟他的老家。
陳之和的老家在比A市更北的地方,冬早開春晚,天寒地凍,有的地方積雪能有一丈厚,梁言顯懷後,子越來越重,他本來是打算勸等來年融雪後再出行的,可心心念念地想去他生長的故土看看,他不忍心看失,就答應了。
陳之和親自駕車,他們清晨從A市出發,走走停停,晚上才到目的地。
車開得慢,一路上晃晃悠悠的,梁言在車上睡著了,車到鎮上時,一點要醒的跡象都沒有。
陳之和把車停好後,解開安全帶,俯靠近副駕駛座,抬手輕輕了梁言的臉,低聲喚道:「言言,言言。」
梁言悠悠轉醒,還很迷瞪,看著上方的陳之和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
「到了嗎?」
陳之和扶著坐起來:「到了。」
梁言轉過頭往窗外看:「天都暗了呀。」
了個懶腰:「我顧著睡了,你開車累了吧。」
「不會。」
陳之和幫理了理鬢髮,拿過羽絨服給穿上,幫圍上圍巾,又伺候把雪地靴穿上。
梁言盯著陳之和,忽然傻呵呵地笑了。
陳之和抬眼:「笑什麼?」
「你這樣……好像我以前當師時候的樣子,我又不是小孩子。」
「手。」
陳之和給梁言戴上手套,「我十八歲離開這兒,那時候你多大?」
梁言撇了下,不願的說:「……八歲。」
陳之和楊了下眉,意思不言而喻。
梁言撇了下,不甘心地咕噥道:「我都要當媽媽了,不小了。」
Advertisement
陳之和幫把羽絨服的拉鏈拉上,輕輕拍了下的肩,低笑道:「到地方了,孩子他媽,走吧。」
他先行下車,繞到副駕駛座給梁言開車門,雪天路,他牽著的手,摟著一路小心地護著。
陳家的老房子是陳父單位分配的,在舊小區里,兩居室,陳之和把二老接到A市後房子就空了出來,家裡老太太知道他們要回老家,提前托人把家裡收拾了下。
進到房子裡後,陳之和先去了暖氣片,確認供暖是否正常,房子雖久無人住,但還暖和,他到看了看,老太太還是周到,不僅主臥的床單被褥讓人給鋪好了,就連廚房的冰箱都上了電,儲藏著好些新鮮的果蔬食材。
梁言下羽絨服,也在屋子裡走了一圈,走到一間房,推門看到兩張並排的小床,回頭問:「這是你和大哥的房間?」
陳之和走過來:「嗯。」
他指了指靠窗的那張床:「我睡那兒。」
梁言走進去,房間不大,兩張床,兩張書桌就差不多把空間給滿了。
走近其中一張書桌,那張桌子上擺了個相框,裡面鑲著一張班級大合照,一眼就看到了陳之和。
合照是高中畢業照的,那時候的他看上去比現在青,梁言慨:「哇,你也有這個時候啊。」
陳之和點了下的額頭:「你以為我生來就是現在這樣?」
梁言又看了兩眼照片上的人:「我就是覺得好奇妙,你那個時候在學校是不是也很歡迎?」
「想知道?」
梁言點點頭。
陳之和拉著往外走:「先吃點東西,晚點告訴你。」
陳之和用冰箱裡的食材煮了個面,梁言懷孕後胃口並未變差,反倒比以前還嗜吃,現在正是需要營養的時候,他不得按一天七八頓養。
Advertisement
吃完東西,陳之和陪梁言在屋子裡走消食,邊走邊說自己以前在學校的事,梁言聽得津津有味,總覺得在他長的地方聽他講以前的事,仿佛臨其境般,即使從未參與,也有共鳴。
晚上,梁言洗好澡就上了床,陳之和洗了澡進來臥室,看到腳丫子在外面,微微擰起眉頭,走過去扯過被子蓋住的腳。
梁言輕輕踢了下被子:「熱。」
「不蓋被子容易著涼。」
陳之和掀開被子,從另一邊上了床,他剛躺下,梁言就自鑽進了他懷裡。
他低頭:「這會兒不嫌熱了?」
梁言找了個舒適的位置窩著,陳之和攬住,握著的一隻手輕輕按著,這段時間有些水腫,指節漲了一圈,婚戒都戴不了。
「我最近長了。」
「嗯。」
陳之和很滿意這個結果。
梁言了他的膛,又往下掐了掐他仍然勁瘦的腰,不滿道:「明明我吃的時候你也在吃來著,怎麼你不長。」
陳之和語調慵懶:「我運。」
「自律的人就是不一樣。」
梁言由衷佩服,枕著他的胳膊,囔囔說道,「希『小燈籠』以後也像你這樣,最好長得像你,格像你,脾氣像你,能力像你……」
「複製人呢。」
梁言絞盡腦想了想:「那長得稍微像我也可以……我也沒別的好基因可以傳給TA了。」
陳之和抓起的手放邊輕輕齧咬了一口:「埋汰誰的眼呢。」
梁言恍然大悟般,鄭重道:「眼還是隨我比較好。」
陳之和一時都不知是在誇他還是在損他,只好無奈一笑,輕拍的背,低聲哄:「睡吧,明天帶你去出門。」
Advertisement
.
梁言不認床,有陳之和在邊睡得很安心。
第二天早上,梁言悠悠轉醒,醒來時邊沒人,習慣地了隆起的肚子,道了句「早安」,爾後緩緩撐著坐起來。
披了件外套走出臥室,正巧陳之和從外頭回來,詫異:「你去鍛鍊了?」
陳之和舉起手示意了下:「去買了早點,小時候常吃的一家店,沒想到還開著。」
梁言洗漱完坐在餐桌上,聞著味兒就食指大。
陳之和把買來的早點一樣樣用盤子擺出來,差不多把一張小方桌擺滿。
「你不會每樣早點都買了一份吧。」
梁言瞠目。
陳之和不予否認:「趁熱嘗嘗。」
梁言拿筷子夾了個珍珠小籠包,一口咬進裡,熱乎乎的讓人倍滿足:「好吃。」
把食咽下去,問道:「你以前最喜歡吃哪樣?」
陳之和的目在桌上掠過,指著其中一盤說:「魚餃,老闆說是用今早在湖裡冰釣釣上來的魚做的,很新鮮。」
梁言聞言,立刻把筷子轉了向,夾起一個魚餃嘗了嘗。
「好吃!」
又夾起一個餵給陳之和,「你也嘗一個。」
陳之和熱了杯牛給梁言,看兩頰鼓鼓,不由說道:「慢點吃,不急。」
梁言喝了口:「我們今天去哪兒?」
陳之和在邊坐下:「看過『采冰』嗎?」
「嗯?
『采冰』是什麼?」
陳之和揩了下的角:「一會兒你就知道。」
飯後,陳之和又把梁言裹個嚴實,他開車載著去了小鎮邊上的一個天然湖泊。
今天天氣正好,雖然氣溫低下,但沒下雪,外頭一片亮。
到了湖邊,梁言才知道「采冰」是什麼意思。
小鎮氣溫零下三十幾度,湖面能結厚厚的一層冰,一群采冰工人在冰面上鑿冰,把一塊塊大冰塊搬上運冰車。
湖面,陳之和不讓梁言上去,只讓站在岸邊看。
「他們運這些冰塊……是為了做冰雕?」
梁言問。
「嗯。」
「好辛苦。」
梁言要去看運冰車,陳之和一路攙著不放手。
「鎮上有冰雕師傅?」
梁言問。
「有。」
陳之和一直注意著的腳下,「有個冰雕公園,想去?」
梁言點頭:「雕冰雕,我還想學的。」
向來喜歡做些手工活兒,小店裡賣的東西也基本是自己做的。
陳之和扶著梁言在運冰車邊上站定,轉頭正巧看到一個采冰工人拖著冰塊往他們這兒來,他和工人對視了眼。
「今年新年禮就送你一塊冰?」
陳之和謔笑著問。
「好呀。」
梁言樂呵呵地點頭,轉眼看到采冰工人正要把一塊冰塊搬上車,努了下,「就這塊好啦。」
陳之和聳了下眉,對那位工人說了幾句話,真的就把那塊冰買下來了。
「它是你的了。」
梁言眨眼,眼睫上都凝了一層細霜:「你真送呀,我們帶不回去的。」
工人把冰塊拖到他們腳邊,梁言低頭去看冰塊,雕冰雕的冰都是經過挑選的,明度要高,這樣做冰燈才好看。
「欸?」
梁言微微彎腰,仔細去看冰塊。
在薄的照下,冰塊折出微,而比冰更閃耀的是冰塊里的一枚鑽戒。
梁言看到那枚戒指的一瞬間,眼眶就紅了。
陳之和看到的眼淚啪嗒啪嗒地砸在冰塊上,一時有些慌了,他扶起,幫了淚,又把人抱進懷裡。
「怎麼哭了?」
梁言在他懷裡嗚咽著,泣不聲:「太、太浪漫了。」
陳之和失笑。
「你怎麼又送戒指啊……我現在戴不了的。」
「你以為我為什麼會送戒指?」
陳之和一手著的背,一手握住的一隻手,隔著手套挲著,「指圍改了,這一枚你能戴。」
他說著下自己的左手手套,在梁言眼前晃了下手:「一對的。」
梁言的淚水又忍不住湧出來。
一直都謹小慎微地活著,不需要大驚喜,有些小確幸就已足夠,可眼前這個男人卻給了無盡的幸福。
梁言吸吸鼻子,忍住哭聲,看著陳之和嗚嗚咽咽地說:「既然這樣,我就再和你求一次婚好了……陳之和,你願不——」
「我願意。」
【如果您喜歡本小說,希您小手分到臉書Facebook,作者激不盡。】
猜你喜歡
-
完結143 章

重生之大佬的復仇嬌妻
前世,她受人蠱惑,為了所謂的愛情,拋棄自己的金主,最后身敗名裂,慘死在家里。 重生后,她只想抱著金主大大的大腿,哪里也不想去。可后來發現,金主抱著抱著,好像不一樣,她有點慌,現在放手還來得及嗎? 某天,金主把人圈在懷里,眸光微暗,咬牙切齒說“叫我叔叔?嗯?” 她從善如流,搖頭解釋,但他不聽,把人狠狠折騰一番。第二天,氣急敗壞的她收拾東西,帶著球,離家出走。
34.1萬字5 41505 -
完結968 章

總裁我不要辦公室戀情
一場奇葩的面試,她獲得了雙重身份,工作日她是朝五晚九忙到腳打後腦勺的房產部女售樓,休息日她是披荊斬棘幫上司的生活女特助。 他們說好只談交易不談感情,可突然有一天,他卻對她做了出格的事……「商總,你越線了」 「這是公平交易,你用了我的東西,我也用了你的」
255萬字8 19761 -
完結10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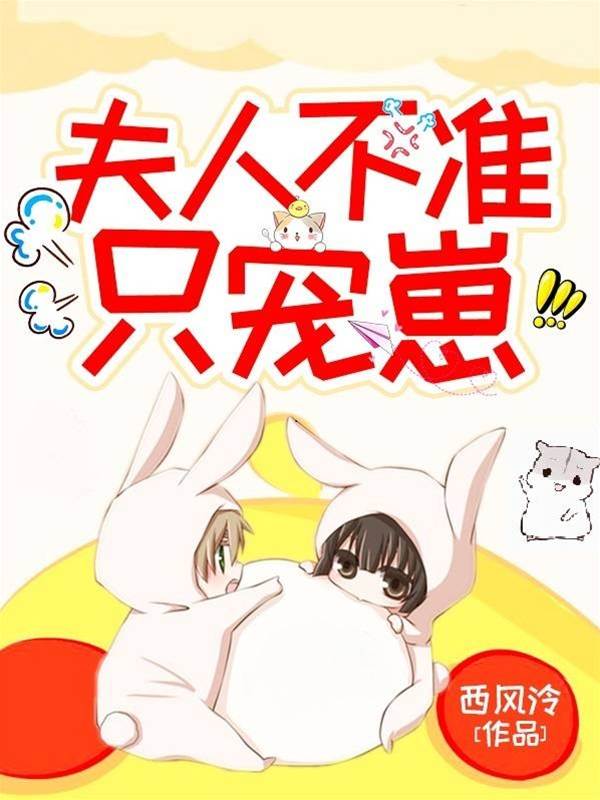
夫人不準只寵崽
南悠悠為了給母親治病為楚氏集團總裁楚寒高價產子,期間始終被蒙住眼睛,未見楚寒模樣,而楚寒卻記得她的臉,南悠悠順利產下一對龍鳳胎,還未見面就被楚家接走。
24.6萬字8 7223 -
完結389 章

炙吻
今年18歲的許芳菲,父親早逝,家中只一個母親一個外公,一家三口住喜旺街9號。 喜旺街徒有其名,是凌城出了名的貧民窟。 許母開了個紙錢鋪養活一家,許芳菲白天上學,晚上回家幫母親的忙。 日子清貧安穩,無波無瀾。 後來,樓下搬來了一個年輕人,高大英俊,眉目間有一種凌厲的冷漠不羈和刺骨荒寒。男人經常早出晚歸,一身傷。 故事在這天開始。 * 又一次相見,是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原,雄鷹掠過碧藍蒼穹,掠過皚皚白雪。 許芳菲軍校畢業,受命進入無人區,爲正執行絕密行動的狼牙特種部隊提供技術支援。 來接她的是此次行動的最高指揮官。 對方一身筆挺如畫的軍裝,冷峻面容在漫山大雪的映襯下,顯出幾分凜冽的散漫。 看他僅一眼,許芳菲便耳根泛紅,悶悶地別過頭去。 同行同事見狀好奇:“你和鄭隊以前認識?” 許芳菲心慌意亂,腦袋搖成撥浪鼓,支吾:“不。不太熟。” 當晚,她抱着牙刷臉盆去洗漱。 走出營房沒兩步,讓人一把拽過來給摁牆上。 四周黑乎乎一片,許芳菲心跳如雷。 “不熟?”低沉嗓音在耳畔響起,輕描淡寫兩個字,聽不出喜怒。 “……” “你十八歲那會兒我執行任務,拼死拼活拿命護着你,你上軍校之後我當你教導員,手把手教你拼組槍支,肉貼肉教你打靶格鬥,上個月我走之前吊我脖子上撒嬌賣萌不肯撒手。不太熟?“ “……” 鄭西野涼薄又自嘲地勾起脣,盯着她緋紅嬌俏的小臉,咬着牙擠出最後一句:“小崽子,可以啊。長大了,翅膀硬了。吵個架連老公都不認了。” 許芳菲:“……”
62.8萬字8.18 159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