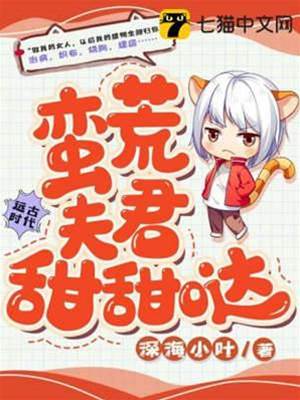《賜卿良辰》 大結局 縱使你死了
如果現在還有什麽可以慶幸的話,就隻能慶幸學過騎馬。
沈連翹還記得那次江流教騎馬,從馬上跌下來,是孔佑一麵責備,一麵把背回京城。
是世淒慘的孩子,從來隻知道保住自己,卻沒想到有個比還要辛苦的人,教會與責任。
良氏族人是的責任,京都的百姓,也是。
城門就在眼前,沈連翹看到有位員站在城門口。他一麵焦急地等待聖駕回鑾,一麵指揮百姓和牛馬從側門通過。他著汗,著肩,又整理好革帶,焦慮張,微胖的子像城門前的一立柱。
那是京兆府府尹湯瑞。
“湯大人!”沈連翹下馬喚他。
“哎喲,和順郡主。”湯瑞走過來,見沈連翹麵蒼白,一手握韁繩,一手捂肚子,連忙快走幾步,問道,“郡主怎麽了?要不要去看大夫?”
“不用!”沈連翹一陣暈眩,腹痛如絞。勉強開口道:“勞煩大人閉城十二座城門,不要讓百姓進去。”
“這怎麽能行?出什麽事了?”湯瑞張口結舌詢問,“百姓們聽說邙山大火,沒心思再瞻慕儀仗,慌著回家呢。”
沈連翹趴在馬背上,緩了緩,才跟湯瑞解釋。
“湯大人,邙山的大火是匪徒放的,城中銅駝街埋有火藥。你讓百姓進去,等於送死。”
“啥?”湯瑞瞠目結舌站在原地,許久才跳起來,呼喚衙役護衛道,“快!快攔住百姓,關城門!關城門!”
城門緩緩關閉,百姓們怨聲載道。
“為何不讓進?”
“該做晌午飯了,大人您管飯嗎?”
湯瑞一開始不想告知原委,可百姓不依不饒,把他圍了個水泄不通。湯瑞覺隻要誰踹他一腳,他就會被踩踏致死。憋悶中,他隻好跺腳解釋道:“不讓你們進!是怕你們死!你們沒聽郡主說嗎?有歹人在城裏埋了火藥!本先去排險,你們再進去不遲!”
Advertisement
“火藥?”
那是隻聽說過,從沒見過的東西。聽說隻有大周軍中有,作戰時燒營做火箭,厲害可怕。
人群向外散開,卻又有人更快地聚攏。
“我的孩子還在家,讓我把孩子接出來!”
“我娘也在家呢!鋪子還開著!”
但衙役和城門擋住大門,死守著,不讓他們進去。
一片混中,他們注意到了沈連翹。
“你就是郡主?你是大梁那個郡主?”
“你是陛下要娶的那位?”
有一個提著野菜籃子的婦人仔細辨認沈連翹,對旁人道:“是!以前就在我們那條街住,我認得!”
沈連翹咬牙關,勉強坐直些,夾馬腹,靠近城門。
“你們不要進去!”說道,“城裏的人也不要出來,以免打草驚蛇,歹人索引燃火藥。”
的聲音刻意拔高,每說一句都要吸一口氣。雖然天氣並不熱,額頭卻布滿細的汗珠。
“那怎麽辦?”
“府會管的吧?陛下還沒有回去。”
百姓們你一言我一語,圍著沈連翹問東問西。卻不再回答,隻慢慢縱馬來到城門前,對湯瑞道:“讓我進去!”
“本去就行了。”湯瑞沒有馬,此時征用了一輛牛車。
“我去,我有辦法。”沈連翹道。
“本為京都父母,怎麽能讓你這位大梁郡主隻涉險呢。本得親自去,本上不能負皇恩,下不能負黎民,百姓有難,本豈能……”
湯瑞喋喋不休說著,沈連翹已經從打開的門中進去。認真看一眼湯瑞,對他道:“別讓陛下來。”
這一眼夾雜著警告和勸誡,端坐駿馬之上的沈連翹像是要奔赴戰場,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將軍。那目不懼來路,直麵生死,帶著凜然的銳氣,直刺湯瑞心中。
Advertisement
剎那間,湯瑞仿佛看到去年匈奴侵時,率軍救城的皇帝陛下。
他打了一個哆嗦,像朝堂之上,溫馴地點頭道:“微臣懂了。”
說完話,才驚覺“微臣”二字不對。湯瑞想要解釋,沈連翹已經縱馬離去。衙役看著他道:“大人,您還去嗎?”
“去!去!”湯瑞鞭打著拉車的牛,“你們記得回稟陛下,不讓他進城!切記!切記!銅駝街,那是陛下回宮要走的路。還有,派人去封其他城門。還有,去通知衛尉軍統帥!快去快去!”
湯瑞駕著牛車進城,已經看不到沈連翹。
後的城門緩緩關閉,而城門毫不知的百姓,在街巷中穿梭而過。他們有的正在逗弄頑,有的在追著逃學的孩子責罵,有的呼朋喚友,步飯館準備大吃一頓,有個賣糖人的因為城裏人生意不好,垂頭喪氣走過。
而城外的百姓,反而無人在意瑣碎的煩心事。
他們靜默一片,直到有人低聲道:“大梁郡主為什麽要進去?不怕死嗎?”
“對啊,怎麽是來救咱們?”
“對啊,我還往使館門上砸過臭蛋呢!”有人疑道。
“你怎麽能這樣呢?你不知道是在城長大的嗎?”立刻有人大聲斥責。
前者咬麵愧疚:“我哪兒知道啊,就聽說大梁打咱們了。”
“大梁跟郡主有什麽關係?是咱們人!”
“對對!”附和聲一片,“郡主是人!是咱們的人!”
“可是郡主……”一個細微的聲音在人群中響起,“能活著回來嗎?”
城外的議論聲漸漸消失,百姓們相互看看,從對方臉上看到難過、敬重、焦急、悲憤、愧和淒惶。
能活著回來嗎?
邙山山火不停。
最早逃下山的,是月老祠的道士。他們說火是從寂照宮燒下來的,山火點燃林間積年的樹葉,煙熏火燎,不民眾被困在山上。
Advertisement
剛剛下山的孔佑轉頭看向山巒。
“陛下,”隨他的太常大人徐易水進諫道,“需要快些命人阻斷山火,挖倒皇陵周圍的樹木,用水澆地麵,防止火燒皇陵。”
“需要多人?”孔佑拿開捂鼻的帕,問。
蔡無疾立刻答話:“衛尉軍全員出,方能做到。”
孔佑俊朗的臉上浮現一憂慮。
“你們全員出去守皇陵,山上的百姓怎麽辦?”他說著命令蔡無疾,“你帶人上山,試著把百姓救下來。無論是背還是抬,務必能救多,就救多。”
蔡無疾領旨退下,孔佑看著毫不的儀仗,點頭道:“走吧,路上不要滋擾百姓。”
孔佑準備進玉輅,視線卻又落在道旁。
那裏有個悉的人。
“嚴君仆。”他止步抬頭,看向層層護衛外,跟百姓一起跪在道旁的男人。
嚴君仆立刻帶著邊的人上前見禮。
“陛下。”
“跟孤一起走吧,”孔佑道,“乘孤的車,路上我們說說話。”
四周的百姓不免出豔羨的神,沒想到嚴君仆卻搖頭道:“陛下大駕鹵簿出行,草民不敢違背禮法。”
孔佑含笑點頭,又看著他邊的人道:“這位,是沈大河嗎?”
沈大河同嚴君仆在路上偶遇,被嚴君仆揪了過來。此時他誠惶誠恐地叩頭道:“草民正是。”
“好好做事。”孔佑叮囑道。
聖駕向前去,遠的道上,一名衛尉軍手握玉墜,飛奔的馬蹄踏破塵土,距離皇帝儀仗越來越近。
皇帝起駕離去,沈大河不願地站起。
“到底要我幹什麽?”他問道。
好不容易今天不用挑糞,沒想到看個熱鬧也能被嚴君仆逮到。
“有個亭子,”嚴君仆道,“你去幫忙拆了。”
他拍落上的灰塵,想到應該告訴皇帝孔家的事,又覺得還是讓孔雲程自己去請罪比較好。
Advertisement
沈大河雖然不願,也不敢反駁嚴君仆。
山下道前,他費勁兒刨開土地,待看到黑的火藥,頓時手腳發麻怔在原地。
“這是?”
“這是要刺殺郡主。”嚴君仆出細長的引信,歎了口氣。
“沈連翹?”沈大河跳腳道,“這不是找死嗎?”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他那個妹妹有多可怕。
嚴君仆笑起來,看著認真幹活滿頭大汗的沈大河,手扶柱子道:“你還蠻聰明,看來除了挑糞,還能做些別的。”
沈大河“嘁”了一聲,似乎本不屑,又似乎心舒暢。
他見過皇帝,過那樣的威嚴和疏離,明白自己是不可能做國舅了。
跟著嚴君仆做個隨從,有吃有酒喝,似乎也不錯。
馬匹在銅駝街停下,沈連翹低聲吩咐後跟隨的衙役。
“向下深挖,看有沒有地道。”
衙役聽命,沈連翹上前,拍響那座宅院紅的大門。
第一次注意到這院子,是因為魏元濟鞋子上沾的泥土;第二次,是因為修好了房子,卻並未見到主人。
該早些來看看的,就算破門而,也好過如今心驚膽戰。
沒有人開門,但大門並未上鎖,沈連翹推門而進,見照壁前的土已經被清理幹淨。
前廳的屋簷下有一堆黑的灰塵,看起來像是燒過紙錢。
“你來了?”猝不及防間,一個聲音從前廳傳出。
沈連翹猛然推開門,見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站在大廳中。他穿著黑的斜襟窄袖長袍,細長眼、矮鼻梁,麵容普通,卻著詭肅殺之氣。
這是沈連翹第一次見到韓涼。
最早沒有忘記名冊時,知道宮中有個衛名韓涼,是良氏族人。
可是也僅此而已。
京兆府外認下蔡無疾;生病時請來孫莊;孔佑去北地,寄信給葉萬鬆;蔚然出嫁,安排崔知黍隨行保護。
良氏族人已散作滿天星,除非必要,不可能一一見過,惹得朝廷懷疑。特別是,想當然以為,的族人,都是忠誠可靠的。
“你認得我?”沈連翹邁前廳。
雖然是秋天,韓涼卻在烤火。他的手在炭火盆上翻轉,拇指和食指並攏著,一線。
一灰白的,小蛇般細的線,從韓涼手心延長到地麵。
“認識,”韓涼道,“良氏的族長大人。”
沈連翹鬆了一口氣。
“既然認識,我讓你放下那繩子,你肯嗎?”沈連翹的聲音威嚴中不失溫和。
韓涼抬頭看著沈連翹,笑了笑。
“族長大人知道我為何烤火嗎?倒不是為了方便點燃引信,而是每到天氣,我的腳和胳膊,就會很疼。”他的臉上褪去了跟隨皇帝多年,暗殺探聽時的冷。像是在同老朋友敘舊,緩慢地說著。
沈連翹走近一步道:“既然如此,我請太醫為你醫治。”
“不必,”韓涼添進火盆裏一顆炭塊,輕聲道,“當初我的父母死在宜驛站,嬸娘要帶我搬到幽州去,我說大仇未報,怎敢離京。錦安十五年我十三歲,躺在黃河邊的冰雪上,等到狩獵的楚王經過,帶我回宮。我的寒疾是自己故意得的,每次疼痛時,我都在想,當年父親母親在大火中,也是這麽疼嗎?”
沈連翹麵悲戚道:“比這個還要疼。”
“哈,”韓涼嘲笑一聲,搖頭道,“你不會覺到,也不記得,不然你就不會帶領合族數百人為大周效命,更不會嫁給劉氏皇族!”
沈連翹出手,也烤了烤。
火焰滾燙,火舌隻要稍微接到皮,便覺得疼痛。如果這樣的火遍布全,如果在火中活活燒死,那樣的慘狀,不敢想,也不忍想。
夾竹桃的毒讓沈連翹幾乎站立不穩,在片刻的暈眩中,努力整理思緒,勸說韓涼。
“當年作惡的人均已伏法,楚王已死,楊桐陌恐怕也死在邙山了。這樣還不夠嗎?”
“不夠!”韓涼的聲音拔高幾分,“怎麽能夠?當年我藏在宜驛站外,親眼看到他們火箭,又進去絞殺。你見過用弓箭殺人嗎?長弓套著脖子扭上幾圈,窒息而死的人被割爛脖子隻剩下骨頭,流滿地。”
沈連翹盯著韓涼的眼睛,詢問道:“所以呢?所以就要做出比楚王更殘忍的事嗎?當年的良氏無辜,如今城中的百姓,豈不同樣無辜?劉瑯當年隻是一個七歲的孩子,他的父母兄弟同樣死在宜驛站。你報仇,能這樣報嗎?”
韓涼罩在火盆上的手微微抖,有一瞬間,他猶豫了一下。
“是啊,能這樣報嗎?”他的手靠近火焰,在難以忍的疼痛中著收回,又忽然笑了,“可是你不會以為,所有的良氏族人,都聽你的話吧?”
“不是聽話,”沈連翹道,“是有良知。”
韓涼搖了搖頭。
“你不知道我替楚王殺了多人。好人,壞人,忠臣,佞,老人,孩子,當你手上沾染足夠多的,良知是什麽,早就忘了。比如今日,你可知道有一引線通往大梁使館嗎?使館旁邊住著大周顯貴,更有幾皇族宅邸。燒起來,就都完蛋。”
沈連翹抬手了口。
心髒在那裏混地跳,快速而不規整,連帶著的呼吸都起來。
“你不要這樣,”沈連翹用盡力氣開口,“你見過芙蓉,就是你的堂妹。我們死去的父母已經不能複生,你從這裏出去,一聲妹妹,幫擇婿出嫁,再得到一個家。”
韓涼看著溫地笑。
因為這個笑容,他俊朗幾分,也鬆弛了些。
或許這是他十多年來,最放鬆戒備的時刻。
“族長大人,”他聲道,“請你離開。”
韓涼的手在炭火上揚起,手裏握著的引線抖著,沈連翹才發現那些引線有好幾,或許是通往不同的地方。
在恐懼和驚慌中最後勸道:“皇帝不會來了!你燒了也沒用!”
“你不知道,”韓涼道,“那些土堆在銅駝街那麽久,就是為了讓你發現。給良錦惜的隻言片語,也是為了讓你想到我。聽說族長大人你失去記憶了,就算你想不起來,也會有人告訴你。隻要你來了,他就會來。你聽——”
伴隨著這句話,門外傳來輕捷的腳步聲。門被撞開窗被砸破,孔佑和江流帶著衛尉軍衝進來,數十把弓弩對準韓涼。
“網之魚。”江流道。
韓涼笑笑,對孔佑道:“陛下,宜驛站的亡魂,等著你。”
他的手在火盆上方鬆開,引線盡數掉落下去。沈連翹不顧疼痛手,想要抓住引線。可縱使有火中取栗的勇氣,那引線燒得也又急又快。又去拽地上的,可韓涼上前,擋住了。
他的手中出匕首,向沈連翹揮來。
“翹翹——”後有一隻手抓住了沈連翹的襟,把向外扯去。與此同時,數把弓弩齊發,弩箭準確無誤地沒韓涼的,把他擊倒。
鮮在韓涼黑的服上散開,他通紅的眼睛定定地看著沈連翹,含笑說話。
“夫人懷你時,我還給你唱過……歌。”
“快走!走!”沈連翹牽住孔佑的手向外,可剛走一步,便昏厥過去。
“出去!”孔佑大聲喊道,他攔腰抱起沈連翹,同衛尉軍一起向屋外躲去。
猜你喜歡
-
完結6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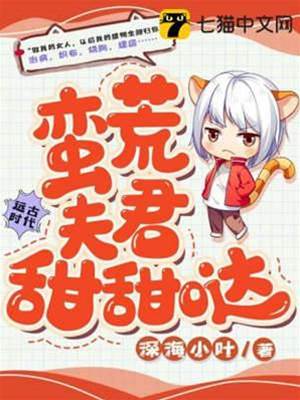
蠻荒夫君甜甜噠
薛瑤一覺醒來竟穿越到了遠古時代,面前還有一群穿著獸皮的原始人想要偷她! 還好有個帥野人突然出來救了她,還要把她帶回家。 帥野人:“做我的女人,以后我的獵物全部歸你!” 薛瑤:“……”她能拒絕嗎? 本以為原始生活會很凄涼,沒想到野人老公每天都對她寵寵寵! 治病,織布,燒陶,建房…… 薛瑤不但收獲了一個帥氣的野人老公,一不小心還創造了原始部落的新文明。
117.6萬字8 37504 -
完結114 章

村姑廚娘
苏秋睡了一觉,就从饭店大厨变成了瘦弱村姑。父母皆亡,底下还有三个年幼弟妹,家里穷的叮当响,还不时有人来讨债? 这日子实在是有些难过。 苏秋可不怕,大勺在手,银子我有。 谁敢欺负我,就让你尝尝菜刀的厉害! 银钱不愁,弟妹也可人疼,日子是越过越好。 眼瞧着姑娘到了出嫁的年纪,说亲的一个挨一个,连那京城官家公子都为了口吃食成天围着苏秋转。 山脚下的猎户开始着急了:媳妇这么优秀,会不会嫌弃我? 猎户奶奶恨铁不成钢,隔日找到苏秋:姐妹儿,看在都是祖国花朵的份上,你考虑考虑我孙子?以后你喊我奶奶,我叫你姐姐,谁也不耽误谁!
15.6萬字8 6222 -
完結524 章

重生后被迫嬌養黑蓮花
上輩子,姜柚錯過鎮北王世子蘇衍,遭親人陷害,渣男背叛,落了個被剖腹活埋的下場,連兩個剛出生的孩子也慘遭毒手! 一朝重生,回到命運轉折點,她果斷抱蘇世子大腿,改寫命運! 智斗姐妹,打臉主母,主持宗族,姜柚戰無不勝;發家致富,手撕渣男,攪亂朝局,姜柚步步為營。 這輩子,姜柚只想專心搞事業! 蘇衍:「撩完就跑,不合適吧?」 姜柚:「那你想要如何?」 「你嫁我,或是我娶你」 他們的相遇相知相許,早已是命中注定。
93.6萬字8 37926 -
完結942 章

重生我嫁給了未婚夫的死對頭
86.7萬字8 235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