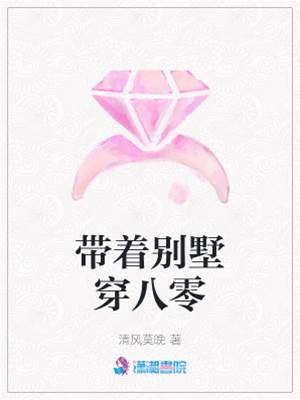《再度招惹》 第96 章 chapter96
閉的房門將楊舒徹底隔絕在外。
那些楊舒用謊言堆積起來的,名為“一家三口”虛幻泡沫頃刻間四散而去,好像站在坍塌的廢墟裏,孤立無援。
此刻楊舒才意識到,原來許校程可以這樣狠。
楊啟一直站在一旁,遲遲沒有上前。
猶豫半晌,才開口:“姐。”
楊舒背對著他抬手有些倔強的了一下控製不住的眼淚,麵對自己的弟弟,盡量保持著麵和理智,可角怎麽也扯不出一個得的笑。
楊啟見站在旁邊小象實在可憐,小臉哭的紅,一直低聲啜泣。
他走過去將小象抱起來,放到車裏安小孩兒的緒,幾分鍾後示意楊舒上車,他送他們回去。
車一直維持著抑的沉默,路過一個又一個路口,最後在楊舒家門前停下。
小象在路上時就睡著了,楊舒抱著他要去開車門,才發現車門鎖著。有些不解的看向駕駛座的楊啟。
滿是疲憊道:“想問什麽就問吧。”
楊啟是想問很多東西,那些他道聽途說的,無意中知曉的,資料查到的……他想不通,自己一向明理的姐姐怎麽會卷這樣一場糾紛裏。
他更驚訝於欺瞞家人長達六年的時間。
“姐,你又何必呢?”
楊舒沒說話。
楊啟低聲音說:“現在該怎麽辦?你怎麽辦?你又該怎麽和伯父伯母說清楚這件事?怎麽和小象說清楚許總不是他的爸爸,他爸爸另有其人?你真的太糊塗了。”
楊舒聽著他的指責,猛覺惱怒,“我能怎麽辦?!許校程他從一開始就不給我留後路,他公開宣稱和我沒關係,讓我丟臉又丟工作。他就是故意的,一開始就算計好的!我連工作都沒有,拿什麽去和蘇家爭養權?”
Advertisement
說著,越來越生氣,越來越偏激,“他算計好了一切,就等著把我往下拽,他想把我拽下去,去討好蘇家,討好蘇印。都說蘇印過的多艱難,可那些不都是自找的嗎?為什麽不幹脆死在外麵……”
楊啟聽不下去了,冷聲打斷,“夠了!”他目滿是陌生和失,“你為什麽會變這副模樣?楊舒,你怎麽變的這麽是非不分?醒醒吧,拽你下來的從來不是許校程,破壞你現在生活的也不是蘇印。是你自己,從來都是你自己。”
楊舒急促呼吸著,自己弟弟的指責像是耳扇在的臉上。
覺得痛苦,又覺得迷茫。
懷裏小象睡的很,小手不安的拽著的服。
強迫著自己冷靜下來,那些失控時口而出的話連自己都覺得匪夷所思。
“我不是壞人。”半晌,說。
楊啟一言不發,隻是有些傷心的看著。
“我不是壞人,我不是故意要把事弄今天的樣子。”
楊舒覺得所有的事都不是故意的,隻是在每個選擇的關口,都選了對自己最有利的選項。
蘇展車禍後發現懷孕,沒有勇氣和能力生下孩子。約好了流產手,但看到病床上永遠不可能醒來的蘇展時,又覺愧疚。許校程的出現讓多了一個選項,既可以留下孩子,又可以和喜歡的人相。毫不猶豫的將所有難題拋給許校程,讓他承擔。
將那筆錢私自扣下,沒拿給蘇印時,的想法也很簡單,自己好不容易才和許校程有了一些牽絆,蘇印既然已經和許校程分開了,就不要再藕斷連。這樣,對大家都好。
醫院見懷孕的蘇印,躲在樓梯口避而不見,得知蘇印流產後更覺得鬆了一口氣。因為知道許校程的格,一旦讓他發現蘇印也懷孕了,肯定會和蘇印複合,那和蘇展的孩子應該怎麽辦?怎麽辦?
Advertisement
不像蘇印,有許校程的偏,也有蘇展的維護。
隻能想盡辦法對自己好一點兒。
“我想讓自己過的不那麽艱難,這有錯嗎?”問楊啟,也在問自己。
人人都自私,人人都慕強,哪怕平時說的再大義凜然,可真到選擇的關頭,還是會做一個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
楊舒覺得,沒做錯。
隻怪世事無常,差錯之下,蘇印因為的選擇盡苦楚。
楊啟聽完的話片刻沉默,“姐,自己沒有錯,但你也不應該傷害別人。通過傷害別人得來的東西,遲早有一天要還回去的。走到這一步,你不無辜。”
建立在謊言之上的名利、工作、滿家庭,終究不屬於。
楊舒啞口無言。
楊啟說:“這個孩子,估計也就是你的籌碼和手段。你要是不好好養,就還給蘇家吧。”
楊舒有些怔愣,“連你也要這麽說嗎?”抱了小象,啞聲道:“蘇印的痛苦,不是我一個人造的。”
楊啟明白的意思,有些疲憊道:“姐,許校程現在的煎熬,並不比你。”
楊舒聞言,幾次言又止。
-
時隔近一年,蘇印再一次接了電視臺的采訪。
在“致鬱魔畫”事件長時間發酵以來,第一次正麵回答了有關畫作的問題。
網絡轉載的視頻裏,那個傳言中的“天才畫家”第一次在公眾麵前臉。
一簡約的裝扮,白皙漂亮,眼神純粹疏離,看著有些不善言辭。
對主持人說:“想通過這次機會,來回答一下很多人關於那些畫作的疑……那件事引起了不風波,網友的討論我都有看到,藝創作是自由的,可畫作展出麵向公眾,除了藝本外,就應該承擔起它的責任。我為自己的疏道歉。”
Advertisement
聲音平緩,一一回答主持人的問題。
在解釋“致鬱魔畫”的創作機時,說,“……在那些畫裏,如果有人看到了希,那是真的。如果有人看到了痛苦,那也是真的。畫下那些畫時,我正在非常黑暗低穀的階段,痛苦無法宣泄時,隻能通過畫筆。那些畫一定程度上救了我,在最絕的時候,一次次將我從邊緣拉了回來。很多人說它是‘致鬱魔畫’,其實它最初的名字是‘深仰’,在深淵,也在仰。”
主持人一直安靜聽蘇印的解說,或許是被上疏離破碎的神態染,主持人溫聲詢問,“那你現在還好嗎?”
是否從那些痛苦無中走出來了?
蘇印一向話,隻有在談起創作時才顯得不那麽沉默。
聽著主持人的問題,安靜片刻,對著鏡頭出一個很淺的笑,“有些痛苦注定無法走出,可是我現在已經能夠坦然的去麵對、接。”
半年以前,滿心瘡痍四漂泊時,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可以直麵那些畫作,能坦然解說它們的來曆。
蘇印覺得,這已經很好了。沒必要刻意去忘、去丟棄,走過的路總會留有痕跡。
當主持人問,“你覺得,自己最大的進步是什麽?”
蘇印不著邊際的答,“能不退步就是進步吧。最大的進步……可能就是,我不再執著的想在裏得到救贖。”
采訪時間並不長,在結束時主持人問,新一的畫展是不是要提上日程了,蘇印說暫時沒有這個打算,想要休息一段時間,可能會去遊學。
主持人追問會去哪裏,蘇印沒有。
-
那段采訪視頻在網上的討論度不低,向恒看到後跑來問蘇印,“你打算遊學的事,怎麽沒和我說?”
Advertisement
蘇印淡然道:“你最近忙著結婚,也沒問啊。”
向恒抱歉一笑,中斷了話題,電話掛的很快。
蘇印開始搬家了,想在出國之前多陪陪陳眉。
日常東西已經在陳眉的幫助下搬的差不多了,公寓那邊還剩了畫架和一堆料。
趁著空閑,蘇印又去了一趟公寓,將這些東西帶了回來。
車停在家門口,從後備箱裏搬出這些東西。將東西放到一邊,關好後備箱,剛直起,腳邊的東西就被提起來了。
回頭看。
許校程已經拿起東西,他也不知道突然從哪裏來的,穿著正裝,像是剛結束工作。
蘇印鎖上車子,轉回來拿他手裏的東西。許校程沒給,隻是問:“要拿到樓上?”
蘇印點頭。
許校程說:“我送你上去。”
蘇印安靜看他。
“你一個人也拿不上去,我就送你到門口。”許校程說。
選擇最難做,當決定出國後,蘇印對許校程倒沒有之前的排斥。
沒拒絕,走在前麵帶路。
陳眉還住在原來的地方,這裏除卻不久前,許校程也來過一次。
六年前他就是到這裏來找的蘇印,站在不遠的老槐樹下給蘇印打了電話。
現在,連那顆老槐樹都還在,外麵早已經高樓林立,可是這個小區還是沒怎麽變,還是原來沒超過十層的樓房。
許校程跟在蘇印的後,進了公寓樓,才回頭說:“電梯壞了,得走樓梯。”
許校程愣了一下,隨即淡然的點點頭,隻“嗯”了一句。
蘇印家在六樓,兩人一前一後的往樓上走。蘇印一向四不勤,嚴重缺乏鍛煉,走到三樓有些累了。
許校程什麽話都沒說,還是麵如常的拎著那些東西跟在後。
他一直沉默又淡定,看蘇印停下,臉上才出一些詫異。
問:“怎麽了?”
蘇印看他,目又移向他的手裏。
頓了頓,說:“……我好像記錯了,電梯應該是修好了。”
許校程也一頓,目在的臉上停頓片刻,看著的眼睛。忽的勾了角:“應該?”
蘇印有些尷尬,可是目又直視回去。“修好了,去乘電梯把,我走不了。”
語氣平靜,又有些強裝的淡然。也沒等許校程反應,就先一步去了電梯間。
許校程看了眼手裏的東西,又看著蘇印的背影,笑著搖搖頭,跟在了的後。
到樓上,許校程還沒將東西遞給,蘇印就已經打開了門。
“放到客廳。”蘇印說。
許校程跟著進了房間,屋子裏麵空空的,並沒有人在。
再沒有招呼他,隻是把一些畫筆拿到了臥室裏麵。
許校程就站在客廳裏,左右環顧著。下午照進客廳,明燦燦的一片。旁邊的櫃子上,還放著蘇印和母親的合影。
“近期是要留在北京?”許校程問了,但更像是在試探。
臥室的門開著,蘇印正彎著腰收拾東西,應了句:“不一定。”
許校程又問:“為什麽?”
蘇印被他問的一愣,什麽為什麽?
“蘇印,你能告訴我你在想什麽嗎?”
蘇印站在門邊,停住了作。隻是安靜的看著他。
“你在想什麽,你直接說出來。我猜不出來你現在的心思,也猜的很累。這麽多年了,你還是一樣,什麽事都不會說,隻是讓我猜。可是蘇印,我現在真的猜不出來。”
不猜不出來,他快被蘇印的態度整瘋掉了。
他快瘋掉了。
半晌,蘇印才將目移到了別。
“我不懂你在說什麽。”答。
許校程淡淡的笑笑,有些無奈。
怎麽會不懂,隻是不願意回應罷了。
他走過去,到了的麵前,低頭看著。手想的臉,可是又收了回來。
“蘇印……”
他剛出口,一陣敲門聲打斷了他的話。
兩人一齊朝門口看過去,都頓了幾秒。蘇印最先反應過來,扯著他就往臥室走。
將人拉進臥室裏,“你不要出來。”
許校程頓了幾秒,問:“做什麽?”
敲門聲停了一會兒,又繼續響起來了。蘇印一手還握著門把,一手將許校程往臥室裏麵推了推,又叮囑他一次:“你別出來。”
許校程看是真有些慌了,沉默了片刻,點點頭。
蘇印開門出去,又立即拉上了房門。
許校程背靠著門邊站了一會兒,踱步到了裏麵。
臥室並不太大,左邊靠牆的位置放著書桌和一個小型書架,上麵擺滿了書。許校程走過去仔細看了看,發現這些書都有點舊了,並且其中也夾雜著一些練習冊。
這些都是之前的東西,房間裏的很多東西都已經顯得有些陳舊。
是真的很多年都沒有回家,這裏還保持著原樣。
許校程對眼前的空間是有一些悉的,之前他來過一次。
蘇印去開了門,門外站著的母親一時間有些張。
陳眉走進來,邊換鞋邊說:“忘記帶鑰匙了,幸好你在家。”
蘇印有些張的站在一旁。
陳眉換好鞋,直起就看到蘇印有些不正常的神。將手裏的拎著的菜遞給蘇印,問:“怎麽這麽久才來開門?”
蘇印“啊”了一聲,眼神卻不控製的向自己的臥室瞟了一眼。
“我······打電話,沒聽到。”
神淡淡。
陳眉繞開進來,到了客廳。
蘇印問:“今天怎麽這麽早就回來了?”
比以往正常下班的時候都要早,剛才蘇印聽到敲門聲的時候還愣了一下,想著不大可能是母親,但是又做了最壞的打算,才讓許校程別從臥室裏出來。
現在看來,這個決定對到不能再對了。
陳眉倒了杯水,自顧自的喝起來。不知怎的,蘇印覺得母親的臉不是很好。
“今天是報名,名報完開了個會就回來了。”陳眉說。
蘇印“哦”了一聲。
低著頭想了一會兒,手去翻裝著菜的袋子。看了半天,開口:“媽,你沒買啊,我想吃糖醋排骨。”
“昨天買了,冰箱裏有。”
蘇印沉默。翻袋子的作也停下了。
“我還想喝你煮的魚湯,家裏沒魚吧?”
陳眉不知是工作累了還是怎麽了,手了眉心。
“我們去買魚吧。”蘇印說。
陳眉放下了手裏的水杯,拍拍旁的位置,“小印,先過來陪媽媽說幾句話。”
蘇印將袋子係好,還工工整整的打了個結放到一邊。
一步一步不不慢的朝著母親走過去,以往沒覺得,現在才深切的到什麽做“做賊心虛”。忍著緒,盡量讓自己鎮定,不去再看臥室。
走到母親邊坐下來,“說什麽呀?”
陳眉手了蘇印的頭發,很是溫和的看著蘇印。
是真的想和蘇印好好聊聊,陳眉覺得自己好友的兒子趙子睿是真心不錯,子直爽,為人簡單。可是這都撮合這麽長時間了,原以為還是有點希的,結果今早給趙子睿打電話的時候人家卻好像突然就沒多大熱了,說話也是吞吞吐吐的,言外之意就是他和蘇印不合適。
陳眉委婉的問他哪兒不合適,趙子睿隻說姻緣這東西得看緣分。
陳眉了解好友的兒子,能這麽說話肯定是蘇印哪裏又做的出格了。
“小印,你給媽媽說說,子睿那孩子怎麽樣?”陳眉問。
蘇印眼可見的皺眉。
“這問題你之前問過我。”
“那你就再說一次,仔細想想再回答。”
蘇印倒真是認真想了一會兒,說:“我和他,沒戲。”
房間裏格外安靜,許校程剛從書架上出一冊書。
猜你喜歡
-
完結566 章

顧先生的金絲雀
c市人人知曉,c市首富顧江年養了隻金絲雀。金絲雀顧大局識大體一顰一笑皆為豪門典範,人人羨慕顧先生得嬌妻如此。可顧先生知曉,他的金絲雀,遲早有天得飛。某日,君華集團董事長出席國際商業會談,記者舉著長槍短炮窮追不捨問道:“顧先生,請問您是如何跟顧太太走到一起的?”顧江年前行腳步一頓,微轉身,笑容清淺:“畫地為牢,徐徐圖之。”好友笑問:“金絲雀飛瞭如何?”男人斜靠在座椅上,唇角輕勾,修長的指尖點了點菸灰,話語間端的是殘忍無情,“那就折了翅膀毀了夢想圈起來養。”
159.6萬字8 16339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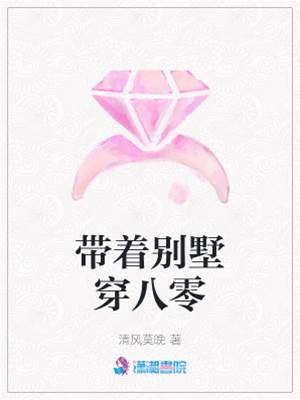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5946 -
連載830 章
厲總,夫人不想復婚還偷偷生崽了
姜彤剛辦理了離婚,后腳就發現她懷孕了。兩年過去,看到這條新聞的姜彤,趕緊藏好了和前夫長得如出一轍的小包子。藏不住了,只能帶著兒子跑路。那個殺伐決斷的男人氣勢洶洶堵在門口,直接抱起她往床上丟。“想帶我的崽跑去哪?嗯?”“我錯了……唔。”-小劇場:很久之后,姜彤去南山祈福,才看到厲璟辰在離婚那年掛在月老樹的紅條。
146.9萬字8.18 145547 -
完結234 章

蝴蝶效應
雙重生 雙向救贖 ----------------------------- 宋郁自縊而亡的消息炸裂在一個普通的清晨,翻涌、龜裂、燃燒了一個月后歸于平息,人們開始慢慢接受這位娛樂圈的天之驕子、最年輕的大滿貫影帝已經逝去的事實。 只有周雁輕,他不相信那個他視如人生燈塔的人會
38.8萬字8.18 243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