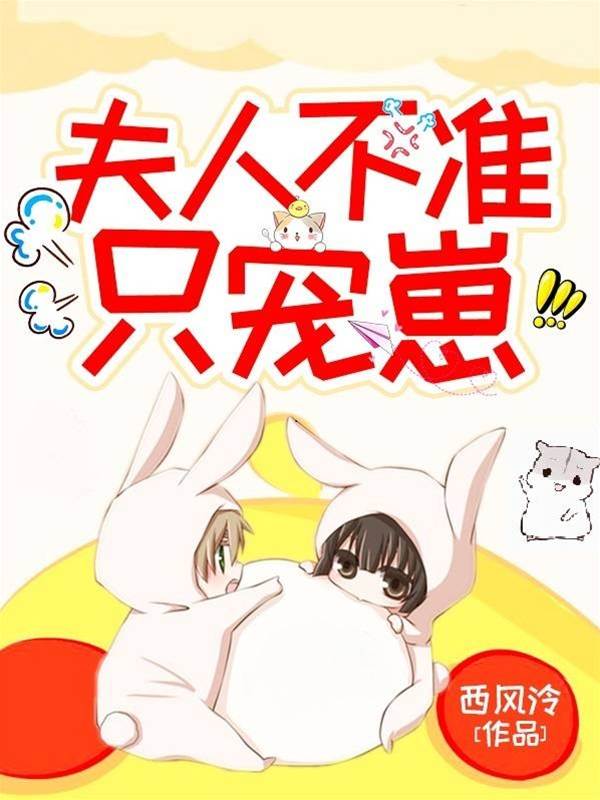《池中歡》 第20章:蒼蠅
祝鳶唱完歌下班回家,看見小區門口站著一個有些悉的人。
瞇了瞇眼,才發現是陳明恩。
陳明恩站得筆直,面容淡淡的,眼神也沒什麼緒,似乎是跟著池景行跟久了,整個人的氣質和他如出一轍。
祝鳶知道他是在等自己。
走去他旁,“陳先生。”
陳明恩頷首道,“祝小姐,池讓我在這里等您,把這個給您。”
他拿出一張黑金卡來,全黑磨砂的質地,卡上沒有一個多余的字,只在右下角有一個金的池。
祝鳶接過那張卡,垂眸看著,不知道心里在想什麼。
“祝小姐,這是星國際的黑卡,額度不限,您可以去購置一些喜歡的服首飾。”
周日的聚會,作為池景行的伴,需要有足夠匹配他的外形和穿著。
祝鳶和陳明恩道了謝,回家之后接到了池景行的電話。
他在煙,吐了口氣。
“回家了?”
祝鳶“嗯”了一聲,“池喜歡什麼樣的禮服?”
池景行瞇了瞇眼。
“你今天穿的紫,很好看。”
祝鳶心下了然,“我知道了。”
他忽然又低低笑了一聲。
他每次這樣笑的時候,祝鳶都覺得心里有些發,好像他又在醞釀著什麼壞主意。
Advertisement
但其實,他好像從來沒有對壞過。
祝鳶正打算開口和他說晚安,卻聽見那頭傳來一道有些妖嬈的聲,“池還喝嗎?”
的話停留在嗓間,耳畔已經響起“嘟、嘟、嘟”的聲音。
他掛斷了電話。
祝鳶放下手機,平靜地走進浴室里洗漱,回到床上,調好了次日的鬧鐘,關燈。
……
周六一早,祝鳶給時麥打了個電話。
#每次出現驗證,請不要使用無痕模式!
沒有買過禮服,也不太懂品牌質一類的東西,只能求助時麥。
時麥倒是樂得想陪,挽著一路嘰嘰喳喳。
“你最近忙死了,除了睡覺就是工作,我都不敢打擾你。”
祝鳶笑了笑,“我比別人浪費了兩年,要多花點時間。”
時麥有些心疼地握了握的手,“鳶鳶,你別給自己太大力,那不是你的錯,人生是馬拉松,不是短跑,兩年而已,在你的生命里不值一提。”
是啊,生命是馬拉松,不是短跑。
但如果不跑快一點,再快一點,可能連獲得馬拉松比賽的資格都沒有。
缺錢的事沒有告訴時麥,不想為任何人的負擔。
星國際是海市最頂尖奢侈的國際商場,里面的服飾除了一線國際品牌外,還有不高定的工作室。
Advertisement
時麥一件一件地陪挑。
祝鳶拿起一件淡紫的抹長,在前比劃了一下,咨詢了時麥的意見后走進試間。
再出來時,祝鳶原本就白皙發亮的在淡紫的襯托下愈加細膩,長上細小的碎鉆閃耀刺眼,的魚尾設計將曼妙的材勾勒得淋漓盡致。
時麥掐著下上下看了看,“很漂亮,可是不夠艷誒,沒有把鳶鳶你的絕世貌徹底展現出來。”
祝鳶看了看鏡子里的自己,想起池景行說的話。
“他喜歡紫。”
時麥頓時出一副了然于心的模樣來,壞笑著挑了挑眉,對著眉弄眼。
“嘖嘖嘖,為悅己者容,你這副模樣,簡直就是為丈夫心
打扮自己的小妻嘛。”
祝鳶卻只是有些輕笑出聲。
“拿人錢財,忠人之事罷了,”拉開簾子走進試間,“小姐,這一件,謝謝。”
時麥看著消瘦輕挑的背影,淺淡的紫在的上,心里忽然一頓。
總覺得,鳶鳶穿上這件禮服的樣子,有些眼。
皺眉想了想,卻怎麼也想不起來。
祝鳶走出來,拿著黑卡結賬,看了一眼,“想什麼呢?”
時麥搖搖頭,又仔細地想了想,半天沒得出個結果來。
罷了,聳聳肩,可能是之前看過的時裝展有類似的款式吧。
Advertisement
買好禮服,祝鳶接到了陳明恩的電話。
陳明恩恭恭敬敬,沉聲道,“祝小姐,池前段時間為您定制的首飾已經到了,現在放在星國際四樓的yul收藏中心里,池讓您去試一試。如果您不方便的話,我現在去取首飾給您送到家里。”
祝鳶看了看樓道索引,道,“不用了,我現在就在星國際,我自己去試吧。”
陳明恩道,“好的,到時候您直接出示黑金卡就好了。”
祝鳶道了一聲謝,掛斷電話。
時麥挽著的手咬牙切齒,“我好恨,我也好想要!”
祝鳶揶揄地看了一眼,“你時家大小姐想要什麼東西,家里沒有啊?”
時麥撇撇,“自己買來的哪有別人惦記著買來送你更難得啊。”
祝鳶不由得失笑。
上了四樓,o足足占據了接近一半的空間,歐洲皇室的裝修風格,帶著中古的味道,一件件珠寶首飾鑲嵌在防彈玻璃,幽暗的燈打在上面,像是古老神話里的寶藏。
祝鳶一眼
#每次出現驗證,請不要使用無痕模式!
就看見了位于收藏大廳正中央的那條淺紫的寶石項鏈,懸掛在優雅的模上,無聲靜默地注視著周遭的一切。
下一秒,看見了一張完全不想看到的臉。
賀嶼的母親杜英就站在那條寶石項鏈一旁,和幾個看上去打扮不俗的太太們談笑風生,旁邊站了兩個柜姐,微笑地為們服務。
Advertisement
一位太太似乎很喜歡那條寶石項鏈,輕蹙著眉,“真的不可以再預定一套嗎?價格不是問題,時間上我也可以等。”
柜姐微笑回答,“周太太,這條項鏈是貴賓從國外請設計師定制的獨家款式,全球只有這一條,實在是沒有辦法的。”
一旁的杜英正要說話,眼神一瞥,便看見了不遠正緩緩走過來的祝鳶。
杜英挑了挑眉,上下打量了祝鳶幾眼,從鼻間發出一聲冷冷的嗤笑。
旁的太太們連忙問怎麼了。
杜英嘲諷地笑了笑。
“沒什麼,只是在這麼好的環境里看見一只蒼蠅,覺得有些掃興。”
時麥瞇了瞇眼,祝鳶卻拍拍的手,示意沒事。
杜英周圍的太太們哪個不是人,聽見杜英這樣說,瞬間轉過頭看過來。
一看見祝鳶的臉,太太們瞬間出幾分驚艷的表來,同為豪門夫人,們一向最忌諱的,就是外面年輕姑娘們的貌,丈夫在外面如何們管不到,于是只能把氣撒在同為人的年輕姑娘上。
周太太上下打量了祝鳶幾眼,笑著問杜英,“這位,你認識?”
杜英嗤笑一聲。
“不過是從前圍著我兒子到轉的一只蒼蠅罷了,真晦氣。”
祝鳶淡淡地笑了笑,盯著杜英刻薄的臉。
“被蒼蠅圍著的,可不是什麼好玩意兒啊。”
猜你喜歡
-
完結143 章

重生之大佬的復仇嬌妻
前世,她受人蠱惑,為了所謂的愛情,拋棄自己的金主,最后身敗名裂,慘死在家里。 重生后,她只想抱著金主大大的大腿,哪里也不想去。可后來發現,金主抱著抱著,好像不一樣,她有點慌,現在放手還來得及嗎? 某天,金主把人圈在懷里,眸光微暗,咬牙切齒說“叫我叔叔?嗯?” 她從善如流,搖頭解釋,但他不聽,把人狠狠折騰一番。第二天,氣急敗壞的她收拾東西,帶著球,離家出走。
34.1萬字5 41505 -
完結968 章

總裁我不要辦公室戀情
一場奇葩的面試,她獲得了雙重身份,工作日她是朝五晚九忙到腳打後腦勺的房產部女售樓,休息日她是披荊斬棘幫上司的生活女特助。 他們說好只談交易不談感情,可突然有一天,他卻對她做了出格的事……「商總,你越線了」 「這是公平交易,你用了我的東西,我也用了你的」
255萬字8 19705 -
完結10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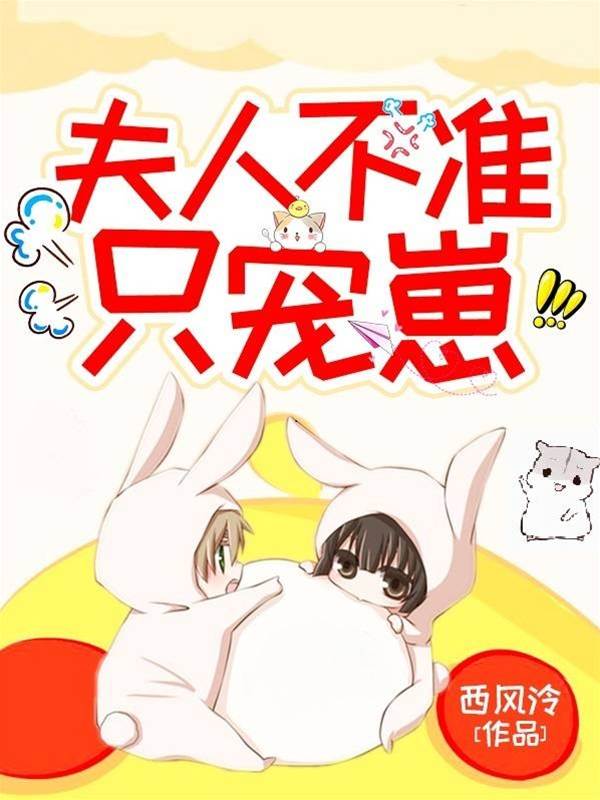
夫人不準只寵崽
南悠悠為了給母親治病為楚氏集團總裁楚寒高價產子,期間始終被蒙住眼睛,未見楚寒模樣,而楚寒卻記得她的臉,南悠悠順利產下一對龍鳳胎,還未見面就被楚家接走。
24.6萬字8 7222 -
完結389 章

炙吻
今年18歲的許芳菲,父親早逝,家中只一個母親一個外公,一家三口住喜旺街9號。 喜旺街徒有其名,是凌城出了名的貧民窟。 許母開了個紙錢鋪養活一家,許芳菲白天上學,晚上回家幫母親的忙。 日子清貧安穩,無波無瀾。 後來,樓下搬來了一個年輕人,高大英俊,眉目間有一種凌厲的冷漠不羈和刺骨荒寒。男人經常早出晚歸,一身傷。 故事在這天開始。 * 又一次相見,是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原,雄鷹掠過碧藍蒼穹,掠過皚皚白雪。 許芳菲軍校畢業,受命進入無人區,爲正執行絕密行動的狼牙特種部隊提供技術支援。 來接她的是此次行動的最高指揮官。 對方一身筆挺如畫的軍裝,冷峻面容在漫山大雪的映襯下,顯出幾分凜冽的散漫。 看他僅一眼,許芳菲便耳根泛紅,悶悶地別過頭去。 同行同事見狀好奇:“你和鄭隊以前認識?” 許芳菲心慌意亂,腦袋搖成撥浪鼓,支吾:“不。不太熟。” 當晚,她抱着牙刷臉盆去洗漱。 走出營房沒兩步,讓人一把拽過來給摁牆上。 四周黑乎乎一片,許芳菲心跳如雷。 “不熟?”低沉嗓音在耳畔響起,輕描淡寫兩個字,聽不出喜怒。 “……” “你十八歲那會兒我執行任務,拼死拼活拿命護着你,你上軍校之後我當你教導員,手把手教你拼組槍支,肉貼肉教你打靶格鬥,上個月我走之前吊我脖子上撒嬌賣萌不肯撒手。不太熟?“ “……” 鄭西野涼薄又自嘲地勾起脣,盯着她緋紅嬌俏的小臉,咬着牙擠出最後一句:“小崽子,可以啊。長大了,翅膀硬了。吵個架連老公都不認了。” 許芳菲:“……”
62.8萬字8.18 159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