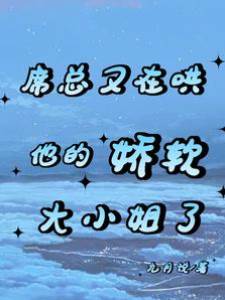《經年莫忘》 第四十三章
楚行微微張口,最後仍然沒有發出聲音來。
楚行從清早到傍晚,都一直坐在床沿。中間罌粟連同小貓都已經小憩了好幾覺,然而每次醒來,總是第一眼就能看到他的影。罌粟不小心對上他的視線時,還能看到他正溫和地著,衝著微微一笑。
然而每次罌粟又都默不作聲地別開眼。
楚行知道一定滿心滿眼都希他能離開臥房。發病後,心思比之前好猜許多。希他離開的眼神此刻就明明白白寫在的臉上,被楚行看到,卻假作不懂。
兩個人從早上對坐到夕西下,直到最後一霞也掩去,罌粟終於忍不住了。
一天沒有吃東西,早已經得不了,卻仍是固執地不肯開口。這幾天思維遲緩,也閉得有如貝蚌,除去在夢中,平日裏尚未開口說過一句話。罌粟又看了一眼往昔總是擺一盤糕點,今天卻空無一的床頭,把眉心擰了擰,在楚行牢牢鎖住的目底下兀自歪頭想了一會兒,最後麵無表地躺下去,做出繼續睡覺的姿勢。
楚行在這時微微了一下,罌粟半閉上的雙眼頓時睜開,警惕地著他。楚行探過來,罌粟瞳孔微微,下意識便往床的更深躲去,卻快不過他的手,下一刻發頂便被楚行輕輕了一下。
他的作很輕,又快,不過一下就收回。罌粟的牙關咬,聽見他低聲的名字,臉上微笑容著問:“了沒有?”
罌粟自然不答,又往裏麵靠了靠,那個樣子,明顯是希能把他屏蔽在半米之外。楚行沒有強求,隻又笑了一下,低低地說:“嗯?了沒有?”
Advertisement
他的話音剛落,便聽到罌粟的肚子了一下,即便是隔著被單,也能清楚聽見。
罌粟雖然神誌懵懂,卻也知道這是糗事,臉上慢慢紅起來,最後蔓延到脖頸。側過去,背對著他,楚行不肯就此放過,湊過去,角含笑,在耳邊說道:“難道我不問你,你就要一直下去都不說話?”
罌粟像是本沒有聽進去,隻注意到他的挨近,頗為不自在地了,繼續往裏麵靠了靠。楚行的笑容收斂了一半,輕輕地說:“罌粟,同我說句話,一句話就好。好不好?”
罌粟閉著眼,睫深長,一不。楚行深深看著,又過一會兒,笑容重新浮上來,語氣較之方才更溫和:“乖,我現在去端魚粥來給你吃好不好?”
他說完,便站起離開了臥房。走到門口的時候又停下,回過頭來看了一眼。
罌粟正轉過半邊子來著他,本來是有些放鬆的樣子,見他頓住腳步,臉上立刻顯出警戒,又是驟然神經繃的模樣。
楚行的眼神又是微微一深,沉默了一下,給做了個安的姿勢,接著走出去,從外麵合上了房門。不過多時他又回來,這次手裏端了一碗香氣四溢的魚粥。
那碗魚粥的香味齊全而好,罌粟得肚子發慌,自楚行進來後,就一直盯著那晚魚粥瞧。楚行在床沿坐下,罌粟的眼神也順著那碗魚粥而落到床邊。楚行看一眼,微微一笑,舀了一小匙近罌粟邊。
罌粟終於回過神來,下意識往後一。
楚行眼神不變,隻聲哄:“不燙。吃一口,好不好?”
Advertisement
罌粟看他一眼,猶豫一會兒,仍是不肯上前。楚行低聲說:“你看,隻是吃東西而已,我什麽都不做。乖,就吃一口,好不好?”
他反複說了多遍,語氣都是低沉和緩。維持著手勢不變,眼神中則出他真的什麽都不會做的意思。罌粟又看他一眼,眼中糾結的意味越來越濃,直到勺中魚粥變得溫涼,終於試探著探過來一點點。
楚行耐心等著,一直到一點一點完全靠過來,微微斂起盯著他看的目,而後低下頭,把那勺魚粥自己咽下去。
他又舀了一小勺,喂到邊。如此重複多次,盡管過程緩慢,罌粟亦存著警戒,到頭來還是令粥碗見了底。楚行把粥碗放下,過懷中手帕,想要拭罌粟的角。這次的頭偏了一下,他的手落下去,隻到了空氣。
楚行看一眼,一言不發地把手帕收了回去。罌粟有些惴惴不安地看他一眼,被他捕捉到,衝著微微笑了一笑。
罌粟見他未有懲罰,又默不作聲地把視線別開。察覺到楚行又有作,未及扭頭過來,臉頰已經被楚行用拇指輕輕了一下。
他的作一即分,在罌粟眉心擰起來之前,楚行又低低喚了一遍的名字:“罌粟,等你好起來,我們……”
他的話說到一半,見罌粟本沒有興趣聽,便停住。罌粟兀自翻躺下去,連脊背都出今天再不想同他打道的意思,楚行看一眼,沒有再說什麽,終究離開。
又過了幾日,鄢玉前來複診,在臥房門口看到的一幕便是罌粟手中抱著一隻小貓,楚行在喂罌粟吃糕點的樣子。
Advertisement
楚行的作緩慢而耐心,隻三小塊糕點就花了十多分鍾。等到把東西喂完站起,見罌粟一隻子蹭了下來,又俯給穿子。罌粟卻不肯配合,他一到的腳,罌粟就下意識往後一。楚行眉目不,一邊觀察著罌粟臉上的反應,一邊低聲哄著,過了兩分鍾,罌粟終於有所鬆,他才輕輕撈過的腳,重新給把子套了上去。
鄢玉把這些看在眼裏,臉上似笑非笑,始終一言不發。直到楚行重又站起,他才打破屋中的氣氛,公事公辦道:“我需要清場複查。楚爺請暫時回避先吧。”
二十分鍾後鄢玉從樓上下來,看到沙發上的楚行,角不不地一撇,皮笑不笑道:“這才一周時間,罌粟居然就能配合到你這種程度。楚爺,你該不會又是耍了什麽手段了吧?”
楚行不答,隻問:“況怎麽樣?”
鄢玉看他一眼,嗤笑了一聲,不客氣地在一旁沙發坐下,說:“還能怎麽樣,不就是老樣子。打碎回爐重造這種事可不是一日之功,楚爺切記急不得。再況且……”
他有意停頓一下,慢吞吞剝了果盤裏的一隻葡萄,才又嘲諷著說下去:“再況且,現在罌粟因神誌不清而意誌薄弱,你才能這麽哄騙。要是等清醒了,你認為還會這麽順從嗎?到時候估計就算你給多隻貓,都不會再看你一眼。所以說,倒還不如就這麽昏沉著呢,反而對大家都有好。您說是不是?”
楚行聽出他話中的刺,卻不置可否,隻拿過幾上的茶盞飲茶。過了一會兒,鄢玉扶了扶眼鏡,又直截了當地說道:“不管你用什麽手段,我隻建議你,不要用任何哄騙或者強的伎倆。這些手段就算現在管用,可等到醒了,那就變後患無窮。”
Advertisement
楚行聽了,意味不明地笑了笑,抬起眼皮看看他,平鋪直敘地說:“聽說有人想手別人的婚事,派人暗地裏調查的時候怎麽沒想過這個問題?”
鄢玉臉半分不變:“我自己的事我有分寸,別拿我的跟你的比。”
楚行低頭抿一口茶,再抬起眼皮的時候臉淡淡地:“沒什麽區別。你要是不手,你那位前友就永遠不會離婚,你就永遠沒有重新上位的可能。我現在要是不做些什麽,等罌粟醒了,我倆的關係不會有毫好轉,還是會離開。我如果做了些什麽,最差的打算也不過是仍然離開我,除此之外,隻有更好,不會更壞。”
“至於手段,凡是對現狀造改變的都是手段。而凡是能達到目的的,就都是好的手段。這些手段我要是現在不用,以後連用的機會都沒有,哪兒去談後患無窮。”
猜你喜歡
-
完結1792 章

厲少,夫人又把你拉黑了
結婚前,被逼娶妻的大佬對她不屑一顧:“記住,你隻是我爺爺派來照顧我的女人,我不愛你,更不會碰你。”結婚後,大佬穿著圍裙拿著鍋鏟一臉氣憤:“不準穿短裙,不準私下去見前男友,不準陪客人喝酒,不準......”她淡淡回眸:“不準什麼?”大佬被看的心下一顫,但想到自己一家之主的地位,還是霸氣道:“不準再讓我跪鍵盤!”
310.8萬字8.67 1247466 -
完結207 章
壞男強吻:契約甜心
她失戀了,到酒吧買醉後出來,卻誤把一輛私家車當作了的士。死皮賴臉地賴上車後,仰著頭跟陌生男人索吻。並問他吻得是否銷魂。翌日醒來,一個女人將一張百萬支票遞給她,她冷笑著將支票撕成粉碎,“你誤會了!是我嫖的他!這裏是五萬!算是我嫖了你BOSS的嫖資吧!”
41.3萬字8 38552 -
完結1165 章

傅少的替嫁寶貝
一場陰謀,她被迫替姐出嫁,新郎是頂級豪門的傅家三少。傳言,傅三少體弱多病,面容丑陋。可是,眼前這個帥得人神共憤、身材堪比男模的男人是誰?!下屬來報:“傅少,太太被投資方黑幕了。”傅少:“追資,黑回去!”下屬再報:“傅少,網友在湊太太和一個男超模的cp。”傅少到言晚晚直播間瘋狂刷飛船:“乖,叫老公!”言晚晚以為這一場婚姻是囚籠,他卻把她寵上天。從此以后,劈腿前男友和渣姐,要尊稱她一身:小舅媽!(1v
191.7萬字8 43102 -
完結4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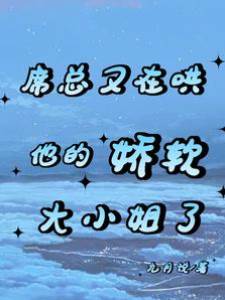
席總又在哄他的嬌軟大小姐了
矜貴腹黑高門總裁×嬌俏毒舌大小姐【甜寵 雙潔 互撩 雙向奔赴 都長嘴】溫舒出生時就是溫家的大小姐,眾人皆知她從小嬌寵著長大,且人如其名,溫柔舒雅,脾氣好的不得了。隻有席凜知道,她毒舌愛記仇,吵架時還愛動手,跟名字簡直是兩個極端。席凜從出生就被當成接班人培養,從小性子冷冽,生人勿近,長大後更是手段狠厲,眾人皆以為人如其名,凜然不已,難以接近。隻有溫舒知道,他私下裏哪裏生人勿近,哄人時溫柔又磨人,還經常不講武德偷偷用美人計。兩人傳出聯姻消息時,眾人覺得一硬一柔還挺般配。溫舒第一次聽時,隻想說大家都被迷了眼,哪裏般配。經年之後隻想感歎一句,確實般配。初遇時,兩人連正臉都沒看見,卻都已經記住對方。再見時兩人便已換了身份,成了未婚夫妻。“席太太,很高興遇見你。”“席先生,我也是。”是初遇時的悸動,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心動。
89.3萬字8.18 16623 -
完結1001 章

冷情虐愛:傅先生的第一罪妻
新婚夜,傅寒君掐著她的脖子作者:“薑亦歡,恭喜你,從今以後身陷地獄!” 他認定是她害死了大哥,娶了她又不碰她,讓她守一輩子活寡! 可惜一場意外,薑亦歡被迫用自己的身體救了傅寒君,並且懷上他的孩子。 薑亦歡藏起孕肚,小心翼翼的活在傅寒君的眼皮子底下。 傅寒君恨她,肆意羞辱折磨她,卻絕不允許別人動她一根頭發—— “傅總,太太跟人打起來了!” 他暗中出手,將那人趕盡殺絕。 “傅總,太太說傅家的財產都是她的!” 他悄悄將股份全部轉到她的名下。 薑亦歡根本不知情,一心隻想逃離,傅寒君強勢將她擁入懷中作者:“傅太太,你要帶著我們的孩子去哪?”
169.4萬字8.18 3948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