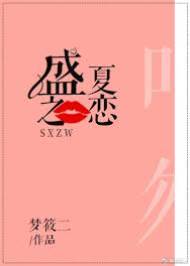《紀爺別虐了,夫人去父留子改嫁了》 第二十七章 年紀輕輕,這就不行了?
秦霜看的眼神一頓發直。
紀寒洲挑起眼簾,見直勾勾地盯著自己的小腹,聲線冷冷道:“你看夠了沒?”
秦霜立刻回過神:“沒看夠,收費嗎?”
司機稍微扭過頭,朝著後麵瞥了一眼,見秦霜直接把紀寒洲服撕了,還以為他倆要在車裏上演什麽呢,嚇得連滾帶爬下了車,關上了車門,走到車頭冷靜去了。
秦霜莫名其妙地回過頭瞪了一眼,“下車幹嘛?”
紀寒洲冷笑一聲:“你還問?”
秦霜突然想到什麽,朝著他的俊臉近:“紀爺,你不會是以為,我想對你做什麽吧?”
一邊說,手指突然撚到了中脘,重重一探。
紀寒洲疼得背脊弓起,脖頸上的舌骨和青筋直線暴起,冷汗沿著下顎,越過結,落鎖骨。
秦霜道:“忍著一點。”
隨手從包裏拿出針灸包,手起針落,兩針刺位之中。
紀寒洲疼得牙關闔,然而,隨著細細銀針,胃部的灼痛,竟不再那麽強烈了。
紀寒洲的臉上也微微恢複了。
Advertisement
他難以置信地看向秦霜。
他以為要幹什麽。
原來……
是想要替他緩解胃疼。
秦霜撇了他一眼,便知道他眼裏在想什麽,冷不丁罵了一句:“變態。”
紀寒洲:“……”
秦霜:“看你一臉很失的樣子,別以為我不知道,你腦子裏是什麽齷齪的想法,告訴你,我對你這種男人沒興趣。”
說完,收了針,
整理好了針灸包,便坐到一邊。
紀寒洲玩味道:“秦小姐真難伺候。不知道,秦小姐對什麽樣的男人興趣?”
秦霜頭也不回地道:“大活好。”
紀寒洲角狠狠搐了一下:“你這話是在含沙影嗎。”
是眼瞎了嗎,沒看過他的真材實料?
秦霜:“紀爺看來最自己還自信的。不過,我不是那種沒見過世麵的人。”
紀寒洲再度被噎得啞口無言。
秦霜降下車窗,對著車外的司機道:“開車!”
司機剛點了煙,才到一半,聽到秦霜的聲音,立刻掐滅了香煙,屁顛顛跑到駕駛座旁邊,拉開車門:“紀爺,您好了?”
Advertisement
紀寒洲劍眉一挑:“什麽‘好了’?”
司機見紀寒洲正在係紐扣,而秦霜則靠在窗邊,氣定神閑地打量窗外,臉冷漠,他角咧了咧,暗暗驚訝。
不會吧?
這麽快。
紀爺年紀輕輕這就……不太行了?
司機將信將疑地上了車,係上安全帶。
紀寒洲看了一眼後視鏡,見司機言又止,一臉惋惜的表,他角狠狠搐了一下,猛不丁意識到,司機在心裏暗暗編排他什麽,頓時惱火起來。
但偏偏司機死死閉,什麽也不問,什麽也不說,紀寒洲自然不可能當著秦霜的麵去挑明這個話題,語氣更冷:“好好開你的車!不要東張西。”
“哦,是。”
……
江山水榭。
車子停穩後。
紀寒洲和秦霜下了車。
負
責照顧宋南梔的保姆匆匆下樓:“紀爺!宋小姐疼得不行,我們正猶豫,要不要把送醫院去呢!”
一見到秦霜,保姆臉有些生氣,就是這個不負責任的醫生,把針紮別人上就走了,害得宋南梔在床上疼得翻來覆去。
Advertisement
紀寒洲對秦霜道:“快點。”
秦霜打斷他:“急什麽,我這就去了。”
說完,漫不經心地走上樓,直到停在宋南梔的房間門口,這才停頓腳步。
隔著門,聽到房間裏不停傳來宋南梔痛苦的聲,看樣子,遭了不罪了。
秦霜推開門,走了進去,站在床邊。
宋南梔疼得渾的睡都被冷汗浸,睜開眼睛,視野模糊之中,約看到一道廓。
不知為何,恍惚以為看到了雲染,嚇得驚了一聲。
“啊——!”
樓梯口,紀寒洲聽到宋南梔淒厲的聲,還以為出了什麽事,一陣疾風一般掠進房間:“南梔!”
秦霜轉過,便看到紀寒洲驚疑的眼神。
他氣勢洶洶地走過來,便看到宋南梔蜷在床頭,不停地道歉:“對不起……對不起……”
疼得神誌不清,以為是雲染化鬼回來了。
秦霜若有所思地看著,尚久,才道:“宋小姐?宋小姐。”
隨著喚了兩聲。
宋南梔這才恢複了神誌,睜大眼睛,直到看清楚是秦霜,緒才逐漸穩定了下來:“秦醫生,是你啊……”
Advertisement
秦霜也懶得糾正了。
看神誌不清
,嚇得魂都沒有了。
不覺得有些奇怪了。
為什麽宋南梔看到,要得這麽淒厲,像是見鬼了一樣。
紀寒洲也懷疑地打量秦霜:“你剛做了什麽?”
秦霜:“我進門,站到床邊,就了。我還了不驚嚇呢。”
說完,道:“宋小姐,躺好吧。”
宋南梔躺了下來。
秦霜利索地幫拔了針。
宋南梔起伏不停的口,才漸漸趨於平靜。
秦霜又保姆喂吃了藥,宋南梔閉上眼睛,竟累得很快睡著了。
紀寒洲在床邊坐了下來,大掌輕輕上被冷汗沾的小臉,眼中心疼之意,快要溢出。
秦霜收拾好東西,正準備走。
門外突然傳來保姆連連驚呼:“小公子,別跑!”
接著,兒特有的稚腳步,掠過門外。
秦霜微微蹙眉。
想起來,紀寒洲有個兒子,既然宋南梔有心衰,這個孩子不可能是生的,那……這個孩子,到底是從何而來?
鬼使神差的。
打開門,走出門外。
走廊盡頭,一個孩子跑過拐角,保姆追其後。
倉促間,隻依稀看到孩子的背影,約與小長意有些相似。
猜你喜歡
-
完結254 章

懷孕后,渣總送我入匪窩換白月光
【虐文+虐身虐心+追妻火葬場+靈魂互換+偏執】陸景深永遠不會知道,沈凝的心先死在他白月光突兀的電話,後絕望在他親手將她送給綁匪,只爲交換他的白月光,更不知,他的白月光挺著和她一樣大的孕肚出現在她面前,她有多怒不可遏和歇斯底里,甚至崩潰,還有當她遍體鱗傷出現在搶救室時,那些冰冷的儀器一點點掏空她如破布娃娃的身體,而他,置若罔聞的眸色終於讓她的淚水決堤。“陸景深,我真想挖出你的心看看是什麼顏色。”他冷哼:“該挖心的人是你,再敢動若霜,我定讓你生不如死。”呵呵,陸景深,但願我們一別兩寬,永不相見,即使地獄,我沈凝也不想再看你冷厲嗜血的臉龐分毫半寸!
46.5萬字8.18 30942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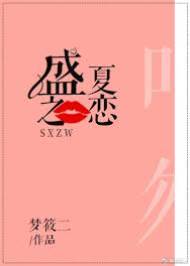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8.18 7712 -
完結319 章

婚後重生,賀少寵妻成癮
賀家賀大少以強勢狠厲著稱。 賀翊川為人霸道冷情,似乎任何人都激不起他的興趣,如同佛子一般,婚後禁慾半年之久。 娶她不過是受長輩之命。 遲早要以離婚收場,蘇溪也這麼認為。 哪知一次意外,兩人一夜纏綿,賀翊川開始轉變態度,對她耐心溫柔,從清心寡欲到溝壑難填,逐步開始走上寵妻愛妻道路! 兩個結婚已久的男女開始經營婚姻的暖寵文! 劇情小片段: 「賀翊川,你今晚怎麼了?你醉酒後可太能折騰人了。」 聽到她耐不住的抱怨聲,賀翊川拾起掛在他脖頸上的小手,輕輕地揉了揉,聲音低啞富有磁性:「今晚高興。」 「為什麼?」 「因為方俊傑他們祝我們新婚快樂,生活幸福。」他一字一句的啟唇,低沉清朗的聲線,清晰分明的灌入她耳中。 聽到後,蘇溪扶住他的手臂,將上半身和他的結實的胸膛拉開一些距離,昏黃的燈光斜照在她明亮的瞳孔里,清澈見底。 「你說該不該高興?」 男人清墨般的眼眸與她四目相對,薄直的唇角邊含著似有若無的笑意,眼神直勾勾地凝視著她。 蘇溪指尖在他手心中微微蜷縮,心跳也不由加速,語調輕緩柔和:「高興。」
52萬字8 10618 -
完結140 章

不言而遇[破鏡重圓]
入職君杉研究所不久,楚言就想辭職了。 她的親閨女指着她的前男友周慎辭大喊:“麻麻,我要這個帥叔叔當我拔拔!” 周慎辭眉梢微動,幽暗狹長的眼眸裏浮着意味不明的情緒。 楚言不合時宜地想起了四年前那個潮溼的夜晚。 光線昏暗,男人身上只隨意披了件浴袍,指尖是還未燃盡的香煙。 猩紅的火光晃動,低沉的聲音略顯沙啞:“楚言,我只問一次,你想好了嗎?” 那時的楚言躺在床上,背對着周慎辭,眼角的淚早已將枕頭浸濕。 可她卻還是佯裝灑脫:“嗯,分手吧。” - 周家是京市是頂級豪門,長子周慎辭更是在商界出了名的縱橫捭闔殺伐果斷,渾身上下都透着生人勿近的氣場。 誰也想不到,他竟然會在大庭廣衆之下蹲下身子,讓一個三歲小孩給他戴上粉紅凱蒂貓的夾子。 “念念,想不想換個新爸爸?”周慎辭溫柔試探。 楚禕念大眼睛一眨一眨:“可是,追媽媽的人好多,要排隊呢。” 周慎辭悄悄把棒棒糖塞進楚禕唸的手裏,道:“好念念,求求了,幫爸爸插個隊吧。” - 小劇場: 某日,總裁辦公室內,平日裏總是乾淨整潔的辦公桌如今一片混亂,隱晦地暗示着剛剛荒唐的不可說。 周慎辭有力的雙臂撐在楚言兩側,將她禁錮在狹小逼仄的空間內,高大挺拔的身姿充滿了壓迫感。 他倨傲地睨着她,語氣冷淡又肆然:“爲什麼不戴戒指?” 楚言擰眉頂嘴:“做實驗不方便。” “戴上。”周慎辭語氣不容置喙。 楚言不服:“有什麼好處?” 周慎辭垂眸,深雋英挺的五官是上帝親手雕琢的藝術品。 “剛給你批了三間全設備頂配實驗室。” 楚言明眸閃動:“不夠。” 周慎辭挑眉,繼而淡聲開口:“那再加一個,今晚不撕你睡裙。” 楚言:“……”
19.5萬字8 352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