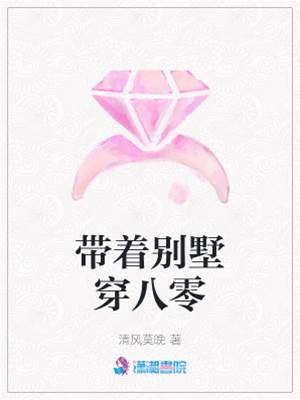《渣男神豪,我能看見欲望詞條》 第475章:撩一下更健康
林浪笑而未語,只是微微挑眉,角勾起一抹似有若無的弧度,眼神中帶著些玩味與灑,既沒承認自己是渣男,也沒否認。
隨后,林浪喝了一口飲料,仿佛黎夢言語間的調侃,不過是一場無關要的玩笑,在這似答非答間,盡顯一種別樣的神與魅力。
黎夢搖晃著紅酒杯,語帶調侃地看著林浪。
“宗保小侄,你這副模樣,可莫要以為能蒙混過關。這般以微笑來回避作答,難不是心中有鬼,默認了自己是那負心薄幸之人?”
林浪角噙著一抹不羈的笑,瀟灑回道:“八姑莫要打趣,小侄不過是見不得人間疾苦,想要渡盡有緣之人。”
“這世間子皆如繁星,各有其璀璨與哀愁,小侄心懷悲憫,不過是略施援手,以暖語藉其心,以陪伴化解其憂,何錯之有?”
“若此便被視作渣男,那小侄這‘罪過’怕是難以洗,只嘆這俠義之心,竟被誤解至深。”
說罷,林浪微微搖頭,似在慨命運不公,實則眼中戲謔更甚。
黎夢沒想到林浪竟借著與耍的玩笑話,大方承認了自己是渣男,甚至還能寥寥數語給自己強行洗白,可見口才和商都很厲害。
于是乎,黎夢繼續調侃道:“瞧你這風流倜儻之姿,眉眼間似藏著無盡思,定是在場之中有諸多故事。”
“小侄你且說說,究竟有多佳人曾為你黯然神傷?”
說罷,黎夢目盼兮,直勾勾地盯著林浪,似要從他臉上尋出答案。
林浪輕咳一聲,臉上笑意不減,眼神卻故作深邃地說道:“八姑,這場之事,仿若繁星閃爍,又豈是能數得清的。”
“小侄不過是在人生旅途中,與諸位子有過幾面之緣,或共賞過春花秋月,或同歷過些許風雨,離別之際,或有惆悵,卻也皆是命運的安排。”
Advertisement
“小侄只愿們日后憶起,曾有一段別樣時,而非傷痛滿懷。至于黯然神傷之說,小侄不敢當,不過是歲月長河中的幾縷漣漪罷了。”
林浪說這話時目坦然地與黎夢對視,似是心中無愧,實則言語間巧妙地模糊焦點,盡顯其高商的周旋之態。
黎夢輕輕掩而笑,眼波流轉間盡是曖昧。
“小侄啊,你這渣男行徑倒真是別一格,渣得如此磊落,這般坦坦,莫不是已將‘渣’字修煉了一門獨特的藝?”
“八姑說笑了,小侄愧不敢當。”
黎夢著林浪深邃的烏眸,俏皮地回道:“尋常渣男皆是遮遮掩掩,汝卻能將其化作一段段看似深的過往,那些子若是知曉你這巧言令的心思,不知是該惱還是該笑。”
林浪淺笑,執起筷子,悠然道:“八姑,佳肴當前,切莫讓其失了熱氣與鮮香。此等珍饈,正宜趁時品味,方不負庖廚之辛勞。”
“事縹緲,終難若此食之實在,且先將腹中空虛填滿,再論其他不遲。”
林浪說話間,夾起一箸菜置于黎夢碗中,神態自若,似已將黎夢的調侃之語全然拋卻腦后。
黎夢知道林浪是在轉移話題,便拿起筷子笑道:“罷了罷了,八姑且看你這場浪子,何時方能真正收心,覓得那能降住你的真心人。”
林浪目灼灼,含而視,緩聲而言:“八姑,佳人展,仿若春日盛綻之繁花,明艷而,恐有顛倒眾生之魅,直教人思繾綣,難以自抑。”
言罷,林浪微微傾,角笑意愈濃,眼神中盡是曖昧之意。
黎夢微微一怔,旋即眼含笑意,輕啟朱道:“宗保這甜言語,莫不是對八姑起了不該起之念?”
Advertisement
“八姑雖有幾分,卻也非那等懵懂,小侄這般夸贊,可是存了戲謔之心,妄圖讓八姑了方寸?”
林浪眼神帶笑,“戲里是八姑,端莊溫婉,宗保敬重又忍不住親近。”
“戲外便有諸般妙境待吾與八姑同探,塵世悠悠,戲外之緣,豈不比戲中更令人心醉神迷?”
黎夢聽出林浪是在,便擒故縱地淺笑道:“哼,八姑可不是那輕易就被迷了心智之人,汝還是莫要在言語上玩火,小心引火自焚喲。”
林浪眉梢輕挑,角勾起一抹壞笑。
“然吾偏生不懼這火焰灼,八姑之火,于吾而言,恰似那海明燈,愈燃愈引得小侄靠近。”
“莫說引火自焚,便是火海刀山,只要能博八姑展,吾亦愿赴湯蹈火。”
;“八姑縱有千般定力,吾也定要在這堅冰之上,敲出之裂痕,看那深藏心底之,如何涓涓流淌。”
林浪說話間眼神熾熱,直勾勾地盯著黎夢,不肯移開分毫。
黎夢有些被林浪到了,眉目含地迎上林浪的目。
四目相對,意橫生。
黎夢秋波盈盈,似笑非笑,眼波流轉間卻難掩那一與心,朱輕抿。
“阿浪你這滿花言巧語,恰似那春日繁花,看似絢爛,實則需防有刺。夢姐我豈會輕易被你這甜膩言語所蠱,上了你的當?”
黎夢雖言語這般說道,可那微微的睫與悄悄泛紅的耳,卻悄然泄了心底的波瀾。
“夢姐,你的臉已經紅了,恰似那之桃,艷滴,莫不是心中思翻涌,才映得這滿面霞?”
“呃……我的臉紅了嗎?”黎夢雙手捂著自己發燙的臉頰。
“夢姐,方才你還言不懼我的花言巧語,怎地現下卻這般怯模樣,可是被我中了心底那?”
Advertisement
林浪的眼神中滿是促狹與得意,子又稍稍前傾,將黎夢的神瞧得更清。
黎夢有些地回道:“好啦好啦!我不跟你耍了,你皮子厲害還不行嗎?”
林浪用公筷為黎夢夾了一塊涼拌豬拱,“夢姐,吃這個以形補形,給你補補。”
“哈……阿浪你好壞啊!”
“居然說我吃豬拱補一補,你是諷刺我長得丑像是豬八戒嗎?”
“沒沒沒。”
“夢姐長得像嫦娥,我長得像豬八戒,嘿嘿……”
“阿浪,豬八戒要是有你這麼帥,那想嫁給豬八戒的孩子不得排隊呀!”
林浪聽了黎夢的話,故意做出一副苦惱的模樣,“太人歡迎也是一種煩惱。”
“阿浪你還自的,就會貧。這飯還吃不吃了,再這般打趣,飯菜都要涼了哦。”
林浪忙不迭地給黎夢盛了一碗湯,“夢姐,先喝口湯潤潤,這湯可是我特意為你點的,就如同我對你的心意,濃郁又溫暖。”
黎夢接過湯碗,嗔怪道:“你這心意都快把我給淹沒了,我怕我這小船承載不起。”
“夢姐的船堅不可摧,我的心意再多也填不滿,只盼夢姐能給我留個角落就好。”林浪含脈脈地看著黎夢。
黎夢低下頭,角卻忍不住上揚,“阿浪,你這是在明目張膽的我嗎?”
林浪壞笑一聲,微微后仰,眼神卻鎖住黎夢,“夢姐,我這哪是你啊?”
“我只是實話實說,表達我對好事的欣賞與向往,誰讓夢姐你渾散發著讓人難以抗拒的魅力,我不過是一介凡人,不自罷了。”
“難道夢姐覺得我這純粹的心意是撥?那我可太冤啦,我明明是在虔誠地靠近你這個神。”
黎夢眉梢輕挑,哼道:“神只可遠觀不可玩。你這般言行,怎讓我覺得,你是不是心懷叵測,想用甜言語哄騙玩我?”
Advertisement
“說吧阿浪,你是不是想玩我?”黎夢歪著頭俏皮的看著林浪,像是把林浪看得的。
林浪連忙擺手,臉上寫滿委屈與無辜。
“夢姐,你可真是冤枉我了。我哪有半分玩你的意思啊?”
“我……我只不過是想跟你親友好的甜互,在你邊你的聰慧與靈,汲取那如春風般宜人的氣息罷了。
“阿浪你好會啊!把想占我便宜說的這麼道貌岸然。”
林浪雙手合十,可憐兮兮地著黎夢,“夢姐,天地良心,我要是有那種心思,就讓我出門踩香蕉皮倒。”
黎夢噗嗤一笑,“看你那樣子,好了好了,暫且信你一回。”
林浪眼睛一亮,“夢姐果然心地善良,我們吃完晚飯之后去哪里玩呀?
“阿浪,你打我主意打得太明顯了,你是在用潛臺詞約我去開房嗎?”
黎夢那一雙眸微微瞇起,似笑非笑地盯著林浪,仿佛要將他心深的真實意圖給看穿一般。
林浪角微揚,出一抹淡淡的笑容,“夢姐,你想多了,我是想吃完晚飯之后,再和你玩一會而已。”
黎夢卻是輕哼一聲,嗔地反駁道:“切,來這套!誰知道你心里到底打的什麼鬼主意呢?我看你是想玩我吧!”
林浪半開玩笑地回道:“本來我對夢姐是沒有邪念的,聽你這麼一說,那我就的問一句,夢姐你好玩嗎?”
黎夢聽后小臉刷地一下就紅了,咬了咬紅,“阿浪你好輕佻啊!我要是回答我好玩,你就想玩我是嗎?”
猜你喜歡
-
完結1069 章

贈你一世情深
我愛了他整整九年,整個少年時光我都喜歡追逐著他的身影,後來我終於成為了他的妻子,然而他不愛我,連一絲多餘的目光都不給我留。 …
199.8萬字8 286874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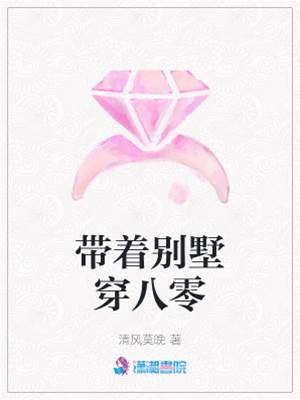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7218 -
完結180 章

正經養崽四年後,豪門親爹找上門
【雙潔】【甜寵】【養狼崽】獨自帶崽的第四年,孩子親爹找上門了。穿著講究的男人站在門邊,問她。“你是尚希?”“…是。”“我是幼崽的父親。”男人霸道強勢:“跟我走,不用想著拒絕、反抗那些沒意義的事情。”尚希盯著他那張和兒子酷似的臉,慢悠悠哦了一聲。其實她壓根兒…也沒想過拒絕、反抗啊。—辜聞明麵上是豪門辜家掌權人,暗地裏是狼人族家主,他在一次發情期提前三天,和走錯房間的純人類女人發生了關係。狼人族一生隻會有一個伴侶,但他討厭三心二意不忠的純人類,拒絕去找她。某一天,他聽到了幼崽呼叫聲。他才知道那個純人類生了幼崽,狼人幼崽正在經曆骨骼發育艱難期。為了幼崽,他把那母子倆接回家住。一開始,他冷冷地說:“我對你沒興趣,我們隻是孩子的父母。”“我隻在意我的幼崽。”兩人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幼兒園。一起參加學校旅舉行的親子活動。一起參加家長會。某一天,尚希去約會了。男人震驚發怒才發現自己的心意。他以帶幼崽出玩為由,斬斷她所有約會。他頻繁搜索:怎麼追求人類女人。他送樓、送車、送包、送飛機……都沒用。約定到了,女人帶著幼崽離開。傲慢的狼人家主,辜家掌權人徹底慌了
35.2萬字8.33 88478 -
完結198 章

退婚當天,我和渣男死對頭領證
父親入院,哥哥被未婚夫親手送進監獄。寧惜一怒退婚,當天便和渣男死對頭到民政局領證。她原本以為,這婚姻就是一場交易。誰想到,便宜老公太黏人。吃飯要她陪,出差要她陪,心情不好還要她哄睡……知道男人心里住著一個白月光,寧惜取出準備好的離婚協議,想要還對方自由。“離婚?”男人一把撕掉離婚協議,“我告訴你寧惜,我江律只有喪偶,沒有離婚。”寧惜……說好的白月光,說好的所愛另有其人呢?“白月光是你,朱砂痣是你……”男人一把擁她入懷,“自始至終都是你!”
35.7萬字8 472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