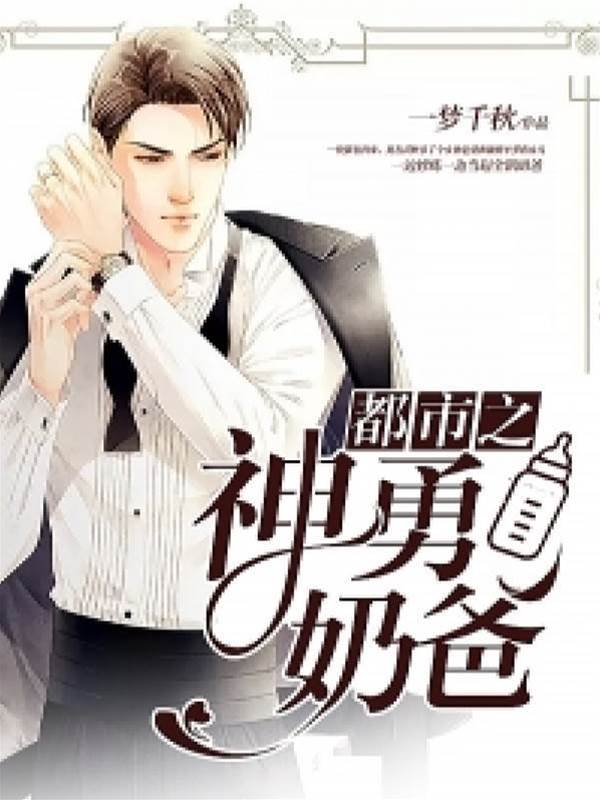《你說沒我也能殺惡靈,現在哭什麼》 363.第363章 對於光明教廷來說,是一件難以啟齒的醜聞
開始漾起一圈圈微妙而又奇異的漣漪。
這漣漪並非尋常水面上的波紋那般簡單,而是呈現出翠綠,那綠鮮艷滴,充滿了生機,
恰似春日裡最鮮的草葉在清晨的中閃爍著迷人的澤。
這抹充滿生命力的綠以楚河的手指為中心,如同被賦予了生命一般,迅速向四周擴散開來。
它的擴散方式猶如一顆石子準地投靜謐的湖面,激起層層細膩而又富有節奏的波紋,
只不過這波紋所蘊含的力量,卻絕非普通的水波之力,
而是足以摧毀一切的毀滅力量。
隨著綠漣漪的不斷擴散,周圍的空氣被一無形的力量,開始變得凝重起來,有一強大的力量正在其中悄然醞釀,蓄勢待發。
接著,
令人驚嘆的一幕出現了:
一片片草葉竟從虛空中緩緩凝結而出。這些草葉形態各異,有的細長如針,有的寬闊似刀,
卻無一不鋒利如絕世寶劍,閃爍著令人膽寒的寒。
它們在空中織,盤旋,彷彿一群被召喚而來的靈,在舉行一場神而又危險的儀式。
隨著數量的增多,這些草葉之劍逐漸形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暴。
每一把劍都蘊含著來自大自然深的神力量,
那力量強大到足以輕易割裂空間,
在空氣中留下一道道目驚心的裂痕,空間在痛苦地。
整個空間,在這強大力量的猛烈衝擊下,
瞬間變得支離破碎,
就像是一面被巨力狠狠擊碎的鏡子,裂痕向四面八方蔓延開來,空間也隨之扭曲變形。
而這場由草葉之劍構的恐怖風暴,此刻宛若一頭被激怒的飢巨,
張開盆大口,帶著無盡的憤怒與毀滅之力,
朝著那座由純粹人堆砌而的人形壁壘猛撲而去。
Advertisement
人形壁壘中的村民們,他們的臉上依舊殘留著驚恐與絕的神,
眼神空而無助。
他們早已被那邪惡的力量控,
失去了自主行的能力,
此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風暴襲來,卻無力掙扎反抗。
風暴無地吞噬著他們,
每一片草葉之劍都如同鋒利無比的刀刃,輕易地切人,將他們的切割開來。
剎那間,花四濺,那殷紅的鮮與翠綠的草葉相互織在一起,形了一幅令人作嘔,慘不忍睹的畫面。
那些曾經鮮活的生命,在這強大的力量面前,
此刻卻如同被絞機無絞碎的泥,
混合著噴涌而出的水,如同一場目驚心的噴泉暴雨,
四飛濺,
將這片原本就充滿恐怖與邪惡的地方,渲染得更加腥與絕。
手掌頭賴以支撐的人壁壘,
在楚河所釋放出的這毀天滅地般的強大力量衝擊之下,
瞬間土崩瓦解,
仿若一座由脆弱沙礫堆砌而的城堡,面對洶湧澎湃,勢不可擋的海浪,
本毫無招架之力,
轉瞬之間便被徹底摧毀。
在場的所有人都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深深震撼,
他們的眼神中充滿了無盡的恐懼,
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生命在自己眼前如風中殘燭般迅速消逝,卻又因被那邪惡力量所控而無能為力,那種絕與無助如同濃重的霾,
籠罩在每一個人的心頭。
而這一切堪稱災難的場景,
不過是楚河看似漫不經心地輕輕一揮手下所引發的結果,卻有著足以顛覆世界的恐怖威力。
整個下水村前來參加祭祀儀式的男人們,
此刻已全然化作了一攤攤令人骨悚然,黏合在一起的碎。
伴隨著如水般大片大片的水噴涌而出,
這些碎和水如暴雨般直接潑灑落在了手掌頭的上。
Advertisement
那洶湧的鮮瞬間將他渾上下原本詭異的紫黑完全掩蓋,
轉而將他整個人渲染了一片令人心驚跳,目驚心的紅之。
大片大片的水裹挾著碎從他的上緩緩落,
滴答滴答的聲響不絕於耳,在這寂靜而又恐怖的氛圍中顯得格外清晰,簡直就是死亡的倒計時鐘聲,每一聲都敲擊在人們的心尖上,讓人不寒而慄。
手掌頭整個人已然在這雨腥風之中驚得呆若木,他那原本就臃腫的軀此刻如同風中的落葉般劇烈抖著。
這抖並非是因為寒冷,也不是由於激,而是源自他心深那無法抑制的驚懼。
他的心中湧起一深深的懊悔與恐懼,他發現自己對楚河這個人簡直是一無所知。
在他之前的臆想之中,楚河為被眾人稱為護國戰神之人,被視作追求武道極致的純粹強者,更是被尊為藍星第一強者的男人,
理應是心懷天下,大無疆,仁慈善良且始終堅守正義的形象。
然而,如今殘酷的現實就擺在眼前,
他所想象的那些好的格特質在楚河上竟然通通都未曾現。
楚河所展現出的,
唯有那令人膽寒的殺伐果斷以及不為任何威脅所的堅毅。
他並非是手掌頭所期的那種心懷慈悲的「聖母」,而是一位真正令人恐懼的鐵強者。
就在這一瞬間,整個下水村的男人全部命喪黃泉,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然就是這個被全大夏國的民眾視為護國戰神的男人。
在驚恐萬分之中,手掌頭終於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的稚可笑,
他之前的種種算計與謀劃,在楚河面前簡直如同孩的鬧劇,不堪一擊。
「楚先生,我們是不是可以坐下來好好地談一談?」
Advertisement
手掌頭強自鎮定,拚命地想要讓自己的聲線保持平穩,可那不經意間微微的抖,卻早已將他心深強烈的害怕暴無。
畢竟,只要是擁有,有有的生靈,在面對死亡的威脅時,心必定會掀起波瀾,絕不可能做到純粹的平靜無波。
「我們背後的黑暗教廷,也不是那麼好惹的。
至我們雙方目前並不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
死掉的這些人,
對於你我這樣的強者而言,
也只不過是路邊微不足道的螻蟻罷了。
人生在世,誰又能保證自己沒有不小心踩死過幾隻螻蟻呢?」
手掌頭試圖用言語來緩解這張到令人窒息的氣氛,同時也在暗示楚河不要輕易與黑暗教廷為敵。
「剛才你用下水村的男人們來威脅我,
現在又要用你背後的黑暗教廷來威脅我嗎?
那就讓你背後的黑暗教廷出來,讓我瞧一瞧吧。」
楚河那張冷峻的面容在昏暗的線下更顯堅毅,
眼神中出的不屑是對世間萬的一種輕蔑。
他緩緩抬起右手,食指輕揚,宛如指揮著無形的樂章,在空氣中自上而下輕輕劃出一道優的弧線。
這一作,看似平凡無奇,卻如同一把無形的利刃,劃破了周遭的寧靜,釋放出令人心悸的力量。
就在這一刻,手掌頭只覺得一難以言喻的震自發,有一無形的力量沿著脊椎直衝而上,
瞬間抵達左臂肩膀的位置。
那是一種細微卻異常清晰的痛,如同千萬細針同時扎,接著,一刺骨的寒意如寒冰般迅速蔓延,沿著左臂的每一寸,每一管,直至指尖,令人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
這還只是開始。
在楚河那看似輕描淡寫的作之後,手掌頭的左臂竟以一種超乎常理的平與整齊,從上悄然落,宛如一片落葉,悄無聲息地飄落在地。
Advertisement
切口,鮮如同被抑已久的火山,
猛然間找到了宣洩的出口,噴涌而出,
化作一道道絢爛的柱,將周圍的地面迅速染一片殷紅,空氣中瀰漫起一濃重的腥氣息,令人作嘔。
楚河的速度快若驚鴻,快到了極致,
以至於手掌頭在左臂離的那一刻,痛楚還未及完全襲來,便已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空虛與恐懼。
他呆立在原地,宛如被某種神的力量定住了形,
雙眼圓睜,目中滿是驚愕與難以置信,死死地盯著那掉落在地上的手臂,要將其烙印在視網上,為永恆的記憶。
那手臂斷裂之,紫黑的鮮如同被喚醒的惡魔,
隨其後洶湧而出,與地面上的鮮織在一起,瞬間形了一灘散發著詭異芒的泊。
那泊中,似乎蘊含著某種未知的力量,讓人心生畏懼,不敢直視。
周圍的一切,在這一刻都變得異常寂靜,
只有那不斷噴涌的鮮和空氣中愈發濃重的腥味,
提醒著人們,這裡剛剛發生了一場超乎想象的恐怖與詭異。
手掌頭的心神,
還未從那突如其來的劇痛與靈魂深的震驚中離,
一更為冰冷且痛楚的便如毒蛇般纏繞上了他的右臂肩膀。
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涼意,
與先前左臂所經歷的如出一轍,卻更加迅猛,更加深骨髓。
他下意識地轉過頭,試圖捕捉這突如其來的災難之源,卻只見到自己的右臂,如同被無形之手輕輕一,便齊刷刷地從上落,切口平整得令人心悸,彷彿是大自然最完的傑作,而非之軀所能承之傷。
鮮,再次如失控的洪水,從斷臂噴薄而出,
與先前左臂留下的泊匯一片,將這片空間染了目驚心的猩紅。
手掌頭的雙眼圓睜,
瞳孔中倒映著的是自己殘缺不全的,以及那不斷流淌,彷彿永無止境的鮮,
恐懼與絕織一張無形的網,將他束縛。
災難並未就此止步。
在他試圖掙紮起,逃離這恐怖現場之時,部突然傳來的空虛讓他整個人失去了平衡,
如同被離了支撐的木偶,不控制地向後倒去,
重重地摔落在冰冷的地面上。
那一刻,他驚恐地發現,自己的右,
不知何時,也已悄無聲息地從上分離,
切口同樣平整無瑕,猶如從未存在過一般。
手掌頭躺在地上,因劇痛而蜷,雙眼中滿是難以置信與絕。
他試圖用剩下的左支撐起,
卻發現那也已失去了應有的力量,綿綿地搭在一旁,顯然,它同樣遭遇了不幸。
四周,是不斷擴散的泊,空氣中瀰漫著濃重的腥與絕的氣息,手掌頭的整個世界都陷了無盡的黑暗與恐懼之中。
這一刻,手掌頭終於意識到,自己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楚河是一個超越了人類理解範疇的恐怖存在,正以一種無法抗拒的方式,剝奪著他的一切。
而他除了絕地躺在那裡,等待著未知的命運降臨,似乎已別無他法。
「不,不要!」
手掌頭這個剛剛還囂張狂妄,不可一世的存在,
此刻卻如同一隻被剝去了翅膀的雄鷹,徹底失去了往日的威風。
他的聲音中充滿了前所未有的恐懼與絕,
每一個字都是從靈魂深被生生出,帶著無盡的抖與哀求。
那些年輕男們看的目瞪口呆,如果不是他們剛才親眼目睹真的不會相信。
這個可憐的臃腫胖子,剛才還不斷的囂張的挑釁譏諷楚河。
他的如今已殘缺不全,僅剩下一條孤零零的和軀幹。
曾經強健有力的四肢,如今只剩下這一孤零零的,支撐著搖搖墜的,顯得格外脆弱與無助。
手掌頭只能用那僅存的五手指,
艱難地撐著地面,
每一次的用力都似乎要耗盡他全的力氣。
他的手指因長時間的而變得模糊,指關節因過度用力而發出「咯咯」的聲響,
彷彿隨時都會斷裂開來。
但他的眼神中卻著一種頑強的求生,那是對生命的,對活下去的執著。
他的軀幹因失去支撐而微微前傾,背部彎曲一個令人心酸的弧度,就像背負著千斤重擔。
手掌頭的臉上滿是汗水與泥土的混合,汗水順著臉頰落,
滴落在地,與地面上的塵土融為一,形一道道蜿蜒的痕跡。
他的雙眼中充滿了驚恐與無助,此時此刻正面臨著生命中最可怕的噩夢。
手掌頭試圖用微弱的聲音求饒,但聲音卻如同被風吞噬般,消散在空氣中。
他只能無助地瞪大眼睛,著周圍這陌生而又恐怖的世界,
心中充滿了絕與恐懼。
他的每一次呼吸都變得異常艱難,
甚至連空氣都在與他作對,試圖將他最後的生命力榨乾。
「看樣子你背後的黑暗教廷已經將你給放棄了。
不然的話,為什麼現在還沒有出來?」
楚河的聲音冰冷而平靜,彷彿在陳述一個無關要的事實。
他的話還未說完,突然間,一條麻繩如同一條潛伏於暗的靈蛇,悄無聲息地自天際垂落,帶著一骨的寒,攜帶著幽冥的呼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楚河的脖頸纏繞而來。
楚河的眼神在那一刻變得冷冽如霜,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形卻紋未,宛如山嶽般沉穩。
他右手如電,準無誤地一把抓住了那條帶著死亡氣息的麻繩。
接著,
楚河猛地一拽,那力量之大,
竟使得原本懸掛在半空中的弔死青年如同斷線的風箏,不控制地向地面墜落。
青年的臉龐蒼白如紙,雙眼布滿了細長如的管,怨毒的目要穿楚河的靈魂,將他拖無盡的黑暗深淵。
楚河卻不為所,他的眼神中只有冷漠。
在弔死青年即將到楚河的瞬間,楚河的五指猛然張開,
掌心之間,金的火焰如同被喚醒的神祇,
瞬間升騰而起,熾熱而耀眼,宛如金的太穿雲層,照亮了這片被恐懼籠罩的空間。
那火焰中蘊含著無盡的威嚴與力量,能夠焚盡世間一切邪惡與黑暗。
楚河猛地一拍,將手掌重重地拍在了弔死青年的膛上。
在接的剎那,
金的火花如同璀璨的煙花,四散飛濺,照亮了青年那蒼白漠然的臉龐。
這火焰接到青年的,便如同貪婪的狼,迅速侵了他那冰寒如冰窖的軀,
從部開始熊熊燃燒,將一切邪與戾氣吞噬殆盡。
青年的雙眼依舊怨毒地盯著楚河,
但那怨毒卻隨著他的急速枯萎而逐漸消散。
他的像是被幹了生命力的花朵,
迅速凋零,皮變得乾癟,萎,骨骼,
最終化作了一縷縷黑煙,
消散在空氣之中,就像他從未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一般。
整個過程中,楚河的面容始終平靜如水,好像只是在進行一場無關要的儀式。
他所展現出的力量與手段,卻讓人心生敬畏,覺如同這片天地間的主宰,
能夠輕易地將生與死玩弄於掌之間。
而那片被金火焰照亮的空間,也在這恐怖而又詭異的氛圍中,逐漸恢復了平靜。
「我還有繼續生存的價值!」
手掌頭見勢不妙,努力急促大聲喊道。
他心中清楚,同伴也就是那個弔死青年已經被楚河瞬間秒殺掉了,
接下來很有可能就到自己了。
他深知,如果再不努力求饒,恐怕就真的沒有機會了。
畢竟,黑暗教廷雖然強大,但遠水救不了近火,此刻能保住自己命的只有楚河。
「黑暗教廷真的很強大,不是我在威脅你。
在大夏帝國的黑暗教廷也只是分部。
留下我,最起碼能夠讓你們擁有一個可靠的關於黑暗教廷的報信息來源。」
或許是擔心來不及把話說清楚就被楚河幹掉,手掌頭在講述的過程當中,語速飛快,幾乎是一口氣把話說完,生怕稍有停頓就會招來殺之禍。
「黑暗教廷,明教廷,你們雙方難道有什麼關係嗎?」
楚河果然如手掌頭所期的那樣,沒有再繼續出手。
他緩緩走到了手掌頭的面前,
居高臨下地看著對方,眼神中帶著一探究與疑,輕聲詢問道。
「黑暗教廷的起源本就來自於西方。
是從明教廷當中分割出來的。
明教廷一直將我們黑暗教廷視為仇,在全球的範圍懸賞追殺我們。」
手掌頭短暫地猶豫了一下,心中權衡利弊之後,
還是決定將自己所知道的況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畢竟,此刻保命才是最重要的。
「明教廷對於黑暗教廷的存在也有瞞,
因為這對於明教廷來說,是一件難以啟齒的醜聞。」
(本章完)
猜你喜歡
-
完結668 章
超級能源強國
1987年的大學生,包分配,做公務員易如反掌.2012年的大學生,爛大街,畢業即失業.穿越成爲1987年的北大生,蘇城終於享受到了天之驕子的待遇.寶潔公司,松下電器之類的世界五百強,是絕對看不上的.外交部、教育部,哭著喊著要他,也是不會輕易同意的.
185.5萬字8 14196 -
完結2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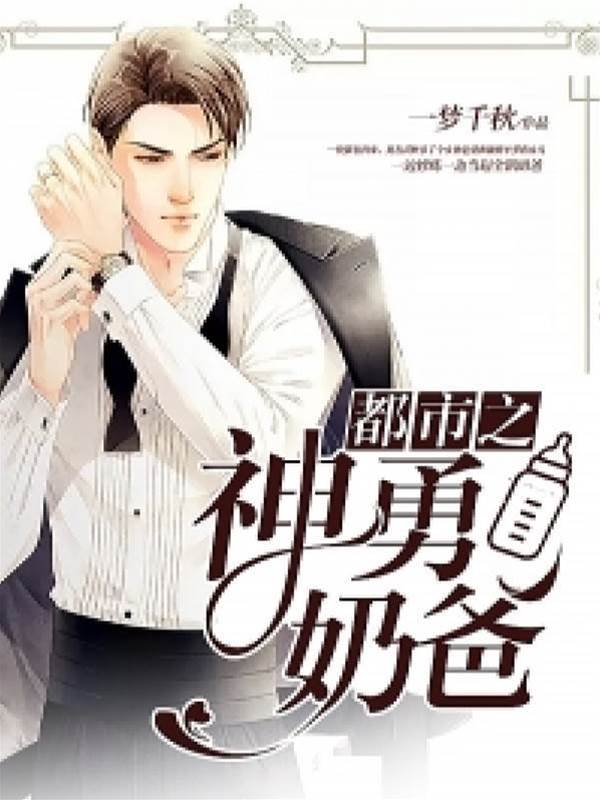
都市之神勇奶爸
一代強者歸來,莫名其妙多了個女神老婆和傲嬌小蘿莉女兒,一邊修練一邊當起全職奶爸,跟在哥面前裝逼,哥的外號叫作神勇奶爸,專制各種不服……
50.7萬字8 17004 -
完結1353 章

荒野求生之我的釣術只是好億點點
【2023年最火的荒野求生小說】 野釣王蘇白魂穿了個富二代,還沒來得享受生活,就被荒野求生365天節目選中。 開局一把魚竿,從此開啟了掛逼一般的求生之旅。 其他選手還在喝咸泥水凄慘無比,蘇白已經抱著女主吃飽喝足。 其他選手還在凄風苦雨瑟瑟發抖,蘇白已經蓋了個二層小別墅準備過冬。 其他選手還在被各路野獸追著跑,蘇白已經左牽黃右擎蒼,在荒野里橫著走啦!
237.7萬字8.18 47045 -
完結488 章
風水鑒寶師
韓景陽商場情場雙雙失意,卻巧獲游戲技能宗師級鑒定術。經他鑒定的古玩統統有了屬性。“財源廣進”的三足金蟾擺件?“延年益壽”的老壽星銅像?“逢兇化吉”的荷花仙子和田玉牌?“家宅平安”的青石碑。“一見鐘情”的元青花西廂人物大罐?“招財+2”的木雕?“長壽+8”的人物畫?“旺夫+12”的漢青銅鏡?“多子+23”的清代黃花梨拔步床?于是,韓景陽朝蜂擁而來的富商明星美女嘶聲力竭地喊道:“排隊排隊,誰插隊就取消誰的購買資格,還有,我真不是神棍,我就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古玩鑒定師。”
89.5萬字8 166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