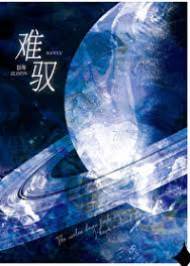《十二年,故人戲》 68.第六十六章 浩浩舊山河(6)
;
「真沒料到,他們會來這麼早。你們準備著,要下車了。」周禮巡連大都來不及穿,搭在臂彎里,在零下十幾度的車廂里穿行而去。 🎨sto.🍒com
沈奚跟傅侗文回到包廂,醒小五爺和培德,譚慶項也很快回到包廂里,大家略作修整,跟隨代表團下了火車。
雪中,天有亮得徵兆,微見星月。
「第一次見到南滿鐵路,」輕聲慨,「這裡的雪比南方要厚多了。」
「關外的雪是最的。」他笑。
小聲問:「這次的路線包含橫濱和紐約,是因為要和日、先私下會談嗎?」
「是。」
國怕日本在亞洲勢力擴張,日本也怕國手亞洲事務,所以都安排了高規格的外活,等待著中國代表團的過境。這種覺並不會讓傅侗文愉快,因為不管多熱的款待,也掩蓋不了一個事實:中國是羊,在等著兩頭狼的決鬥。;
他輕聲道:「不過,我們在國的公使已經和威爾遜達了共識,國會在黎會議上支持中國。所以,我們是要聯制日。」
那日本會善罷甘休嗎?
沈奚擔心。
傅侗文好似讀懂的憂慮,又道:「總長是外場的老前輩,他有應對的法子。」
他們換了汽車,剛好天亮了。
晨里,這風雪大地像一卷無字的宣紙,展開在的眼前。
這是一塊群狼爭搶的土地,如此,如此寧靜。
沈奚從車窗里眺遠方。
緒三十年的日俄戰爭後,沙俄把自己在東三省修建的鐵路分了一部分給日本,改名為南滿鐵路。那時對南滿鐵路意難平,是因為日本在「二十一條」里提到過它。後來在這條鐵路周圍發生了太多的事,日本侵華主力關東軍的誕生,皇姑屯事、九一八事變和復辟的偽滿洲國……;
Advertisement
而在那天,他們路過的那天,一切尚未發生。
***
他們在那天夜裡抵達奉天,接了日本外務省的宴請。
宴席後,立刻登車,前往漢城。抵達漢城後,外總長突然告病,說在夜車上了寒,舊疾復發,雙不便走。不再見客。
數日後代表團抵達橫濱,住在中國城的華僑家裡。
這裡是日本對外港口,也是外國人的聚集地,代表團選擇住在這兒,是方便隨時有了船期,能立刻赴。
到了橫濱後,總長迴避了日本外務省的邀請。日本安排了一系列的外活,包括日皇的接見、授勳和茶會等等,全被總長一句「負病在、不能久坐」推辭掉了。
國、中國駐日公使和總長之間電報不斷,爭論不休。
中日兩國報紙也每日評論,為了外總長突然生病,不肯見日皇而猜測連連。;
外界吵翻了天。
唯有他們所住的地方靜得連風都沒有,雪也落得很輕。
小五爺舉著一份報紙,笑著走:「三哥,你要不要聽,我把翻譯的話都背下來了。」
傅侗文以兩指夾住他手中的報紙,輕飄飄地收過去,細細看。
這份報紙言辭鑿鑿,指責中國外總長在「裝病」,不肯和日方友好通。在報導結尾,還說此事大有幕,只是不便公布。
「日本報紙謠言很多,總在有意引導民眾,」傅侗文放下報紙,慨道,「希國報紙不要全是親日派,引起民眾的猜忌。」
「三哥還懂日文?」小五爺錯愕。
他擱下報紙:「我過去和你四哥是支持維新的,自然會讀這個。」
「倒也是……」小五爺憾,「往日三哥瞞我太深了,竟一字未,讓我險些寒了心。」;
Advertisement
笑:「你三哥說過,你若真有抱負,不必有人同行,也不用誰來指路。」
「嫂子也早知道了。」小五爺錯愕。
「反正比你知道的早。」
「嫂子過分了,過分了。」小五爺哭笑不得。
沈奚將藥碗遞給傅侗文。
不管外總長是真病還是裝病,反正傅侗文是真病了。
從奉天到漢城的夜車上他就開始發寒熱。車廂里零下二十幾度,下車赴宴時室炭火燒得旺,暖如初夏。冷熱替,反覆折騰著,誰都不住。
像這種底子好的休息兩日就好,傅侗文卻只好等著病發。
不過,他心境好,倒也沒大礙。
譚慶項見傅侗文吃了藥,招呼著,閒雜人去碼頭確認船期。對他們來說,在日本多留一日就是多一日麻煩,恨不得今晚就能登船。;
沈奚給他鋪好被褥:「你該午睡了,一會會發汗。」
傅侗文坐在地板上,笑著看,忽然低聲說:「昨日裡我你的睡都了。」
沈奚反駁:「你睡覺喜歡抱人,自己發汗不算,弄得我也像落湯……」
他笑:「何時抱你睡的?我卻不記得了。每日都是?」
見他不正經,不答他。
「這是潛意識的,怪不得三哥,」他又笑,「是驚覺相思不,原來只因已骨。」
……
「一個睡覺姿勢,也能說到相思上。」嘀咕。
「要不是神不濟,三哥還能給你說出更多的門道來,信不信?」
「信。」指被褥,意思是讓他躺下再說。
他毫不急:「喝口茶再睡,好不好?」
「吃藥是不能喝茶的。」;
他雙眸含水,住。
沈奚上不說,也心疼他總躺著養病,只好煮水泡茶。
Advertisement
不消片刻,水汩汩地冒出來。
揭蓋,燙了手,忙住自己的耳垂散熱。
「侗文,」周禮巡穿了件薄襯衫,滿腳的雪,跑進院子,「外務省的車竟然來了。」
他踢掉皮鞋,進房間。
「來做什麼?」
「接總長去東京。」
「這是邀請不,霸王上弓了。」他評價。
「你還有心思玩笑。」周禮巡鬱悶。
傅侗文也無奈:「人家既然派車來了,哪怕總長真病得下不了床,也會被抬著去的,」傅侗文搖頭,「攔不住。」
周禮巡悶不做聲。
傅侗文沉片刻,問說:「他們在東京的安排是什麼?」;
「今夜是別想回來了,要安排總長住在務省舍,」周禮巡說,「先見我們自己的駐日公使,明日見日本外相,明晚去京都桃山明治天皇陵。」
中國的駐日公使是個親日派,日日以辭職威脅總長去東京的,就是他。
「這樣的安排,明晚也會留宿東京,」傅侗文蹙眉,「後日能回來就算快的。」
「可船期已經定了,後日晨起離港,」周禮巡附和,「我真怕趕不上船期,又要在這裡多留十幾日,十幾日的變數有多大,誰都無法預料。」
傅侗文不語。
沈奚看了他一眼,給兩人倒茶。
一小時後,總長帶著兩個參事前往東京。
總長一走,代表團都被籠罩在了霾中,怕東京有變,怕東京有刺殺,怕被強留在東京,錯過船期,引起國的猜忌……
到翌日,院子裡氣氛抑到了極點。;
晚飯時,主人送飯到沈奚房間,還悄悄問,為何從昨日起代表團里的人緒就低落了許多?晚飯全都吃得。
Advertisement
沈奚不便把外上的事和主人說,含糊解釋說,是擔心大雪延誤船期。
主人反倒是笑,說誤了也好,多留十幾日,還能在橫濱四逛逛,尤其是山間溫泉最是好去,都在憾這次大家來去匆匆,來不及款待同胞。
沈奚勉強應對兩句,接了飯菜。
飯後,天徹底黑了。
周禮巡做主買了明日一早的船票。可東京還是沒消息,連電報也沒有。
大家都在猜測,是否總長已經決定改期了?
傅侗文反倒認為,還有一線希準時登船。
「也許沒來電報,是怕親日的日本公使從中作梗。」他低聲道。
「嗯。」沈奚頷首。;
他問主人借了一副象牙制的象棋,在燈下盤膝坐著,把全幅神都投注到了棋盤裡。深的西裝外披在肩上,影子自然地落到的上、手臂上。
茶幾上的一摞報紙是日文的,這兩天早被他翻了無數遍。
沈奚不是第一次陪他「等待」,在徐園裡,等六妹的消息也是如此。分秒期待,分秒猜測,也在分秒擔心對方的安危……
手托著下,看他下棋,久了,嗓子乾。
也麻了。
矮桌上的西洋鐘錶,指向了凌晨一點。
「你……」終於出聲。
傅侗文抬眼。
本想勸他睡,但猜想他躺下也睡不著,還不如下棋,於是改口問:「你不?」
「你不問不覺得,」他低聲笑,「一問,倒是有點。」
「我去找玻璃杯。」說。;
「不是有茶杯?」他下頦指茶幾上的日式茶杯。
「今夜按你喜歡的來。」
大玻璃杯泡茶,這是傅侗文留洋時養的習慣。
想哄他開心。
沈奚拉開門:「廚房有,我見到過,你等我回來。」
鞋在門外。彎腰,拂去鞋上的雪,忽然見到不遠有盞燈亮了。
是總長房外的燈。
一個年輕參事撐著傘,擋著雪,傘下是本該在東京的總長……
「三哥,三哥!」口他。
總長聽到這句,先笑了,遙遙看這裡。
傅侗文手撐著地板,立而起,快步走出,和對方相視而笑。
總長微笑著頷首,對紛紛出來的後輩們說:「痛風得厲害,我要去吃一劑藥。今夜辛苦各位了,還是照舊明早啟程,不要耽擱了正事。」;
言罷,總長夫人已經從房間走出,彎腰為他拖鞋後,攙扶他回了房間。
那個參事被團團圍住,詢問東京的事,為何會提前返回橫濱。
參事接了沈奚遞的茶,潤了潤,便笑著給大家講了前因後果。總長一到東京,就被親日的中國公使拉住面談,總長故意借著病,不談半句外問題,只說痛風難忍。到今日白天見了日本外相,也只坐了二十多分鐘,便病倒了。
最後,只吩咐留下帶去的另一個參事,代替他去陵。
以此後,總長一刻不留,連夜而歸,如此才算是趕上了時間。
一時院笑聲起伏。兩日霾盡去,大夥睡意全無,趁夜收拾行李。
天亮前,他們怕再有變,早早趕到碼頭。
在登船前,有人匆匆送來一份日文報紙,總長閱畢,凝目蹙眉。報紙遞給後諸人傳閱,最後到了傅侗文手裡。;
「出什麼事了?」沈奚心有餘悸,唯恐無法登船。
「報上說,中國參事在去明治天皇陵的途中,汽車遇到了槍擊。」
沈奚吃了一驚。
總長長嘆,輕聲道:「日本人虛虛實實,報紙謠言很多。我們先登船。」
外人員遇刺並不見,昔日李鴻章在日本也遭遇了槍擊,這是他們做外的人必須面對的危險……倘若是真的,登船後會有電報來證實,也有駐日公使協同理。
無論何事,都不能阻攔代表團如期登船。
碼頭魚龍混雜,各國人都有,若有刺殺,防不勝防。
大家都提高了警惕,簇擁保總長登上遊。
因為套房房間,傅侗文把頭等艙都讓給了外部的人。他們定的是一等艙的房間。
遊駛離橫濱碼頭一小時後,沈奚的心略略安定下來。;
打開布紋的手提箱,把傅侗文的先拿出,一一掛在櫥里。
傅侗文笑著,倚在門框上:「你且先收拾,我去看看餐廳。」
「你不怕危險了?」停了手中的活。
「三哥我一個國商人,有什麼危險?」他輕描淡寫道,「順路去問問周禮巡,有沒有新電報來。」
不止他擔心那個參事,也是同樣的心。
沈奚走到他邊,小聲說:「那你去吧,記得回來吃藥。」
「好。」他低聲道。
傅侗文去了頭等艙里,幾個套房房間門都敞開著,笑聲頻頻傳出,皆是鄉音,聽得他也微笑起來。等進了總長房間,客廳堆滿文件箱,讓人完全無法立足。
周禮巡和一位參事笑著倚在箱子旁,見傅侗文進來,把電報塞給他:「正要去找你,你先來了。是虛驚了一場,報紙謠言。」;
電文簡短,是那個參事親自發出的:報載傑在西京驚,全系造,知念特文。
又是新聞造。
傅侗文笑著,心送快下來。
總長接了夫人遞過去的熱巾,笑著指揮他們:「侗文來了也好,幫著挪一挪箱子。」
「三爺是爺子,怎敢勞煩啊。」參事打趣他。
傅侗文搖頭一笑,挽起襯衫袖子,直接手幹活。
這堆文件箱從北京城的陸宅運出,就一直存放在總長和夫人旁,是要文件,箱外全部著英文的中國外部字樣。夫人是個小心的人,每回搬運都要核對,手握著一個文檔,挨個檢查箱子的編號,從頭到尾,不發一言。
等查看完,傅侗文他們在喝茶時,才低聲道:「丁字號木箱不見了。」
眾人皆怔。
總長原本拿茶壺,在給傅侗文他們倒茶,聽聞這句,立時擱下茶壺。;
「怎麼會,再核對一次,」總站接過詳單,「我自己來。」
房間裡除了總長的腳步,還有挪箱子的聲,再無其它聲響。
總長很快核對完,握著清單,不,也不說話。
丁字號木箱,裝得是有關東北、山東、蒙古、西藏的絕外文件,全都是和日本聯繫最切,也只有日本才會真正關心的文件。
就在途徑日本後,整箱文件都不翼而飛了。
得如此準,而又沒有毫的痕跡。
總長沉默著,再次清點了一遍文件箱,最終確認了這個事實。
他摘下眼鏡,靠在牆壁上,右手按住自己的雙眼。
許久後,他重新戴上眼鏡,嚴肅道:「代表團有兩方政府的人在,關係複雜,此事萬萬不能聲張。等到了紐約……再想辦法。」
猜你喜歡
-
完結2171 章
豪門暖婚蜜愛
十三年前,她大雪中救他,十三年後,他害她家破人亡,走投無路時,他逼她做他的女人,她轉身走向另外一個男人:“先生,我今年二十歲,身體健康,體貼溫柔,善解人意,會忠於婚姻,你願意娶我嗎?”顧少修開車門的動作頓住,看清她的模樣後,輕笑點頭:“我願意!”————誰能告訴她,婚前不是約法三章了嗎?他們隻是合作夥伴,婚後AA製,井水不犯河水,為什麼這男人變著花樣兒攻占她的心、俘獲她的人,霸道鎖著她,任她萬般刁難也不肯放?
441.6萬字8 39822 -
完結49 章

八竿子打著你
簡西溪:我和李珩?八竿子打不著啊。 李珩:哦。 簡西溪:? 李珩:你打著我了。 豪門聯姻*先婚后愛*沙雕·甜
9.6萬字8 10347 -
完結267 章

穿越大佬︰我的徒弟是一堆奶團子
【團寵、萌寶、甜爽、穿越】 江湖傳言,逍遙派大師姐是吃人不吐骨頭的女羅剎,早晚要一統天下。 其實她只想嫁人生娃,種田養鴨。 一朝穿越,夢想成真啦! “宮先生,不得了,夫人一胎72寶!” “沒關系,不嫌少,二胎還有機會吶!”
26.4萬字8 6920 -
完結157 章

寵溺
【乖巧內斂但偶爾很A的小姑娘】x【妖孽腹黑超會說騷話的‘斯文敗類’】傅斯衍家里,突然多出來了一個需要照顧的小姑娘。她小小只,笑的時候眉眼彎彎,臉頰有兩個小酒渦,一看就讓人心生憐愛。一出現,就奪了他一生全部的溫柔和寵愛。-S大人人皆知傅斯衍工作中嚴苛到不近人情,誰都不敢惹。不曾想后來某次課前,有人就看到教室外,傅教授把一個生氣的小姑娘抱在懷里,軟聲軟語,眼底盡是寵溺。上課后一分鐘他才進來,面對正襟危坐又一臉八卦的同學,他邊解袖扣,眉梢帶笑,語氣難得溫和:“抱歉,你們師母和我鬧點小脾氣,剛哄好。”眾人:???-有傳聞傅斯衍交了個女朋友,卻一直沒領出來見見,大家都笑他金屋藏嬌。直到某天,朋友們去他家做客。剛進門,就看到一個身材嬌小、穿著睡裙的小姑娘沙發上看電視。女孩看到家里來了生人,害羞地想要跑去樓上,卻被傅斯衍一把抱了起來,聲音微沉:“不穿鞋亂跑什麼,嗯?”容歡勾住他的脖子,把頭埋在他的頸項,聲音嬌軟:“傅叔叔……”圈著她細腰的手箍緊,他語調微揚:“叫我什麼?”她紅著臉,輕輕喚了聲:“斯衍……”他淺笑,吻住她的軟唇,“真乖。”
22.1萬字8 14818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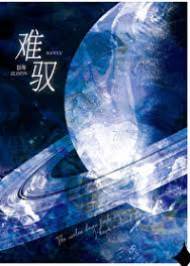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18 113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