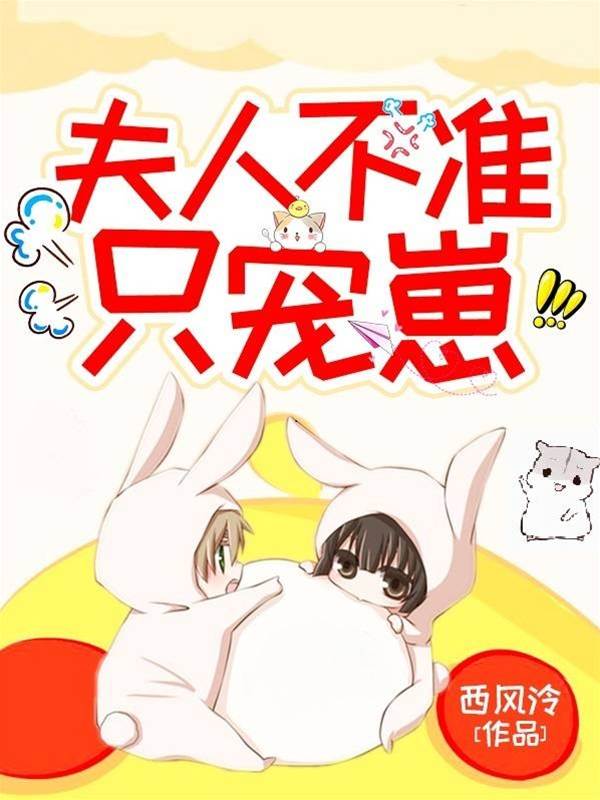《予我千秋》 第23章 貳拾叁
兵帳中油燈的線半明半昧地照著卓炎的臉,的表幾乎沒起任何變化。甚至連多一遲疑都沒有地,轉手便將匣中文書取出,然后逐一展開。
目首先掃到文尾部的日期——
一封是晉歷永仁元年十一月初十。
另一封則是晉歷永仁二年五月三十日。
看清后,卓炎的目不易輕察地微微頓了一下。
在永仁元年十一月初十過后還不到一個月,自豫州奉詔振旅歸京,一城便被械送史臺獄。
永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親手將寫著白首永偕的婚書塞戚炳靖的掌中;一個月后的五月末,謝淖大軍叛晉、與云麟軍并師南下的消息傳遍二國,震驚整個宇。
卓炎低眼,用手指將文書卷軸推平,自右來閱。
兩封文書皆言簡意賅,措辭有力且果決。
永仁元年的這一封并非普通文書,而是在鄂王印之外還加蓋了大晉帝璽的國書。書中答允大平王英肅然,大晉誠愿出借兵力南下,助其登基即大平之帝位。大晉借兵之條件有二:一是王須按此前約定,在即位之后割讓大平金峽關以北之十六州疆土予大晉,以充鄂王之封邑;二是將卓炎送至鄂王手中,大晉不見活人則不發兵。
卓炎看著那“卓炎”三字,定了片刻,才擱下這封,拿起另一封。
永仁二年的這一封文書則是僅蓋有鄂王印的私函。書函中稱,謝淖叛晉實為鄂王之授意,目的在于借卓炎與云麟軍之力,以更的傷亡、更快的速度破金峽關南下,一旦合軍兵抵大平京城,謝淖必會率麾下臨陣反水,挾持卓炎后殺云麟軍一個措手不及,而后兵皇城,拱立王上位;王于大平朝中力促此事,開金峽關與京畿諸路門戶,切勿令兵部發兵北擊云麟軍。
Advertisement
閱罷,卓炎將其向帥案上隨意一丟,舉目看向下首的武。
的臉鎮靜而冰冷,聲音不帶什麼特別的緒:“王的心意,我收悉了。”
然后角輕,看向武的目像是在看著一個活生生的笑話:“自云麟軍功南出金峽關以來,王便再也沒有收到過來自大晉鄂王的信函,更是從始至終都未得到過來自謝淖本人的消息。我說的對麼?”
武絕沒有料到在閱過這兩封文書后會是這樣的反應,一時啞聲,不知該回應什麼。
……
卓炎不高不低的聲音穿過帳幕隙,清晰地傳剛走到帳外的戚炳靖耳中。
邊的親兵去請他來時,并未詳細說是何事。而他眼下聽得里面傳出的這一句,當下便止住了要替他揭開幕簾的士兵的作。
士兵無聲收回手。
戚炳靖給了他一點笑意,然后前,負雙手于背后,神仔細地繼續聆聽里面的對話。
……
帳中,卓炎等了那武半晌,不聞其言,臉上便出些不太耐煩的神來。
以指輕叩帥案,說:“大晉鄂王戚炳靖,英武睿明,才出眾人,于大晉國中權勢滔天,便是大晉新帝亦須賴其以定朝綱。王今能得他相助,大位雖不能說唾手可得,但若籌謀得當無失,亦能有八九之勝算。”
“但若諸策果真無所失,”說著,角出一點譏:“我此刻應已被謝淖挾持,云麟軍更應已被殺個措手不及了,我又豈會有暇在這兒看這兩封文書?”
繼續說道:“謝淖其人,踐歷行伍而通兵事,從一介不知名的邑軍先鋒使憑著軍功一路升至大晉中將軍,僅用了不過一年多而已。當年他與卓疆手,七戰而四勝,四勝皆是速戰速決。這樣的一個人,若早已謀劃好臨陣反水一事,又豈會遲遲不,徒增后事變數?
Advertisement
“我今能收到這兩封文書,足以說明諸事并未如王所謀。我料王久不聞鄂王音信,見云麟軍陳兵城下亦久不見謝淖有所,故而坐不住了,料定已不能再賴鄂王之允助,這才你送這兩封東西來給我看,意在挑撥離間我與謝淖。
“自然,王與我相識多年,不會以為我看不出他這挑撥之意。他之所以赤地行挑撥之舉,是因他以為,既然這兩封文書已儼然無所用了,不如送來給我,縱然眼下謝淖尚未反水,然而這文書背后的事,必能令我對謝淖的信任然無存。他想試一試,如這兩封文書能夠使我與謝淖二軍離心,這局勢必將大變,云麟軍若逢兵,三兩日間必亦顧不得這城中大位;而如若此計不,于他而言亦不會有什麼多余損失。
“我說的都對麼?”
武的額上滲出一層細的冷汗。
卓炎看他一眼,手重新拿起那兩封文書,作從容卻有力,緩慢地將其撕裂四半。
捻了捻指尖,連眼都不再抬,冷冷道:“這兩封文書,皆是大晉鄂王所言所允,可王怎麼就忘了去問問領兵的謝淖——他答應鄂王了麼?”
……
口中所言,遠不及心中所想。
先出現于腦海中的,是江豫燃領先鋒人馬在踏京畿地界后給發的那封信。京畿軍撤防,江豫燃的那句倒是稀奇,如今再看,是一點都不稀奇。
再往前回憶,便是金峽關前后諸事。
最初大平換將,不從北面諸路軍中選人,偏從南邊將沈毓章千里迢迢調來。沈毓章一非王親腹,二是裴穆清生前所看重的門生之一,多年前亦曾主請纓北上抗敵,一向奉聽王之意的兵部竟能在那當口上將他派往金峽關,如今想來,圖的便是沈毓章與時如兄妹般的舊。
Advertisement
但兵部所圖卻并非是為了讓沈毓章以舊前去招降,而是能夠借此找個盡合理的由頭將大平守關之將在二軍對戰之際撤下。沈毓章因念舊而通敵與徇私,縱使當初不為之構陷此二罪,想必兵部亦不會手。而若非沈毓章這等門楣忠正、文武盛名赫然有聲于國朝之中的將領含冤被罷,金峽關守軍之軍心又何以能被輕易搖,金峽關之門戶又何以能被輕易打開。
顧易侍從王多年,借兵部之名北赴金峽關問罪沈毓章的這一趟差使,他辦得是極其漂亮。
當日關外一晤,沈毓章言稱所奉旨意為可招降、不可濫殺。
當然不能殺了。
若殺了,王又何以按鄂王所言,讓謝淖借力云麟軍破關南下?
此后拆毀金峽關墻以要挾大平朝廷,昭慶自請替朝廷北上談和,兵部竟不曾阻攔昭慶分毫;而云麟軍扣住北上談和的昭慶以迫皇帝禪位讓賢,想必更是正中王與兵部之下懷,由此順著皇帝之意,開京畿門戶以迎云麟軍南下,等的便是謝淖會按鄂王所允諾的陣前反水。
諸事一經想通,的心中自然極震極。
二月的寒天雪地中,被晉軍于戎州境劫兵營的每一幕畫面,至今猶在眼前。
此后數月間,于晉都看宮墻外的春日花芽,于金峽關外瞰山谷中的夏夜幽澗,于京城腳下聽兵帳間的秋風颯颯,邊始終不了一個男人。
這個男人,以國書明言索求,將的命納他的掌中,還兵權,予舊部,因一紙婚書而應所取,更在不覺不察之間,默不作聲地將所謀之事以他的方式強勢推助。
……
兵帳幕簾被人自外揭起,有人踱了進來。
Advertisement
卓炎抬眼。
腦海中才想著的男人出現在了的眼前。
戚炳靖步履從容地走至前,將已被撕裂的兩封文書自案上撿起,一瞥之后又扔回案上,目移去看武,說道:“從未應過。”
這話應和著方才那句反問,迫得武額上冷汗又了一層。
卓炎親兵進來,吩咐說:“將此人帶下去關起來。還有,讓我帳外的守衛撤得遠一些。”
親兵遂依言將人綁了拖出去。
幕簾落下,帳中一時變得極安靜,兩人誰都未立即出聲。
就這麼靜了半晌,卓炎才瞟向他,問:“你在外面聽了多?”若不然,怎能夠卡著問完那句話走進來。
戚炳靖于旁落座,答道:“全部。”
一開始,他本無意一直在帳外聽,但說出口的話,思慮嚴條理清晰,層層遞進之下將人得無從應對,不容他帳打斷,于是便多站了一會兒。
他話音落后,二人又沉默了片刻。
夜風刮著兵帳,帷幕被吹得向用力鼓著,有風順著隙進來,撲滅了帳燈苗。
沒人去點燈。
這一片看不清對方的暗如霧如綢,將人攏在其中,令人一時只聽得清外面的風聲與自己的心聲,莫名得催人想要坦誠以待。
黑黜黜的兵帳中,只聽戚炳靖振了振甲,問說:“為何信我?”
對謝淖不會反水的絕然篤定,令他于帳外聞之容。
二人隔得不遠,但卓炎只能辨出他的側影廓,看不見他此刻是何表。他雖只問了四字,卻能在心中替他補全他未說出口的話。
“你要的,從來都不是大平的疆土。”開口,聲音沒什麼起伏,一字字清晰地敲他耳中:“否則,從一開始你便不會留我的命。”
他無聲片刻,又問:“你從何時開始這樣以為的?”
“在你于金峽關城墻上將沈毓章激怒的次日。”
“因何故?”
沒有立即回答,手指無意識地敲著另一只手的掌心,頃,才說道:“那日晨,我與沈毓章議過拆關之事后,他能據實說出為何會被你激怒,他便對我和盤托出。
“我從未對你坦言過我出兵是為了什麼。你曾問過我一次,當時我稱是為報卓氏私仇,你也看似信了。然而你對沈毓章說的那些話,若不是清楚地知悉我所圖究竟為何,若不是全然了解他有著與我相同的不甘與執念,又豈會那般容易地撕破他蓄意的偽裝,以簡單幾句話便將他輕易激怒。
“而你既然早就知悉我為的不是報一己之私仇,就應該知道我所守的是什麼,心中必定明白不論你能給我什麼,我都絕不可能拱手將大平疆土讓予你。
“你亦不可能寄于利用我與云麟軍。旁人或許以為你提兵相助別有所圖,意在借我之力破關之后再尋機與我反目,吞據戰果。但曾與你真正在沙場鋒七次的人,是我。
“謝淖之用兵,謀深而慮遠,從來都是先審我之強弱,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懷必勝之策而后戰,從未有過臨機赴敵之舉。便是如此,你與我之過往手亦曾敗北三回。你又豈會自大地以為與我反目之后真能得勝?
“依你素來用兵之主張,若真要南掠大平疆土,從一開始便不會留我的命。如此,大平北境空虛,你發兵南犯,短時間誰能擋得了你的道?又何必要大費周章地借我之力,圖那只有五六勝算的結果。”
這一席話卓炎講得不快,故而耗費了一些時間。
待講完時,二人的眼睛已適應了這黑暗。
戚炳靖看向,并未回視,但那一雙平日里看起來英氣十足的眉眼此時被夜勾勒得和了許多。
他按所說的想到了那一日。那一日的傍晚,晚風穿堂而過,他醒來時,正對上若有所思地著他的模樣。
而亦是自那一日起,與他相時便慢慢地有了自細微的變化。
停頓許,卓炎繼續說道:“你刻意對沈毓章說那些話,是因你知其必會被傳我耳中。你想讓我自己想,若我想了,遇事便不會輕易人挑撥。若我沒想,你早晚會與我一戰。你擔著這一戰的風險,是想要看一看,我究竟是不是一個無背義之人,我究竟有沒有心。”
沒有問他,說的對或不對。
但最后的這幾句,如火苗細細地燎過他的肺腑,得他沉聲應道:“嗯。”
暗中,卓炎輕輕笑了。
然后手,將油燈重新點燃。
乍亮的芒激得微瞇了一下眼,但很快地,在亮中抬頭看向他,明眸映著火,一如當初晉營相見,得令他挪不開眼。
說:“晉歷建初十六年,你封鄂王。冊禮既行,大晉先帝曾經問你,想要討個什麼樣的人做王妃。當初長寧大長公主講過半句,事后你又補了半句。但是今夜,我想要聽一聽,你的真話。”
戚炳靖看著的眼,沉默了許久。
然后他慢慢地笑了一下,回答:“不求貌,但求才智當與南朝卓疆一般。”
猜你喜歡
-
完結10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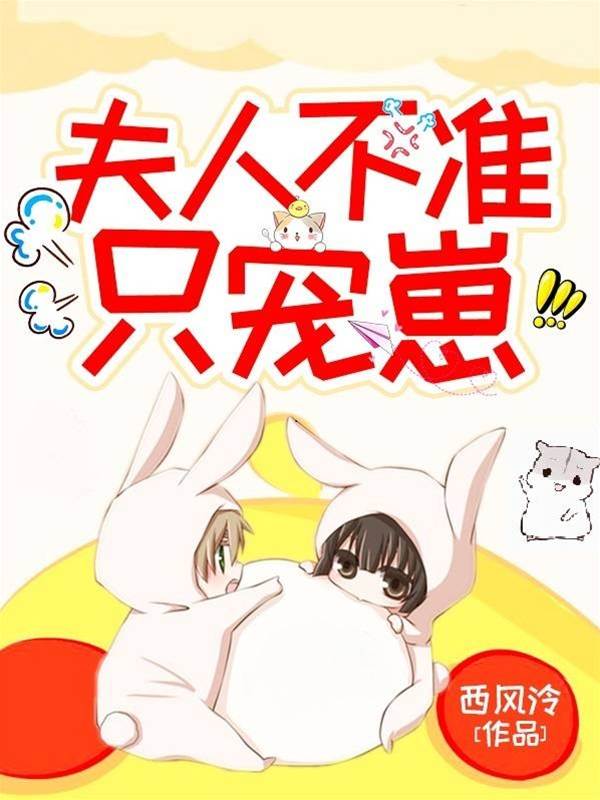
夫人不準只寵崽
南悠悠為了給母親治病為楚氏集團總裁楚寒高價產子,期間始終被蒙住眼睛,未見楚寒模樣,而楚寒卻記得她的臉,南悠悠順利產下一對龍鳳胎,還未見面就被楚家接走。
24.6萬字8 7406 -
完結582 章
顧總,現在的夫人你高攀不起了
結婚三年,楚綿都未能得到顧妄琛的心,一次誤會后,果斷離婚,重回楚家做她的大小姐。父親撒嬌賣萌“寶貝女兒,何時繼承爸爸的億萬財產呀?”媽媽笑顏如花“當設計師跟媽媽干吧!媽媽捧你,必火!”奶奶一臉嚴肅“綿綿必須學醫,一手好醫術,不用可惜了!”楚綿“爺爺,你覺得呢?”爺爺春風得意“要不咱們喝喝茶,種種花,提前享受老年生活?”楚綿以為這就是她的人生巔峰了,誰知,那個一心想要離婚的某渣男怎麼也貼了上來?“綿綿,我后悔了。”渣男醉酒后抱著她,眼尾猩紅,聲音哽咽,“再叫我一聲老公吧……”楚綿莞爾一笑,“前夫哥,您要點臉。”前夫哥“臉沒有老婆重要。”
105.4萬字8.18 3420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