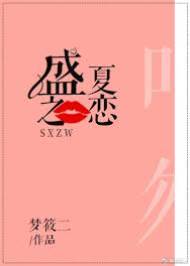《予我千秋》 第24章 貳拾肆
以十分的通徹辟換來了他十分的從容坦,卓炎再度輕輕一笑,沒說什麼。
戚炳靖則泰然問說:“還想要聽什麼?”
他以更直接的方式來應對的直接。
聞此,投向他的目中帶了一調侃:“看你還想說些什麼。”
他接著的目,牽了一下角,道:“很多。”
雖言很多,然二人卻皆未再言。
今夜已說了足夠多,二人之間的氣氛又足夠好,仿佛此刻若有誰再多說半句,便會將這足夠的夜不小心捅破。
被他凝視著,卓炎站起,走至他前。
然后出手,極輕地過他的耳垂,落在了他的肩頭。
被以指尖的地方如被放了一把火,輕而易舉將還想要聽的同他還想要說的話統統燒灰燼。
戚炳靖的臉黯了黯。
他扭過頭,咬住的指尖將的手扯下來,然后將的指尖含口中,以舌輕戲。
的眼睛瞬時浮起一層水霧,目變得如細鉤,勾得他揚臂一把攬住的腰,將按進懷中。
就勢勾住他的脖子,在他暴地解除二人甲的時候,銜咬著他的、耳朵、結,一點一點地將火添得更烈。
他的聲音被功得燒得滾燙,反過來將耳垂也燒得通紅:“想要我怎麼弄?”
昂起頭,被他手下的作撥得難耐,遂用力地掐著他的肩背,著氣答:“……你還不清楚?”
戚炳靖啞著一笑。
他清楚。
他太清楚了。
冰涼的帥案著的前,熱意蒸人的他覆著的后背,死死地按著他扣在腰間的手,汗自頰側被一下下地甩落,濺了那幾半被撕毀的印著鄂王印的文書。
Advertisement
……
是夜臨睡前,卓炎趴在戚炳靖膛上,臉埋進他的肩窩,任他緩慢地著腰間發紅的指痕。
酸痛但又舒服,令微微嘆息。
如是良久,他覺出的呼吸漸趨平和,手勁便也漸漸松了,待睡。
然而卻忽然出聲,聲音輕低,自他肩頭傳耳中:“當日周懌將我丟你大帳前,說他們將軍好。”
戚炳靖聞聲笑了,一時無言。
便也跟著笑了,臉隨著他肩頭的震而輕輕震著。
他從未張口解釋過與他的當初。
而以之聰穎與多思,又怎會想不戎州境二人初見的那一夜。周懌之言,是為了讓他將自罪眷中挑出留下的舉看上去盡合理、避免生出疑心。至于他對的一次次占有與試探,又何嘗不是為了讓這一切盡合二人當初之各自份,為了驗證果真是他為之惦念在心的、心積慮地籌謀與推助的那個人。
今夜,將周懌舊話再提,是在以的方式對他說,都懂。
頃,收了笑意,輕輕蹭了一下他,他便手出去,捻滅了燈燭。
深夜中,他的心跳沉而有力地著的脯。
“我的上,沾過太多。”
卓炎的聲音忽然再度響起。
“該沾的,不該沾的……全沾上了。”又說道。
戚炳靖沒作聲,安靜地聽說話。
而今夜說的那麼多話,都不如此刻說的這兩句,讓他覺得清晰震耳。
的頭在他肩窩里了,似乎想要掩蓋什麼。但他仍然到了肩頭皮上的那幾乎難以察覺到的一丁點意。
曾親手弒兄。的父母亦因而亡。
以雙手掩埋過數不清的同袍尸。亦曾下令屠戮過數萬名敵俘。
Advertisement
而上所沾染的那些鮮,皆是為了多年所守所持之事。
又過了良久,卓炎才聲音悶啞地繼續道:“多謝你。南下一路因你之助,死了很多人。”
謝他,不是為他救了自己的命,是為那些仍然鮮活的大平軍士們的命。
云麟軍的,金峽關守軍的,北面諸路與京畿諸路軍的……的不愿戰,不愿揮戈向同袍,或許他全部都明白,不論曾經與他在沙場上如何戰廝殺過,此刻他都能當得起這一聲謝。
戚炳靖緩緩地以掌輕的后背,算作回應。
待徹底沉靜無聲、在他肩頭進深眠后,他才稍稍側首,就著帳中的月看了看的側。
他的確從未張口解釋過與他的當初。
而那些懂得、以為的當初,卻并不是他與的當初。
……
建初十三年的豫州境,大雪一日接著一日地下。
大晉自西境調來攻城的援軍被派至西邊守圍,無令不需出戰。
每日的清晨及傍晚,他都會借著巡圍之際,策馬出外廓,遠遠地看一會兒風雪之中的豫州城頭。
那個守城的年輕大平將領,他有時能看見,有時則看不見。
能看見的時候,他便會勒馬多站一會兒,目不轉睛地打量那人在城頭的種種舉。年輕將領的形纖瘦而單薄,然勝在意志卓絕不屈,有一回晉軍集各部猛烈攻城,他連續六日每一次巡圍時都能看見他,令他幾乎懷疑那人連續六日不曾歇息過。
每日去看看那個卓疆的年輕平將如何了——此竟為了他此次隨陳無宇出征中最令他沉迷的事。
如是過了近二十日,城下攻城之部中有消息傳至各軍。
消息稱,豫州城大平守軍向城外的箭經晉軍士兵細查,箭鏃看上去極像是百姓們在倉促間燒熔城中錢幣而制的,料想平軍城頭兵罄,難以久持。
Advertisement
陳無宇聽后,特意人去要了一支這樣的箭來看。
除了箭鏃之外,連箭桿也非軍中常制,更像是劈裂門板而制的。
陳無宇看罷后,對他道:“如此來看,我軍回師之日可期矣。”
他則盯著陳無宇手中的箭,久久不言。
風雪之中城頭的一幕幕于他眼前飛掠而過,如此將敗之際,他竟不知有人的意志還能夠堅定若此。
陳無宇看出他神有異,問說:“殿下有何心事?”
他沒有立刻回答,而是抬頭向遠,那一片蒼茫的城墻在他眼中漸漸地化變了雄弘森嚴的宮墻。
須臾,他沉下目,自嘲地笑了一聲,說:“陳將軍。有人從軍,是為戰一國之存亡;有人從軍,卻是為避一己之禍難。”
陳無宇聽了這話,豈能不明白他意指何人何事,一時不知該接些什麼。
他又說:“卓疆雖為敵將,卻令我敬而重之。”他手拿過那箭,翻看頃,“我敬他這一腔忠。若他戰死城頭,將軍請攻城之部收他全尸,我必親為之葬。”
為戰一國之存亡的人,將死;為避一己之禍難的人,可旁視其死而葬之。
豈還有比這更諷刺之事?
然而陳無宇卻沒有等到替卓疆收尸的那一日。
大平守軍兵罄后的第五日,晉軍收到了皇帝命諸部撤軍北退的詔令。
大軍不得不從,攻城之部按令偃旗息鼓。
而晉軍在退兵之時,無人知曉卓疆從京中帶來豫州的兵馬僅剩下了三百人而已,豫州城原守軍皆已陣亡,若晉軍不退,豫州城破不過再一二日之事。
在整軍回撤西境的途中,寒風呼,陳無宇在馬上飲了幾口酒驅寒,然后且嘆且道:“陛下多疑,偏在此時罷兵。大平宿將裴穆清既死,后輩中尚無智勇過人、經百戰之驍將,我軍不在此時將豫州城一舉攻破,真是白廢了這十年難遇之良機!卓疆經此一役,聲名于大平國中必將大振,且此人又是這般堅勇不屈、悍不畏死的子,若大平將他留在北境,往后大晉要想再討得便宜,只怕更難。”
Advertisement
寒風難掩他臉上寒,他冷冷一笑,道:“父皇若不多疑……將軍以為,我還有命活到現在麼?”
陳無宇沉默,目復雜地看他兩眼,然后將手中的酒囊一把扔進他懷中。
他接過,掂了兩下,拔開塞子一飲數口。
酒將口刮得火辣辣的疼,他的心底卻仍然僵、冷、、寒。
回到西境后的沒幾日,他收到了長姊的信函。
自他從軍以來,長寧一月一封家書,同他說些京中近況、皇室諸事,以及總是不了問問他,需不需要幫些什麼。
這回的信中,長寧先說自己又收得幾幅大平先賢畫作,這些費了近四年的功夫才得來的寶貝,待他下回回京時給他瞧瞧。
然后又說,父皇近日抱恙,久不臨朝,國政皆委炳軒置,然又對炳軒不甚滿意,幾次于炳軒覲見時當眾摔罵;侍奉父皇多年的文總管說,父皇這是想他了,但心中又還是恨,便將這恨意轉嫁至了炳軒上;邊但凡知悉的人都勸不了,也不敢勸,更別提旁人了。……
他閱罷,將信燒了。
然后坐著,慢慢闔上了眼。
黑暗中,死窒不的覺籠罩著他,他看不見什麼是真正的生路,無邊無際的不見天日令他想要以洗盡這一切。
但不知為何,便在心中這暗無天日的黑境中,突然莫名地閃過了一刻的皚皚堅城。
那城是風雪之中的豫州城。
那皚皚之是一個人將甲上的厚雪。
那個人在八面圍城的絕境中向死而生的堅悍與孤勇,如同一柄鋒利的長劍,遽然劃破籠罩著他的無邊暗,讓一抹微弱的亮進他的心底。
他睜開眼。
然后給長寧提筆寫了一封回信。
信中他說,皇姊得大平先賢之畫,多賴長年委人于大平京中經營,而今他亦想委皇姊幫忙,于大平收買一個人的消息。
那個人,是他永不可能為的人,卻給了他在絕境中向生的明。
……
清晨,天半亮而鳥鳴清脆。
卓炎枕在戚炳靖肩頭的姿勢整夜未變。
了,就聽見他說:“醒了?”
應了一聲,然后換了一繼續枕著,儼然還未完全清醒。
他遂隨手將攬著,讓安心繼續睡。
然而帳外卻響起江豫燃急切而洪亮的聲音:“卓帥,城中急報!”
“報。”清醒了八九分,沖帳外說了聲。
“昨夜皇帝遇刺,消息剛自城中傳出來!”
卓炎在戚炳靖的懷中僵了一瞬,下一刻翻而起。
一面披,一面冷靜問外面:“死了?”
江豫燃則飛快地回稟說:“皇帝無恙,而王重傷,幾乎不免,現下生死難測。”
猜你喜歡
-
完結3081 章
名門掠婚:顧少,你夠了
他許她一世,寵她入骨,待她如寶。她以為這就是所謂的幸福。 一朝從雲端跌落,粉身碎骨,她黯然退場。 五年後,再次重逢。 “蘇可歆,我們和好吧。” “我們已經錯過了五年,想和好?晚了!” “隻要是你,多久都不會晚。”
556.3萬字8.46 3549658 -
完結1853 章

重生之捉鬼天師
上一世的遲姝顏活的憋屈,明明是個大富大貴的命格,卻被人‘借運’,福氣變黴氣,一手好牌打爛,家破人亡,親戚霸占瓜分財產,高考考試被人舉報作弊,前途儘毀。 而她還傻兮兮的對策劃一切的始作俑者好友感恩戴德。 直到有一天,一個天師點破這一場騙局,收她為徒。 遲姝顏恨,浴火重生,成為道上聞風喪膽的沾滿鮮血的女魔頭,殺儘所有黑心腸的人,因此也斷了自己的生機。 重生一世,她帶著上一世的記憶又回到高考前的十七歲。 這一世的她身負異能,能夠預見任何人的運勢和未來,十分精準,算無遺漏。 她發誓將上輩子害她家破人亡的人全部踩在腳底。 隻是仇還剛報冇多久。 有一天摸到一個商圈大佬,竟然看見自己穿著某款貓耳朵情趣衣服從浴室出來乖乖跪在大佬西裝褲下叫爸爸。 遲姝顏震驚臉:我未來到底混的多摻?這麼冇有節操! 祁臻柏,帝都權勢滔天,根基深厚祁家的掌權人,當之無愧的天之驕子,長相俊美,性格冷漠,手段鐵血強勢,貴市排名第二的單身漢,哪哪都好,唯獨體弱多病,被醫生斷定活不過三十歲。 前世一生定格在二十九歲。 然而今世,遇到她開始,就有些不同了。 暑假掙錢篇一 “這年頭,騙子也太多了。” “可不是,有手有腳,也不乾點好的工作。” 一群人對擺攤算命的遲姝顏指指點點,一邊嫌棄裝騙子也不不裝像一點,遲姝顏巋然不動,一邊畫符,一邊含著棒棒糖。 一個月後 “遲大師,幸好上回您跟我算命,才讓我逃過一劫。” “遲大師,您這驅鬼符籙怎麼賣,我要十張!” “遲大師,您順便幫我把我一家人的運勢都算了吧,錢都不算什麼。” 眾人看著收錢收到手軟的遲姝顏,眼神發亮,高人收錢這麼俗氣的事情居然都‘仙風道骨的’,果然是高人。
250.2萬字8.18 101865 -
完結75 章

誘甜
沈暮有個暗戀的網友。 他是她獨在法國生活四年的特效藥。 但沈暮一直沒鼓起勇氣和他見面。 直到畢業回國。 機緣巧合,沈暮在江盛旗下的公司實習。 某天上班摸魚,她錯轉小文章給網戀對象。 標題是:男人的喘氣聲有多性感? 沈暮瞬間慌顫到無以復加。 剛想撤回,就接到總裁辦的座機。 男人矜貴的尾音漫進耳底:“來我這。” 江辰遇,江盛集團繼承人。 商界公認的最年輕有為的總裁。 英眉墨瞳,冷性自持,想嫁他的粉絲不啻任何當紅流量。 沈暮對這位大佬從來抱著望而生畏的心態。 進他辦公室都在心驚膽戰:“江總。” 辦公桌前,江辰遇撩了下眼皮。 目光從文件凝到她身上:“怕我?” “不、不是……” “站這麼遠?” 等她走近,江辰遇挑眉:“上班開小差。” 沈暮:? 他微不可見地彎了下唇。 嗓音莫名繾綣起來:“想聽麼。” 沈暮:?! #某人表面高冷正經,背地里卻在身體力行地和小姑娘網戀# [閱讀指南] ①、雙向暗戀/治愈/網戀/辦公室,1V1,he,雙c。
28.4萬字8.09 35846 -
連載1055 章

相親當天和豪門大佬閃婚了
急于結婚,喬蕎隨便拉了個“破產”的小老板領了證,本是打算與他相扶相持平平淡淡的過下去。誰知婚后:她想買輛四五萬的奇瑞QQ代步,抽個獎卻能中一輛免費的保時捷。她想貸款買套小樓盤的兩居室,抽個獎又意外中了一套大別墅。她每次遇到困境的時候,他也總是臨危不亂易如反掌間幫她迎刃以解。直到某一天,有人奉承阿諛的來到她的面前,叫她一聲:商太太。她才知道,原來她嫁了一個身家千億的財團大老板。(雙向奔赴,甜寵,打臉爽文,扮豬吃老虎。)
204.2萬字8.46 472175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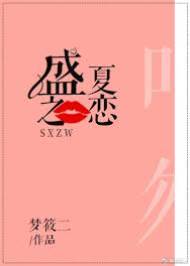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8.18 776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