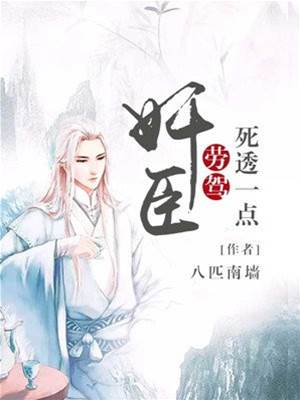《月明千里(嫁給一個和尚)》 第 201 章 海都阿陵番外(作話還有)
……
瑤英的真的摔斷了,醫者幫接骨,疼得一的冷汗。
塔麗哭著幫洗:“公主,您就從了王子吧,別再想著逃走了。王子聽說您孤逃走,不顧自己有傷在,馬上去找您,王子是狼窩裏長大的,暴,能對您如此,您……”
言又止。
瑤英笑了笑,抬起頭,臉上沒有一:“你是不是想說我不識抬舉?”
塔麗眼神躲閃。
瑤英上發燙,意識逐漸模糊:“我是被他搶來的!陪我和親的親兵、我的烏孫馬,他們一個個死在我麵前,上個月謝錦也因為傷勢太重沒了,阿青不敢告訴我……我都知道,我不能倒下,我要帶他們回去,讓他們魂歸故裏……我不會忘記,他辱我,折磨我,把我當玩……我熬了過來,所以了一個特別的玩……”
是李仲虔帶大的,雖然多病,但是沒有過什麽委屈,有兄長疼,有忠心的部曲,是一個人,好端端一個人,不稀罕海都阿陵折磨之後的那一點施舍!
可是他太強大,北戎太強盛,想要逃走真的太難了。
瑤英渾都在疼,指甲陷進的織,勾起幾條金線。
睜開眼睛。
床上鋪著的不是尋常毯,而是一張旗幟,是從葉魯部帶出來的,塔麗幫收著。
王庭的旗幟,雪白金紋,有種世獨立的傲岸。
瑤英攥下的旗幟。
曇羅伽。
一個慈悲的僧人,王庭的君主。
還有機會,不能放棄。
第6章
大帳裏,海都阿陵的部下和瓦罕可汗的人在對峙。
兩幫人馬氣勢洶洶,手都按在刀柄上,氣氛僵持。
一個細長眉眼、穿錦的男人越眾而出,輕蔑地瞥一眼因為傷隻能坐著的海都阿陵,滿臉不悅地道:“阿陵,你不出那個漢,我們回去怎麽向大汗代?葉護是和大汗一起長大的族弟,他不明不白死了,大汗隻是要你出漢而已,你這麽怠慢我們,是不把大汗放在眼裏嗎?”
Advertisement
海都阿陵抬眸,淡淡地道:“不敢對大汗不敬。不過和葉護爭執的人是我,前幾天襲葉護的人也是我,此事和漢無關,我自會向大汗解釋清楚,至於葉護到底死在誰手上,大汗明斷,一定能查出真兇,不會冤枉了我。”
錦男人冷笑:“不錯,大汗明察秋毫,自有決斷!但是我今天是來帶走漢的,引得你和葉護刀兵相向,是不祥之人,天底下的人那麽多,你不會為一個漢得罪葉護的家人吧?把出來!”
他話音落下,跟隨他的人紛紛把刀,滿帳刀影晃。
托木倫幾人然變,也跟著拔刀。
海都阿陵眼神示意部下退後,站起,走到錦男人麵前:“賀哆,我是大汗養大的,不會拿自己的人出去頂罪,大汗要怎麽懲治我,我先領了。”
賀哆瞇了瞇眼睛。
海都阿陵停頓了一下,一字字道:“這個漢,你帶不走。”
他沒穿甲,麵平靜,賀哆卻覺到了他上約約克製的淩人殺氣,托木倫他們站在他後,個個兇悍。
一隻深不可測的頭狼,帶著一群絕對忠於他的野狼。
賀哆定了定神,強撐著沒有出怯懦之態,怒道:“這是你自己選的!既然你拒不出漢,那就別怪我下手不留!”
海都阿陵一言不發,走出大帳,扯下上衫,麵朝著瓦罕可汗所在的方向跪下,赤著的腰腹纏著厚厚的紗布,可以看見殷紅跡出。
“王子!”
托木倫幾人搶上前,海都阿陵搖搖頭,幾人暗暗咬牙,對一眼,退了下去。
賀哆獰笑,揎拳擄袖,親自行刑。
營地裏的人不敢靠近,站在遠觀。
賀哆說到做到,下手果然沒有留,長棒專門挑著海都阿陵傷的地方打,托木倫氣得臉紅筋暴,險些把牙齒咬碎。
Advertisement
等賀哆停手離開,托木倫連忙扶著海都阿陵回帳。
醫者給海都阿陵換藥,他連吃了幾枚強心丸,揮手讓所有人退下。
不多時,氈簾晃,腳步聲由遠及近,一人走到木床前,皺眉道:“你居然為了一個漢當眾挨打,難道你真像流言裏說的那樣,被一個漢迷得神魂顛倒?”
海都阿陵睜開眼睛,翻坐起,麵無表地道:“這事和漢無關,我和大王子他們遲早會起衝突。”
來人審視他片刻,“你心裏有數就好,你是堂堂北戎王子,神狼的後人,斷事已經為你挑選好妻子,你的正妻隻能是北戎貴族之後,別為一個漢前功盡棄!”
海都阿陵撇撇角:“賀哆,說正事。”
賀哆臉上表搐了兩下,掩下不滿,道:“我已經代表大汗責罰過你,葉護這事算是先揭過了。王庭久攻不下,軍中人心渙散,斷事要你早做準備,大汗不久就會召你統兵。大王子他們的手段,大汗看得很明白,這次大汗為了息事寧人才派我來討要漢,大汗知道葉護不是你殺的,你切勿急躁。大王子那邊,斷事會替你留意。”
海都阿陵點點頭。
賀哆和他談了一會兒,怕消失太久被人懷疑,掩上麵巾,悄悄出去。
“賀哆。”
後傳來海都阿陵的聲音。
“記住你的份,別打漢的主意。要是出了什麽事,我親自取你的命。”
賀哆心裏一驚,出了一冷汗,頭也不回地離開。
海都阿陵躺下養傷,一邊思考該怎麽應付大王子,一邊想著能不能趁這個機會在攻打王庭時立下功勞,不知不覺睡了過去。
的手著他的額頭了過去。
海都阿陵即使睡在自己帳中也十分警醒,眼睛還沒睜開,右手已經飛快橫掃過去,閃電一般,攥住床邊人的脖子。
Advertisement
手細膩,子掙紮著息,雙手攀著他的胳膊,不停掙紮。
海都阿陵眉頭輕擰,手上力道不減:“你怎麽在這裏?”
瑤英在他掌中抖,紅張開,麵上紅,滿頭鬢發鬆散,一雙眸子怒視著他,因為呼吸不暢,眼中淚水盈聚,眸粼粼,潤中迸出兩道倔強的寒,似有兩團火焰在裏麵熊熊燃燒。
振迅速湧遍全,海都阿陵幾乎立刻起了反應,這樣的風如果是在床上,該是何等的暢快。
他可以日數,什麽模樣的人都見識過了,但卻沒有哪一次能讓他有此刻這種難以言說、不可抑製的興難耐。
海都阿陵直接將人拽到眼前,對著那雙朱紅的咬了下去。
他淡金的眸子裏滿是懾人的.,瑤英睜大眼睛,不知道從哪裏來的一力氣,使勁往後一仰,掙開海都阿陵的錮,整個人摔倒在地,劇烈咳嗽,渾發抖。
海都阿陵被推回床上,猛地清醒過來,試著抬了抬,發現自己全無力,完全使不上力氣。
“怎麽回事?”
他問,聲音已經恢複平時的淡漠。
瑤英了幾下,強按下驚懼,抬手攏起散落的發,回到床邊,舉起藥碗,“你挨了打,昏睡過去,發起高熱,托木倫要我來照顧你。”
海都阿陵嚨又幹又,底下還興著,上卻酸沉重,傷口可能化膿了。
他聞到自己上一皮腐爛的氣味,著帳頂,嗤笑一聲:“托木倫被你騙了,居然讓你來照顧我,也不怕你趁機殺了我。”
瑤英沉默,拿起水囊,喂他喝水。
海都阿陵咕咚喝了半水囊的水,結滾,目凝定在臉上。
脖子上還留著他剛剛掐過的紅印,臉上沒有一表,冷冰冰的,紅豔。
Advertisement
他被賀哆當眾打了一頓,換做其他人,肯定早就得淚水漣漣,卻毫無反應。
海都阿陵笑了笑:“你照顧我的時候是不是在想怎麽做可以殺了我?”
瑤英眼簾抬起,漆黑的眸子和他淡金的眸子對視,“不錯,我想了好幾種辦法,可惜托木倫還是留了一手,我沒有下手的機會。”
海都阿陵忽地手,抬起瑤英的下,手指挲了幾下。
“如果你了我的人,和其他北戎人那樣為我生兒育呢?”
瑤英迎著他迫人的目,平靜地道:“那我就有更多下手的機會,殺一個沒有防備的枕邊人更容易。”
兩人離得很近,呼吸纏繞,卻沒有毫旖旎,一道氣息剛猛霸道,一道氣息堅韌,兩道氣息無聲地對抗、相爭,他看似掌控全局,牢牢地製著,卻始終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順從。
海都阿陵明白,假如他先毀了兩人之間的約定,眼前這個人一定會得寸進尺,利用這一點強迫他做出更多讓步。
他給不出,那就隻能殺了。
要麽得到,要麽毀了,他不能容忍在別人麵前溫小意,在別的男人下歡愉。
就像他馴服不了的鷹,隻能被他親手掐死。
可他現在暫時舍不得就這麽毀了,那麽多人,唯有可以挑他的心思。
海都阿陵鬆開手,躺回枕上:“我了。”
瑤英眼皮低垂,眸中水閃爍,弱無依的模樣,像是隨時會流淚——但終究沒有落淚,轉捧來托盤,遞到海都阿陵麵前。
“喂我。”
海都阿陵吩咐道。
瑤英一語不發,捧起碗送到海都阿陵邊。
海都阿陵頭昏腦漲,意識越來越模糊,其實本沒什麽胃口,不過看著不甘不願地伺候自己,心裏莫名快意,一碗清湯寡水也喝了下去。
“大王子的人還會責罰你嗎?”
瑤英忽然問。
海都阿陵挑眉,莫非看著冷漠,其實心裏還是有些?
他心裏很清楚不可能關心自己,但是心底仍然有愉悅浮了起來,“你兄長和太子李玄貞會講和嗎?”
瑤英搖搖頭。
李玄貞不止一次咬牙切齒地告訴,他不會放了李仲虔。
海都阿陵冷笑:“大王子也不會放過我。我不是大汗的兒子,可我比大汗的所有兒子都要優秀,所以我必須死。我是狼養大的,狼子野心,大王子、二王子……小王子金,不管誰繼任大汗,我隻有死路一條。”
從前,他是狼孩的時候,跟著母狼捕獵,赤...,毫無恥可言。
第一次看到部落時,他激得無以複加。
原來他是人,這世上有很多和他一樣的人,他不是野的怪胎。
瓦罕可汗收養他,教他和人一樣走路說話,告訴他人不會像野那樣生活。
高熱讓海都阿陵的記憶更加清晰,他眸中暗流洶湧,“大王子他們找到我,告訴我,我是狼窩的野種,像狗一樣滿地爬,不配做大汗的義子……我想融部落,必須要做一件事……”
瑤英眼底掠過一道了然。
海都阿陵並不意外知道這事,想殺他,一定打聽了很多他的往事。
能這麽快猜出來,他角勾了一下,接著道:“我必須親手殺了養大我的母狼,他們才會接我。我想做大汗的義子,想為一個人,於是我拿著刀回到狼窩,親手殺了養大我的狼……”
他滿是,拖著母狼的回到部落,等著大汗的獎賞。
等來的卻是大汗不敢相信、警惕的眼神。
大汗欣賞他的勇武,最後還是收養了他,但沒有認他當義子,而是讓他拜其他人為義父——他不是大汗的義子,也就不能和其他王子競爭大汗之位。
“他們告訴我,想做人,就得殺了母狼……我殺了母狼,他們又告訴我,我狼心狗肺,做不了人,以後一定會背叛部落……”
海都阿陵笑出了聲:“不管我是人還是野種,等我為大汗,所有人都會臣服在我腳下。”
他強壯,天賦過人,他比其他人更出,注定不會久居人下,他馬蹄所到之,都會被他率兵征服,東方,西方,更遙遠的從來沒有族人踏足的地方,都將為他的領土。
強者為尊。
弱小者會被無捕殺,為其他類的食,強大的野才能吃飽肚子,在荒野中存活下去。
這也是部落的生存之道。
他絕不會坐以待斃。
海都阿陵的聲音越來越低,意識墜黑暗,睡了過去。
半夢半醒間,他掃一眼床邊的瑤英,朦朧的爐火微籠在上,側對著他,靜靜聽他訴說,眉眼看起來格外和。
海都阿陵邊有很多忠心的部下,一隻狼無法抵抗整個部落,也無法南征北戰,他從小就懂得怎麽收攬人心,讓別人為他出生死。
除此之外,他沒有姐妹,沒有兄弟,沒有信得過的人,也沒有孩子——孩子太累贅,現在的他危機四伏,不需要孩子。
人能讓他銷.魂,但.過去,他不想多看們一眼,們應該乖乖聽從他,在他需要的時候殷勤服侍他,為他持庶務,以後為他生兒育,讓他的脈延續。
而他保護們,讓們食無憂。
。您提供大神羅青梅的嫁給一個和尚
猜你喜歡
-
完結3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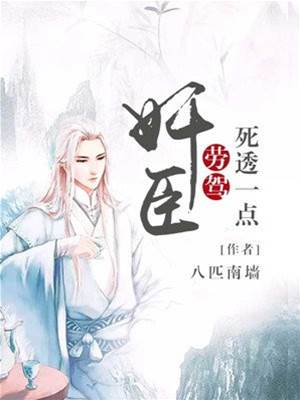
奸臣,勞駕死透一點
蘇問春五歲時撿回來一個臟兮兮的小乞丐,十年后小乞丐踩著蘇家步步高升。春風得意之際,蘇問春伏在他腳邊求他為蘇家討個公道,只得他兩個字:活該!后來蘇問春受盡酷刑著牙闖出一條血路終得平反。兩人尊卑顛倒,他一身囚衣坐在死牢,卻是一臉繾綣:“不是一直…
70.1萬字8 6496 -
完結723 章

嫡女謀:邪王盛寵傾城妃
她是褚王府正牌王妃,本該榮華富貴,一世無憂,卻眼瞎心盲,害的身邊人盡數慘死,親生骨肉被煉成丹藥。 幾世輪迴磨鍊后,攜靈寵高調重生! 從前的她,囂張跋扈,愚昧無知;如今的她,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復仇是她重生的唯一目標! 為了彌補遺憾,本想偷了種子就跑,卻不想還是落入了那個男人的陷阱…某王爺斜靠軟榻,慵懶一笑:「聽說王妃想要個孩子,今日月色朦朧,星辰萬里,本王有一本『造人指南』想跟王妃共同探討…」
131.2萬字8 27994 -
完結88 章

錦衣良緣
燕京人人都知,定安伯府的庶出六小姐是個虛榮女,她整日花枝招展,千嬌百媚,貪慕榮華,誰娶她誰倒霉。 燕京也人人都知,永平侯府的三公子是個紈絝子,他整日裏打馬遊街,吃喝玩樂,不求上進,誰嫁他誰可憐。 一紙詔書將這兩個荒唐人物扯到了一起,做了夫妻。 ...
13.1萬字8 9591 -
完結114 章

笑話?狀元郎和大將軍,這還用選
李華盈是大朔皇帝最寵愛的公主,是太子最寵愛的妹妹,是枝頭最濃麗嬌豔的富貴花。可偏偏春日宴上,她對溫潤如玉的新科狀元郎林懷遠一見傾心。她不嫌他出門江都寒門,甘等他三年孝期,扶持他在重武輕文的大朔朝堂步步高升。成婚後她更是放下所有的傲氣和矜持,為林懷遠洗手作羹湯;以千金之軀日日給挑剔的婆母晨昏定省;麵對尖酸小氣的小姑子,她直接將公主私庫向其敞開……甚至他那孀居懷著遺腹子的恩師之女,她也細心照料,請宮裏最好的穩婆為她接生。可誰知就是這個孩子,將懷孕的她推倒,害得她纏綿病榻!可這時她的好婆婆卻道:“我們江都的老母豬一胎都能下幾個崽兒,什麼狗屁公主有什麼用?”她舉案齊眉的丈夫怒道:“我平生最恨的就是他人叫我駙馬,我心中的妻與子是梨玉和春哥兒!”她敬重的恩師之女和她的丈夫雙手相執,她親自請穩婆接生的竟是她丈夫和別人的孽種!……重活回到大婚之後一個月,她再也不要做什麼好妻子好兒媳好嫂子!她要讓林懷遠人離家散,讓林家人一個個全都不得善終!可這次林懷遠卻跪在公主府前,哭著求公主別走。卻被那一身厚重金鎧甲的將軍一腳踹倒,將軍單膝跪地,眼神眷戀瘋狂:“微臣求公主垂憐……“
21.3萬字8 1508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